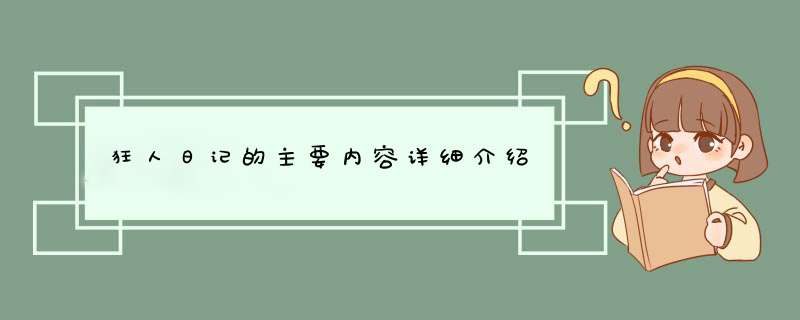
《狂人日记》是鲁迅创作的第一个短篇白话日记体小说,也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狂人日记》主要内容。
主要内容
小说主要内容是以一个“狂人”的所见所闻,指出中国文化的朽坏。日记前言以文言文书写,为日记作者的一位友人所写。日记作者之前患了“迫害狂”的病,他已痊愈。日记则以白话文书写,为作者患病时的所见所闻。”《狂人日记》整篇作品几乎都是狂人内心世界的表白。狂人认为周围的人都在吃人,自己也要被迫吃人或被人吃。狂人被关起来,拒绝家人送来的饭菜,拒绝被医治,一直劝说周围人不要再吃人。直到最后狂人发现,也许自己就曾在无意中吃过自己妹妹的肉。绝望中的狂人发出“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的呼喊。
狂人日记佳句鉴赏(1)“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表现了狂人怀疑传统,研究一切得启蒙者的思想特点。
(2)“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是狂人对“吃人者”本质的认识。
(3)狂人在“歪歪斜斜的每叶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的历史的“字缝里”,看出了“吃人”两个字,是他对封建礼教的实质所作的历史概括。作者中所提及的活生生的吃人的事实,则是这一历史和结论的旁证。虽然狂人把“把脉”理解为“揣一揣肥
瘠”是混乱的臆想,但既然古代能够“易子而食”,现实中狼子村能够吃人,为什么自己的大哥不可能吃自己呢。荒诞的逻辑中自有逻辑的合理性。
(4)狂人“踹”了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是对于吃人社会的“经典”“戒律”的蔑视和斗争。通过“古久”和“陈年流水簿子”的形象暗示意义,将矛头直接指向了保守
的传统文化。
(5)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是狂人对未来社会的幻想和规划。
作者简介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字豫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民主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早年与厉绥之和钱均夫同赴日本公费留学,于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肄业。“鲁迅”,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最为广泛的笔名。
《狂人日记》讽刺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
“吃人”:封建主义礼教。《狂人日记》是满纸疯话,却是对中国社会的怀疑和拷问。狂人的精神病状的描写是逼真的,而他的几乎所有语言又都是带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的。他的形象本身的象征意义则更为突出。
“吃人”是鲁迅对现实的隐喻,不仅指吃人肉,也指人间苦难的事实和产生苦难的根源。通过象征和暗示,从作品字里行间所传达出的信息中可以发现,狂人实际上是一个站在时代前列的反封建礼教、反封建家族制度的启蒙者。
《狂人日记》作品鉴赏
《狂人日记》整篇作品几乎都是狂人内心世界的表白。狂人认为周围的人都在吃人,自己也要被迫吃人或被人吃。
狂人被关起来,拒绝家人送来的饭菜,拒绝被医治,一直劝说周围人不要再吃人。直到最后狂人发现,也许自己就曾在无意中吃过自己妹妹的肉。绝望中的狂人发出“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的呼喊。
在小说的开头“狂人日记序”中写道:“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狂人病体痊愈暗示的是其他人在精神上的不正常。在众人眼中,狂人是一个患有迫害狂恐惧症的病人,在狂人眼中,其他人才是吃人的人。这样的不同角度和立场,深刻的揭示了病态社会的悲哀。
中国历史上的狂人中国历史上的狂人中国历史上的狂人中国历史上的狂人 在中国五千多年古老的历史和文化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以其独特的历史条件和文化氛围,孕育和培养了自己的知识阶层——士,亦即所谓文人。勿庸讳言,文人阶层是有其自己的特点的。在中国历史上,许多文人以极大的热忱,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和探究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和社会,正所谓上察天文,下究地理,忧国忧民,直面人生。由于时代条件的不同,主客观因素的差异,在文人阶层中,也呈现千姿百态之状,从而展示出异常复杂,异常鲜明的个性特征。有的对现实不满,予以猛烈抨击,以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有的要求进取而被拒纳,便心灰意冷消极遁世;有的恃才傲物而狂放不羁;有的因生活遭际而变得孤傲不群;有的视名利如粪土,或醉心艺术而与世俗远离;……凡此种种,无不与现实的社会规范发生尖锐对立。于是,具有这样一些个性特征的文人也就被世俗社会视为“狂人”。 文人变成狂人,虽然人数不多,但在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中,都能找到一些,这就形成了一种狂人现象。狂人现象既反映了中国历史上一般士人阶层的心态运动过程,但又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这个范围,从而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民族心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天日益引起人们重视的民族心态研究中,把它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加以总结和讨论,是很有意义的。可惜的是,到今天为止,学术界对中国历史上的狂人现象并没有给与足够的重视,虽然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狂”作为一种人格,给中国士人,特别是诗人以巨大影响,并且形成了狂狷人格,如东方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张节末的《狂与逸——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两种人格》,把狂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两种基本人格加以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叶舒宪的《阉割与狂狷》,也是把狂作为一种人格与被阉割的人格相对比,来揭示民族性格中的两种相对立的现象。但把狂人作整体研究,或是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来研究的成果,现在还不多见。应该说还是一个空白。因此,对狂人现象进行整体研究,以揭示这一历史现象产生的深层背景,从而进一步揭示中国知识阶层的独特个性,乃至整个民族的性格,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何谓“狂”与“狂人” 狂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其意义有三: 一是如《老子》所说:“驰聘畋猎令人心发狂”之“狂”。这种狂有内在的和外在的两种表现。由于外部条件的刺激,思维主体在心理活动中出现超正常的精神亢奋。“心不定故发狂”(魏源《老子本义》),心理意识在一种不正常的不稳定的状态中运动,致使思维者的心理规律出现紊乱,情绪的变化非常明显。一般情况下,这只表现为内在变化,即使诉诸外部行为,也不会超出正常人的行为标准。当外界刺激一旦突破思维主体在精神上的承受能力,使之高度紧张的精神世界完全崩溃,那么,思维主体的行为便会随内在心理的紊乱而出现异常,这就是平常人们所见到的精神病患者。 二是如孔子所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之“狂”。这里的狂,已不只是纯粹的心理意识,而是转化成人格表现。它所体现的不仅仅是行为上的不合于伦理规范,更重要的是它表现为思维主体把自己与其他社会个体相区别的思想上和行为上的标志。孔子赋予它的规定性特征是直、肆、荡。“直,正见也”(《说文解字》),“肆,极意敢言”,“荡,无所据”(刘宝楠《论语正义》),可见,孔子所谓狂,是敢于直陈正见,敢做敢为的行为表现。这些行为表现是行为者基于对社会和群体的责任感,为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群体利益而产生的,是行为者要求积极进取,有为于世的反映。如果“见”不以礼法为依据,则必会失之于“荡”。“据,即据于德之据,无所据,则自放于礼法之外”(刘宝楠《论语正义》),超出礼法之外,毫无所据,必去“直”而成狂妄。由直而狂,乃是孔子所谓狂的根本所在。因直而能肆,肆则能进取,肆之极则为荡,荡则狂妄。在孔子看来,真正的狂者是勇于进取的。与狂一起被孔子所称道的还有狷。“狷者守节无为”,“狷者慎守一节,虽不能进取,亦自不为不善。”(刘宝楠《论语正义》)即所谓独善其身者。他们虽不能补社会之偏,但能在乱世中保持气节而不被世俗所污。狷介中正,洁身自好,保己之德,正己之心,其实是狂的另一种表现。孟子对狂的解释是:“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孟子·尽心下》)赵歧注曰:“嘐嘐,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考察其行不能掩其言,是其狂也。”(焦偱《孟子正义》)朱熹也认为,“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由于狂者怀有一种阔大的抱负,所以其出言便要超出一般社会个体的接受能力和认识水平之上。他们思慕古圣先贤,欲以古圣贤自比,但其行为却往往与其言不相符,言大而行小,故显出其狂妄。这虽然超出了孔子狂而直的特征,但其慕古人之高风亮节并因以自况,也是勇于进取的一种表现。 三是如王夫之之所谓狂。在王夫之那里,狂是与圣相对照的。“所念者特未定矣,之于圣之域乎?之于狂之径乎?克念而奚即入于圣?故必目言其所念者伊阿?而后圣狂之分以决。”王夫之的圣与狂指的是两种思想境界,二者的区别在于“念”。所谓念者,“意动而生心者也”(王夫之《尚书引义·多方》),即思维主体的各种欲望和思想意识。这些欲望和意识必须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必须使之合乎一定的社会规范和伦理要求。思维主体对这种“念”的态度不同而行为表现亦不同,念者入于圣,罔念者入于狂。狂者,就是毫无限制地任“念”扩张,不加任何约束。他不能坚定自我与社会共同的伦理信念,而去任意对古已有之的共同信仰和道德规范加以指责和违反,其念不能专一,并且自以为是,有意识地超出社会共同规范的限制。“乃所谓异端者,诡天地之经,叛先王之宪,离析《六经》之微言,以诬心性而毁大义者也。”(王夫之《读通鉴论》)这种“异端者”,正在于对先圣先贤的言论和礼法提出质疑而不使自己局限于已有的思维框架之中,能够按照自我的思维模式去审视这个被赞誉被称颂的世界,重新认识自我在这个世界上本有和应有的地位。“由此言之,彼异端者狂也,其自谓圣而适得狂者,罔念而已矣。”(王夫之《尚书引义·多方》)在王夫之的狂之概念里,更多的是与传统和社会普遍意识相悖的叛逆思想,其所有的外部表现,全在于内心的妄念,其行为的不检,言论的易变,全应归之于心的易动。如果说,在孔孟那里,狂多少还有被称道的方面,而在王夫之这里,狂则完全被否定了。这种区别,显示出了历史上对狂由肯定到否定的思想演变过程。 以上是古人对狂之意义的三种理解。除前者着重于纯粹心理意识的变化而不搀杂社会功利性因素外,后两者所阐明的则主要是狂者因内在思维与社会群体正常思维不同而造成的与一般社会的冲突。这是非狂者在非主观的角度上对狂者的一种评判。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他们都是以社会规范行为标准对狂者作出评价。但假若以狂者自身来看,所有的狂都是思维主体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把自我个性突出出来,使自身非常鲜明地超越于社会群体之外,形成了超社会的个体人格。这种狂者与一般社会的对立,使一般社会的共同伦理要求和社会规范成为狂者破坏的主要目标,他们对已为整个社会群体所普遍接受和遵奉的社会规范提出质疑,并以自己的行为予以撞击。当然,在狂人中这种批判精神有的表现明显,有的表现隐约,从而呈现一种扑朔迷离的复杂状态。 今人对狂的解释建立在现代心理科学发展的基础上,更为科学和准确。现代心理学家称狂人现象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其主要特征是“时常做出不符合社会要求的行为”。①这种反社会型人格障碍一般又被称为“精神病态”。但按默比乌斯的解释应是“正常人的一种疯病,变异,是正常人的不正常”。②所谓正常,是指狂人们——即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者——的思维意识并非是错乱的,而是正常的,他们都有各自的认识社会的标准、生活准则和思想追求及正常的行为方式,而且其中大部分狂人都有一般人所常有的有为于社会的功利要求和价值观念。但是,由于他们的理想要求在现实社会往往得不到满足或在现实社会中受到挫伤,因而在行为方式上便有意识地突破现实社会的规范,使自身与社会相对立,与群体相脱离,着意表现自我人格,突出自我个性。如果与整个社会的一般伦理规范相比较,这就具有了“不正常”的特点。正因为这种所谓的不正常,才使他们自身具有了特殊价值。如果消除了这种不正常,那么他们作为狂人的价值也就消失了
综观中国历史上的狂人现象,狂人的“不正常”,亦即“不符合社会要求的行为”,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以精神病患者的行为表现逃避社会制裁,保全自身;(二)远离社会,放任自然,洁身自好,隐逸不出;(三)在“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信念指导下,视“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为己任而又傲人傲世;(四)行为放纵,出言狂妄,孤傲不群,蔑视礼法;(五)远在江湖而心怀朝阙,身世飘零而忧国忧民,虽忠君爱国,但不被见用;(六)性情孤僻,不入世俗,醉心艺术,任性任情;(七)恃才傲物,言高忤上,蔑权贵,疾世俗,功名利禄,不为之动;(八)敢于对先圣先贤的思想提出质疑,“诡天地之经,叛先王之宪”,诬心性而毁大义,自谓异端。凡此种种,无不因志高言大、狂放不羁而与社会、政治、伦理发生冲突,从而表现为一种反社会性。这种反社会性既有内在的主观因素导引,又有外部的客观条件促成,因而使狂人现象成为一种极为复杂、极为矛盾的社会和心理现象。 二、狂人的八种类型 根据上述狂人的定义,我们大致可以这样说,先秦的箕子、许由、接舆、庄子、杨朱、屈原,两汉的郦食其、东方朔、仲长统、赵壹、孔融、弥衡,晋代的皇甫谧、竹林七贤(阮籍、稽康、刘伶、向秀,阮咸、山涛、王戎)、陶渊明,唐代的贺知章、李白、杜甫、张旭、怀素,宋代的苏轼、米芾,元代的倪瓒,明代的唐寅、祝允明、李贽、徐谓,清代的朱耷、石涛、郑板桥,等等,皆属狂人之列。 中国历代狂人因生活的时代条件不同,各自的个性心理因素不同,因而狂人行为的表现方式也不尽相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某些狂人的身上找到这方面或是那方面的一致性或相似性。因此,也就可以对之进行类型的划分。为了论述的方便,现根据中国历代狂人的行为表现和思维意识上的共同特征,将之概括为以下八种类型。但限于篇幅,对这若干历史狂人不可能面面俱到,更不可能详加论述。 (一)佯狂者 关于狂的外在表现,《太平御览》卷七三九引《神异经》说:“西方有人,饮食,被发佯狂。其妇追之不止,怒,亦被发。名曰狂,一名颠,一名狷,一名风。此人夫妻与天俱生,狂走东西。”这种狂的外在表现,被佯狂者所利用。佯狂的目的是为了逃避,为了使自己摆脱某种与己不利的困境,有意而为之。在佯狂者中,有的是参与了某种政治斗争,失意后以佯狂来求得宽容,逃避胜利者的制裁。商代“纣为*佚,箕子谏,不听,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同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于民,吾不忍为也。’乃披发佯狂为奴。”(《史记·宋微子世家》)《史记·龟策列传》也记载:“箕子恐死,被发佯狂”。汉代蒯通劝淮阴侯反汉,不听而佯狂为巫(《汉书·淮阴侯列传》)。有的是禀性高逸,不愿被世俗所牵制,为保持自己个性,以佯狂脱离群体而独身自处,如楚狂接舆。“陆通,字接舆,楚人也。好养性,躬耕以为食。楚昭王时,通见楚政无常,乃佯狂不仕,故时人谓之楚狂。”(皇甫谧《高士传》)“楚狂接舆,躬耕以食,楚王使使者赍金百镒,愿请治河南,接舆笑而不应,乃与其妻偕隐”(《韩诗外传》)。 可以说,凡佯狂者,皆是世俗社会及其政治斗争与思维主体直接冲突的结果。他们戴着狂者的假面具,掩藏起真实的自我,以其狂乱的行为,掩盖着真实的目的。 (二)隐逸的狂人 隐逸之狂,按孔孟的定义应该称之为“狷”。刘宝楠《论语正义》曰:“狷者慎守一节,虽不能进取,亦自不为不善。”焦循《孟子正义》引《国语》韦昭注曰:“狷者守分,有所不为也。”所谓“慎守一节”、“守分”,乃在于保持自身高洁而不与世俗相并论。狷者不是直接与社会相冲突,而是使自己远远地避开世俗社会,不参与外部的政治活动和社会事务,静心寡欲,弃名绝利,以求得与天地为一的思想境界,在内心深处体验自然与我合一后的愉悦情感,以自己的行为向世俗社会提出抗议,具有明显的反社会性。因其行为隐秘,不与世人来往而又超逸不俗,居山林处幽雅之境而被称为“逸民”或“隐逸者”。
隐逸的狂人最大的特点是鄙弃名利,蔑视权贵,不与政治同流,不与世俗交往,对于现行社会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拒不接受。他们追求一种超社会超物质的纯自我理想型的思想境界,表面看来是使自我与自然合一,实际上正是在这种合一之中使自我人格得到了充分体现。他们对自我人格的热烈追求,使得他们生活恬淡虚静,从而实现了无为和自由、真情与真我的合一。这成为他们对现实政治和现有伦理规范进行抗争的特殊斗争形式。“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情”,“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后汉书·逸民传序》)。总之,他们以不仕为高标,以远俗为手段,以适情为追尚,以全生为目的,内心恬淡,行为超逸,使自己远离社会,脱离政治,洁身独处,以世外人的身份冷眼观世事的变化。许由听尧让位而临河洗耳,庄子“宁其生而曳尾于途中”而不愿“死为留骨而贵”(《庄子·秋水》),杨朱“捐一毫利天下而不为,悉天下奉一身而不取”(《列子·杨朱》),他们无不“立乎损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由此看来,隐逸之狂的真正狂处,在于他们将自身与社会相对立,不将社会普遍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加于自己身上,而是对此进行逃避和消极的对抗。他们虽与世俗社会无面对面的冲突,以无为对有为,而且也不把自己对社会的反对强加于他人身上,但它确实构成了一种反抗,即一种消极的反社会行为,因此,对社会心理和民族心态的影响,是很大的。 (三)入世的狂人 真正能体现孔子“狂者进取”精神的,应是入世的狂人。积极入世,有为于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的主要表现,是中国古代士人阶层的主要特征,也是士人实现自我价值的主要途径。它主要表现为社会个体对现实政治的热心和济世拯民理想的渴望。但是,在古代中国,社会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需要有相应的政治地位,政治地位的获得是才智发挥的先决条件。只有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价值理想才有得以实现的可能。因此,中国古代士人阶层从来把地位和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对“庙堂之高”的向往成为历代文人的共同特征。入世的狂人则把这种向往推至极点。“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历代文人理想的入世之路,并有许多人经由此路走向“庙堂”。 士人阶层对家国的忧患意识则是其入世的根本原因。“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种对国家对人民和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使得他们在忧叹之中努力寻求济世救民的方案。这种自觉的参与意识又构成了他们入世的主要内容。 在忧患意识和参与意识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古代士人阶层中,有许多人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面对纷乱复杂的社会,油然而生济世救民非我莫属的思想。东方朔就很典型。他曾上书武帝曰:“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二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汉书·东方朔传》)迫切的入世之心,溢于言表。他们对那些碌碌无为的庸俗之辈往往加以鄙视,并以此而傲人傲世。但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权利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又往往使这些地位相对低下的士人,难以跻身于政治权力的圈子之中,致使他们生发出无限的怀才不遇的失落感,从而对社会产生怨恨。傲世和怨世成为中国古代士人阶层的普遍心态。 入世的狂人正是在傲世和怨世的双重心态挤压下产生的。他们一方面要突破政治条件的限制,寻求实现理想和抱负的道路,使自己的才能得到发挥,填补价值理想不能实现时的内心创伤,因而希冀一朝被执政者理解、发现、认同和接纳。为此,不惜狂言乱语,大话连篇,以种种反常行为引起统治者的注意。郦食其自号“高阳酒徒”,即是一例。另一方面,入世的狂人又鄙视世俗社会的庸俗之辈,不愿与之为伍,将自己高置于其上,处世孤傲,行为高标,甚至自以为是,孤芳自赏。但不论是怨世还是傲世,其用意只有一个,那就是努力使自己能够有为于世。 (四)放荡的狂人 所谓放荡,是指行为不检,不遵循正常的社会规范。荡者,已如前述,即“无所据,自放于礼法之外。”放荡的狂人最大的特点是不受社会共同的伦理规范的约束,在行为上毫无顾忌,完全依从自我情感行事。他们不是从现实的社会整体利益出发,而是只凭自我意识,把自我价值看得高于社会价值,因而在行为上自行其事,孤傲不群,蔑视一切,自我放纵,不考虑自我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影响,把自我与社会完全置于对立面上,不回避任何社会谴责,同样,任何社会谴责对他们也无济于事。他们所着意追求的是人生历程中生命的最大价值(标准由他们自己确定),生活的充分体验,自我情感的尽情宣泄。因此,他们豪情奔放,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在他们的感情中,过多的是对生命短暂的哀叹,对自由欢乐的向往,所以充满着生命的活力。 放荡的狂人与社会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与政治的冲突。任何统治者总是以自己的统治利益为重,对于社会上任何不利于自己统治的行为都要加以禁止。放荡的狂人以自我为中心,对于政治加以轻视,蔑视权贵,轻贱礼法,在自我情感的尽情宣泄中毫不顾及统治者的利益。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是因为政治权利对他们的排拒和对他们个性的压抑,以及因政治动乱而使他们对权力失去信心而厌恶权力。在这类狂人中,其实不乏治国救民的宏图伟志,但他们不愿受制于政治,不能低颜附势于权贵,因而嵇康有与山涛绝交之书,阮籍有大醉六十日拒婚于皇上之举,陶潜有不折腰于五斗小儿之说,李白有“低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之叹。所以,他们之中虽也有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寻找进仕之路者(如李白),但却不能真正成为统治阶层中的一员,而且有的还因与政治的冲突而断送了性命。 二是与正统思想的冲突。中国自汉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便成为历代的正统思想。历代统治者总是以实际上被改变了的儒家思想为治国治民之本。而放荡的狂人大多所接受的是道家思想,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处世行事,因而与正统的儒家思想发生矛盾,“讬好《老》《庄》”(嵇康《忧愤诗》),“不涉经学”(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不但言论上要“非汤武而薄周孔”,在行为上也蔑视儒家规范,对那些“惟法是修,惟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晋书·阮籍传》)的“正人君子”给予极大的嘲讽,骂之为“处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同上)的虱子。这些冲突,一方面使他们在思想上与正统思想更加格格不入,另一方面又使他们在行为上更增其狂放。 三是与传统伦理规范的冲突。这是历代狂人的共同特征,在放荡的狂人中尤为突出。放荡的狂人反社会要求尤为强烈,对社会伦理规范的破坏尤为坚决。他们以行为癫狂著称,不考虑任何社会后果,只要感到尽兴,什么行为都可以做出。不仅“任宠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嵇康《忧愤诗》),而且大胆提出“礼岂为我设”(《晋书·阮籍传》),因而能够“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放诞有傲世情”(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甚至“脱衣裸形于屋中。人见讥之,则答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世说新语·任诞》)这种勇于冲破世俗伦理常规,将真实的自我人格作为表现内容的大胆行为,是他们真性真情的真实表露。这些看起来癫狂放荡的行为,实际上包含着行为主体的内心痛苦,是他们与社会直接冲突的最明确的表白。放荡的狂人在“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指导下,以他们狂放的行为表白了他们对社会的抗议,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反社会行为者”。 (五)处江湖之远的狂人 处江湖之远,意即不在朝廷,没有一定的政治权力,不能把权力运用为实现自己理想抱负的工具。在中国古代狂人中,明显地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对权力的视而不见,十分淡漠,不仅不去积极地追求,反而即使别人亲自委托任用,也不接受,以显示自己的清高。另一种则是对权力的热切追求。这种追求不是为了把权力当成谋取私利的工具,而是作为实现有为于世理想的一种保证。处江湖之远的狂人属于后者,但又被统治者排斥于权力圈子之外。此类狂人是入世狂人的一种特殊类型。他们都曾使用过权力,并通过服务于朝廷展示过他们治国安邦的才能,在实现他们的社会理想过程中,曾享受过理想实现后的喜悦和满足。但由于他们最终不能适应君王的需要而被贬斥,远离朝廷,流落江湖。失落感在他们的心态中尤为强烈。 处江湖之远的狂人,最大的行为特征是他们虽处江湖之远,却心怀朝廷,心中充满着对国对民的忧虑。在忧患意识和责任感的驱使之下,他们时刻怀有一种为国为民尽力的热忱,对于那些把持朝政的庸官俗吏特别憎恶,对君王受佞臣蒙蔽十分不满。强烈的爱与憎交织在一起,却无法用行动来排解,于是便在流离中尽情地倾诉、吟唱,以诗歌来表达他们真诚而热切的内心世界。他们诉诸诗中的有理想和向往,有徘徊和彷徨,有深沉的叹惜和不尽的失望,有诚挚的表白和强烈的愤懑。这一切,不是为了别的,全部是为了他们所热爱的国家和人民,“长太息以掩涕兮,哀生民之多艰”(屈原《离骚》),“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他们所交付的是一颗赤诚的爱国爱民之心,而他们在流离中如癫似狂的行为则是他们内心痛苦的真实写照。 (六)一任性情的狂人 “性”是人的自然禀赋,“情”是人的欲望、情感、情绪等等,它们是与“理”、“法”对立冲突的。是任性情还是任理法,乃是困扰古往今来多少人的永恒之结。一任性情的狂人,其特点在于能把性与情提到首要位置,不加约束地任其自然发展,虽然并非要求所有的性情都得到满足,但却要求积郁胸中的炽烈情感能得到尽情渲泄。他们多为艺术中人,无论是对社会的不满还是对自己遭际的不平,他们大都将情感诉诸艺术,用艺术形式来展现丰富的内心情感世界。 在一任性情的艺术狂人中,性与情的满足与渲泄是不相同的,适性是为了尽情。他们大多行为怪癖,个性与常人迥异,从而显示出他们作为狂者的个性特征。心境澹泊,轻贱名利,鄙弃世俗,桀傲不顺,不遵礼法,使他们与世俗社会明显地隔离开来。宋米芾有洁癖,“至不与人同巾器”(《宋史·米芾传》),元倪瓒更有甚者,“盥濯不离手,俗客造庐,比去,必洗涤其处”(《明史·倪瓒传》),这种好洁成癖正是其厌恶俗世的明显例证。明祝允明“恶礼法士”(《明史·文苑传二·祝允明传》);徐谓则对当时所谓达官贵人、骚人墨客,“皆叱而奴之,耻不与交”(袁宏道《徐文长传》);清郑板桥“自愤激,自竖立,不苟同俗”(郑板桥《自叙》),愿“耳无俗声,眼无俗物,胸无俗事”(郑板桥《六十自寿联》),这些不与世俗为伍的行为,既显示出其脱俗颖立的个性特征,又反映了他们内心澹泊恬淡的思想追求。 但更能显示任性情的狂人的癫狂的还在于他们对于艺术的痴迷和在艺术中情感的渲泄。他们把对世俗的厌恶和内心的孤独,皆诉诸艺术。艺术上的癫狂真正体现了其狂的特征。唐张旭性“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新唐书·文艺传》),其“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万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韩愈《送高闲上人序》)。宋米芾见“无为州治有巨石,状奇丑,芾大喜曰:‘此足以当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为兄。”(《宋史·米芾传》)在痴情于艺术的狂人眼里,一块怪石竟也具有了巨大的艺术欣赏价值,真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表白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