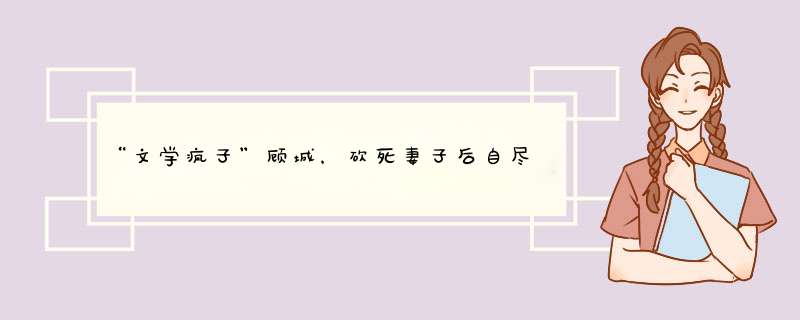
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一代人》。
这句话非常出名,几乎每个人都有所耳闻过,但你一定不知道这句话会是顾城写出来的,作为文学界的“疯子”,顾城一直都是文学界不太愿意提起的一个人,他就像一个长不大的男孩,醉心在自己的世界,当世界支离破碎时,最终走向了毁灭。
顾城在感情当中一直渴望这罗曼蒂克般的爱情,试图住在理想中的世外桃源,然而谢烨和英儿却又是现实的,在感情夹缝当中,顾城最终走上了杀妻之路。
顾城,1956年出生在北京一个诗人之家,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父亲文化熏陶下,顾城也走上了文学之路。
不过他的性格相对孤僻,他总是喜欢一个人独处,没有朋友,唯一的说话对象是大他几岁的姐姐,姐姐没空时,他就对着墙壁发呆,或者一个人讲故事,这让顾城将自己的内心封闭了起来。
后来被下放到农场,顾城更加不知道该怎么跟人相处了,1974年回到北京,此时的他已经18岁了,也需要开始养活自己了,即便无法跟人交往,他还是找了几份工作。
顾城当过搬运工、锯木工,借调编辑,他也开始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诗歌,影响力越来越大,顾城也成为了朦胧诗派主要代表人,诗歌拯救了他的人生,他因为诗歌开始跟人产生了联系。
1979年7月,顾城坐火车前往北京,在火车上遇到了同样喜欢诗歌的谢烨,他对她一见钟情,谢烨也喜欢上了顾城,两人双双坠入爱河,虽然两人的婚姻遭到了父母的反对,但两人还是排除万难走到了一起。
即便顾城不太会做家务,也不愿意跟长辈们来往,但是谢烨对顾城还是非常骄傲的,不过两人的幸福婚姻,并没有维持多久,英儿开始介入他们的生活。
英儿比起谢烨更加主动,热情,英儿一开始以朋友的身份接触两人,谢烨跟她讲了很多顾城的喜好,她便投其所好,时间长了顾城就沦陷在英儿的热情当中,谢烨虽然痛苦,但她并不想就此离开顾城。
顾城给不了英儿名分,英儿也不在乎,因为她当时跟刘湛秋正在交往,她似乎也只是图个一时新鲜。
1987年,顾城前往了德国参加了明斯特“国际诗歌节”,英儿也想出国,就跟着他一块定居国外,三个人在新西兰激流岛生活。
顾城喜欢这样的世外桃源。不用跟任何人打交道,每天就是写写诗、养养鸡,过得诗情画意,小“木耳”出生之后,渐渐打破了激流岛的平静生活,顾城并不喜欢这个儿子,他将“木耳”送了给姐姐抚养,他继续过着自己的生活。
然而英儿和谢烨有点接受不了,谢烨想要见自己的儿子,英儿想要更加充实的物质生活,她为了一张绿卡嫁给了德国老头,顾城十分悲痛,经常跟谢烨起冲突。谢烨也是准备跟他离婚,他也承受不了。
当顾城提出将“木耳”带回家时,谢烨只是对他说:一切都已经晚了。她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了。
1993年10月8日,两人就离婚的事,又起了争执,顾城不容谢烨破坏他的梦想王国,用斧头将她砍伤,顾城没有及时送她去医院,而是匆匆忙忙写下了遗书,随后找了一棵树上吊自杀了。
至于“木耳”一直由顾城的姐姐在照看,为了不让他重蹈覆辙,她并没有告诉他的父亲就是顾城,并有意引导他攻读理工科,现在他已经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工程师。
……《疯娘》很感人的文章,里面主人公的娘就是疯子,描写很细,几乎全篇都在写。
疯娘
23年前,有个年轻的女子流落到我们村,蓬头垢面,见人就傻笑,且毫不避讳地当众小便。因此,村里的媳妇们常对着那女子吐口水,有的媳妇还上前踹几脚,叫她“滚远些”。可她就是不走,依然傻笑着在村里转悠。
那时,我父亲已有35岁。他曾在石料场子干活被机器绞断了左手,又因家穷,一直没娶媳妇。奶奶见那女子还有几份姿色,就动了心思,决定收下她给我父亲做媳妇,等她给我 家“续上香火”后,再把她撵走。父亲虽老大不情愿,但看着家里这番光景,咬咬牙还是答应了。结果,父亲一分未花,就当了新郎。
娘生下我的时候,奶奶抱着我,瘪着没剩几颗牙的嘴,欣喜地说:“这疯婆娘,还给我生了个带把的孙子。”只是我一生下来,奶奶就把我抱走了,而且从不让娘靠近。
娘一直想抱抱我,多次在奶奶面前吃力地喊:“给,给我……”奶奶没理她。我那么小,像个肉嘟嘟,万一娘失手把我掉在地上怎么办?毕竟,娘是个疯子。每当娘有抱我的请求时,奶奶总瞪起眼睛训她:“你别想抱孩子,我不会给你的。要是我发现你偷抱了他,我就打死你。即使不打死,我也要把你撵走。”奶奶说这话时,没有半点儿含糊的意思。娘听懂了,满脸的惶恐,每次只是远远地看着我。尽管娘的奶胀得厉害,可我没能吃到娘的半口奶水,是奶奶一匙一匙把我喂大的。奶奶说娘的奶水里有“神经病”,要是传染给我就麻烦了。
那时,我家依然在贫困的泥潭里挣扎。特别是添了娘和我后,家里常常揭不开锅。奶奶决定把娘撵走,因为娘不但在家吃“闲饭”,时不时还惹是生非。
一天,奶奶煮了一大锅饭,亲手给娘添了一大碗,说:“媳妇儿,这个家太穷了,婆婆对不起你。你吃完这碗饭,就去找个富点儿的人家过日子,以后也不准来了,啊?”娘刚扒了一大团饭在口里,听了奶奶下的“逐客令”显得非常吃惊,一团饭就在嘴里凝滞了。娘望着奶奶怀中的我,口齿不清地哀叫:“不,不要……”奶奶猛地沉下脸,拿出威严的家长作风厉声吼到:“你这个疯婆娘,犟什么犟,犟下去没你的好果子吃。你本来就是到处流浪的,我收留了你两年了,你还要怎么样?吃完饭就走,听到没有?”说完奶奶从门后拿出一柄锄,像余太君的龙头杖似的往地上重重一磕,“咚”地发出一声响。娘吓了一大跳,怯怯地看着婆婆,又慢慢低下头去看面前的饭碗,有泪水落在白花花的米饭上。在逼视下,娘突然有个很奇怪的举动,她将碗中的饭分了一大半给另一只空碗,然后可怜巴巴地看着奶奶。
奶奶呆了,原来,娘是向奶奶表示,每餐只吃半碗饭,只求别赶她走。心仿佛被人狠狠揪了几把,奶奶也是女人,她的强硬态度也是装出来的。奶奶别过头,生生地将热泪憋了回去,然后重新板起了脸说:“快吃快吃,吃了快走。在我家你会饿死的。”娘似乎绝望了,连那半碗饭也没吃,朗朗跄跄地出了门,却长时间站在门前不走。奶奶硬着心肠说:“你走,你走,不要回头。天底下富裕人家多着呢!”娘反而走拢来,一双手伸向婆婆怀里,原来,娘想抱抱我。
奶奶忧郁了一下,还是将襁褓中的我递给了娘。娘第一次将我搂在怀里,咧开嘴笑了,笑得春风满面。奶奶却如临大敌,两手在我身下接着,生怕娘的疯劲一上来,将我像扔垃圾一样丢掉。娘抱我的时间不足三分钟,奶奶便迫不及待地将我夺了过去,然后转身进屋关上了门。
当我懵懵懂懂地晓事时,我才发现,除了我,别的小伙伴都有娘。我找父亲要,找奶奶要,他们说,你娘死了。可小伙伴却告诉我:“你娘是疯子,被你奶奶赶走了。”我便找奶奶扯皮,要她还我娘,还骂她是“狼外婆”,甚至将她端给我的饭菜泼了一地。那时我还没有“疯”的概念,只知道非常想念她,她长什么样?还活着吗?没想到,在我六岁那年,离家5年的娘居然回来了。
那天,几个小伙伴飞也似地跑来报信:“小树,快去看,你娘回来了,你的疯娘回来了。”我喜得屁颠屁颠的,撒腿就往外跑,父亲奶奶随着我也追了出来。这是我有记忆后第一次看到娘。她还是破衣烂衫,头发上还有些枯黄的碎草末,天知道是在那个草堆里过的夜。娘不敢进家门,却面对着我家,坐在村前稻场的石磙上,手里还拿着个脏兮兮的气球。当我和一群小伙伴站在她面前时,她急切地从我们中间搜寻她的儿子。娘终于盯住我,死死地盯住我,裂着嘴叫我:“小树……球……球”她站起来,不停地扬着手中的气球,讨好地往我怀里塞。我却一个劲儿地往后退。我大失所望,没想到我日思夜想的娘居然是这样一副形象。一个小伙伴在一旁起哄说:“小树,你现在知道疯子是什么样了吧?就是你娘这样的。”
我气愤地对小伙伴说:“她是你娘!你娘才是疯子,你娘才是这个样子。”我扭头就跑了。这个疯娘我不要了。奶奶和父亲却把娘领进了门。当年,奶奶撵走娘后,她的良心受到了拷问,随着一天天衰老,她的心再也硬不起来,所以主动留下了娘,而我老大不乐意,因为娘丢了我的面子。
我从没给娘好脸色看,从没跟她主动说过话,更没有喊她一声“娘”,我们之间的交流是以我“吼”为主,娘是绝不敢顶嘴的。
家里不能白养着娘,奶奶决定训练娘做些杂活。下地劳动时,奶奶就带着娘出去“观摩”,说不听话就要挨打。
过了些日子,奶奶以为娘已被自己训练得差不多了,就叫娘单独出去割猪草。没想到,娘只用了半小时就割了两筐“猪草”。奶奶一看,又急又慌,娘割的是人家田里正生浆拔穗的稻谷。奶奶气急败坏地骂她:“疯婆娘谷草不分……”奶奶正想着如何善后时,稻田的主人找来了,竟说是奶奶故意教唆的。奶奶火冒三丈,当着人家的面拿出根棒一下敲在娘的后腰上,说:“打死你这个疯婆娘,你给老娘滚远些……”
娘虽疯,疼还是知道的,她一跳一跳地躲着棒槌,口里不停地发出“别、别……”的哀号。最后,人家看不过眼,主动说“算了,我们不追究了。以后把她看严点就是……”这场风波平息后,娘歪在地上抽泣着。我鄙夷地对她说:“草和稻子都分不清,你真是个猪。”话音刚落,我的后脑勺挨了一巴掌,是奶奶打的。奶奶瞪着眼骂我:“小兔崽子,你怎么说话的?再这么着,她也是你娘啊!”我不屑地嘴一撇:“我没有这样的傻疯娘!”
“嗬,你真是越来越不象话了。看我不打你!”奶奶又举起巴掌,这时只见娘像弹簧一样从地上跳起,横在我和奶奶中间,娘指着自己的头,“打我、打我”地叫着。
我懂了,娘是叫奶奶打她,别打我。奶奶举在半空中的手颓然垂下,嘴里喃喃地说道:“这个疯婆娘,心里也知道疼爱自己的孩子啊!”我上学不久,父亲被邻村一位养鱼专业户请去守鱼池,每月能赚50元。娘仍然在奶奶的带领下出门干活,主要是打猪草,她没再惹什么大的乱子。
记得我读小学三年级饿一个冬日,天空突然下起了雨,奶奶让娘给我送雨伞。娘可能一路摔了好几跤,浑身像个泥猴似的,她站在教室的窗户旁望着我傻笑,口里还叫:“树……伞……”一些同学嘻嘻地笑,我如坐针毡,对娘恨得牙痒痒,恨她不识相,恨她给我丢人,更恨带头起哄的范嘉喜。当他还在夸张地模仿时,我抓起面前的文具盒,猛地向他砸过去,却被范嘉喜躲过了,他冲上前来掐住我的脖子,我俩撕打起来。我个子小,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被他轻易压在地上。这时,只听教室外传来“嗷”的一声长啸,娘像个大侠似地飞跑进来,一把抓起范嘉喜,拖到了屋外。都说疯子力气大,真是不假。娘双手将欺负我的范嘉喜举向半空,他吓得哭爹喊娘,一双胖乎乎的小腿在空中乱踢蹬。娘毫不理会,居然将他丢到了学校门口的水塘里,然后一脸漠然地走开了。
娘为我闯了大祸,她却像没事似的。在我面前,娘又恢复了一副怯怯的神态,讨好地看着我。我明白这就是母爱,即使神志不清,母爱也是清醒的,因为她的儿子遭到了别人的欺负。当时我情不自禁地叫了声:“娘!”这是我会说话以来第一次喊她。娘浑身一震,久久地看着我,然后像个孩子似的羞红了脸,咧了咧嘴,傻傻地笑了。那天,我们母子俩第一次共撑一把伞回家。我把这事跟奶奶说了,奶奶吓得跌倒在椅子上,连忙请人去把爸爸叫了回来。爸爸刚进屋,一群拿着刀棒的壮年男人闯进我家,不分青红皂白,先将锅碗瓢盆砸了个稀巴烂,家里像发生了九级地震。这都是范嘉喜家请来的人,范父恶狠狠地指着爸爸的鼻子说:“我儿子吓出了神经病,现在卫生院躺着。你家要不拿出1000块钱的医药费,我他妈一把火烧了你家的房子。”
1000块?爸爸每月才50块钱啊!看着杀气腾腾的范家人,爸爸的眼睛慢慢烧红了,他用非常恐怖的目光盯着娘,一只手飞快地解下腰间的皮带,劈头盖脸地向娘打去。一下又一下,娘像只惶惶偷生的老鼠,又像一只跑进死胡同的猎物,无助地跳着、躲着,她发出的凄厉声以及皮带抽在她身上发出的那种清脆的声响,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最后还是派出所所长赶来制止了爸爸施暴的手。派出所的调解结果是,双方互有损失,两不亏欠。谁在闹就抓谁!一帮人走后,爸看看满屋狼籍的锅碗碎片,又看看伤痕累累的娘,他突然将娘搂在怀里痛哭起来,说:“疯婆娘,不是我硬要打你,我要不打你,这事下不了地,咱们没钱赔人家啊。这都是家穷惹的祸!”爸又看着我说:“树儿,你一定要好好读书考大学。要不,咱们就这样被人欺负一辈子啊!”我懂事地点点头。
2000年夏,我以优异成绩考上了高中。积劳成疾的奶奶不幸去世,家里的日子更难了。恩施洲的民政局将我家列为特困家庭,每月补助40元钱,我所在的高中也适当减免了我的学杂费,我这才得以继续读下去。
由于是住读,学习又抓得紧,我很少回家。父亲依旧在为50元打工,为我送菜的担子就责无旁贷地落在娘身上。每次总是隔壁的婶婶帮忙为我抄好咸菜,然后交给娘送来。20公里的羊肠山路亏娘牢牢地记了下来,风雨无阻。也真是奇迹,凡是为儿子做的事,娘一点儿也不疯。除了母爱,我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在医学上应该怎么破译。
2003年4月27日,又是一个星期天,娘来了,不但为我送来了菜,还带来了十几个野鲜桃。我拿起一个,咬了一口,笑着问她:“挺甜的,哪来的?”娘说:“我……我摘的……”没想到娘还会摘野桃,我由衷地表扬她:“娘,您真是越来越能干了。”娘嘿嘿地笑了。
娘临走前,我照列叮嘱她注意安全,娘哦哦地应着。送走娘,我又扎进了高考前最后的复习中。第二天,我正在上课,婶婶匆匆地赶来学校,让老师将我喊出教室。婶婶问我娘送菜来没有,我说送了,她昨天就回去了。婶婶说:“没有,她到现在还没回家。”我心一紧,娘该不会走错道吧?可这条路她走了三年,照理不会错啊。婶婶问:“你娘没说什么?”我说没有,她给我带了十几个野鲜桃哩。婶婶两手一拍:“坏了坏了,可能就坏在这野鲜桃上。”婶婶问我请了假,我们沿着山路往回找,回家的路上确有几棵野桃树,桃树上稀稀拉拉地挂着几个桃子,因为长在峭壁上才得以保存下来。我们同时发现一棵桃树有枝丫折断的痕迹,树下是百丈深渊。婶婶看了看我说,“我们到峭壁底下去看看吧!”我说,“婶婶你别吓我……”婶婶不由分说,拉着我就往山谷里走……
娘静静地躺在谷底,周边是一些散落的桃子,她手里还紧紧攥着一个,身上的血早就凝固成了沉重的黑色。我悲痛得五脏俱裂,紧紧地抱住娘,说:“娘啊,我的苦命娘啊,儿悔不该说这桃子甜啊,是儿子要了你的命……娘啊,您活着没享一天福啊……”我将头贴在娘冰凉的脸上,哭得漫山遍野的石头都陪着我落泪……
2003年8月7日,在娘下葬后的第100天,湖北大学烫金的录取通知书穿过娘所走过的路,穿过那几株野桃树,穿过村前的稻场,径直“飞”进了我的家门。我把这份迟到的书信插在娘冷寂的坟头:“娘,儿出息了,您听到了吗?您可以含笑九泉了!”
外加这篇也是“疯娘”: 感恩的芦苇
程勤华
十五年前的一个冬天,一个疯女人抱着她的洋娃娃,在垃圾桶边发现了她,疯女人丢了手中的洋娃娃,一路傻笑,一路疯跑,一路胡言乱语,把她抱回了家。
奶奶发现疯女人怀里的洋娃娃,换成了一个小襁褓。费了好大劲,才把襁褓从疯女人手里夺过来。一条碎花的被子,裹着小猫一样瘦弱的女婴,女婴的脐带已发炎溃烂。她不会大声啼哭,偶尔哭一声,像北风在呜咽。
奶奶说:“罪过啊!罪过!留下这个小可怜吧,也可以让我那可怜的疯媳妇免些心焦。”疯女人一把抢过襁褓,唱着跳着,算是哄襁褓里的女婴睡觉。
疯女人原来是个聪明伶俐的农家女。有一天,她在场地前的桑树地里采桑叶,四岁的女儿抱着洋娃娃在场地上玩,只一眨眼的工夫,就找不见了女儿。她发了疯似地满村子找,全村人帮着她找了一天一夜,还报了警。后来,别人从她们家场地上的那口水井里,发现了她的女儿。女人不吃不喝好几天。人们再看见她时,人已疯了,蓬头垢面,逢人傻笑,抱着女儿的洋娃娃在村里到处游荡。
奶奶抱着女婴,去镇上的卫生院,给女婴的脐带消毒包扎。回来的路上,奶奶看到小河边上几棵叶子枯黄的芦苇,在北风中随风舞蹈。奶奶对襁褓中的女婴说:就叫你小苇吧,你一定要像芦苇一样,好好长大。
有了小苇,有很长一段时间,疯女人不再去外面游荡,人也安静了很多,经常抱着小苇傻傻地笑。后来小苇上了学,疯女人又开始满世界地疯跑了,不洗脸,不梳头,就往外面跑。有时几天不回家来,有时到小苇的学校,脸贴着玻璃窗,对着小苇傻傻地笑。因为有个疯妈,有的同学不愿搭理小苇。调皮的男同学经常用疯妈的名字来称呼小苇。
一次,疯女人偷吃了别人的东西,被人打得体无完肤。爸爸在外打工,奶奶瘫在床上,照顾疯妈的任务,理所当然地压在小苇孱弱的肩上。疯妈力气大,有时还打小苇,小苇根本管不住她的疯妈。奶奶对小苇说:随她去吧。小苇对奶奶说:她是我妈,没有她哪有我?我不管她谁管她?
从此,小苇上着课,心里惦记着她的疯妈:早上上学时,把疯妈锁在房间里,不知道是不是又砸了锁逃出去。想着想着,小苇就走神了,老师问小苇问题,小苇答不上来,老师生气地说:小苇,难道你也和你妈一个样?
小苇的眼中噙满泪水,她真想和同学老师们说:“疯妈不是我的亲妈!”这句话无数次在小苇的喉舌间打着转,小苇还是没有说出来。
十五岁的小苇,站在我的面前,出落得像一朵雨后的荷花。
小苇问我:姨,你是从城里来的吗?我说:是。小苇一双大而黑的眼睛,闪亮闪亮,忽闪了几下,欲言又止,离开了。
一会儿,小苇牵着她的疯娘来了。小苇一边静静地听我们讲话,一边给她的疯娘剥了一颗糖,掸掸疯娘身上的尘土,对她的疯娘说:“妈,你乖乖地坐在这里,有糖吃呢。”
看着小苇给疯妈剥糖的手,我的心被揪了起来。一个十五岁的少女,怎么可以有这样一双手?关节粗壮,皮肤粗糙,皲裂加上冻疮,手背又肿又紫。小苇的手上,记载了她生活的艰辛和磨砺啊。
我问小苇一个很残酷的问题:长大了,想过一种怎样的生活?小苇对我说:我要呆在娘的身边,照管着她。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疯娘不再乱跑,乖乖地呆在家里,我去附近的工厂打打工,每天能回家,给娘洗洗脸,梳梳头。
我忍不住再一次嘘唏。这个有着芦苇一样生命力的女孩,让我忍不住想起一句话: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这个叫小苇的女孩,不仅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而且还是一根懂得感恩的芦苇。
慵懒颓废的哼唱,声音不大,空灵的歌声,这首歌应当属于丧歌一类。我是通过邢晗铭才知道的这首歌。高潮处很好听,可能有人会觉得这类歌比较小众,上不了台面,但其实与众不同就会有市场,有需求。作词作曲都是许哲佩,有才华的唱作人,偏低音,不是靡靡之音,唱需要一定的嗓音和技巧,嗯。不疾不徐,歌手这么多年来都基本不温不火。词写的有意思,高潮处如涨潮,一浪一浪的冲击,一首悲伤的歌,可能也带有治愈,全程意识流。邢晗铭唱的不输原唱,情绪是不稳定的,暗流波涛汹涌,压抑着的都最终失控,催泪是有效果的。可能失恋后听也合适。
就像是作者的日记一样,编曲还不错,许哲佩就像是一个精灵歌手一样,看着也与众不同,内心世界是丰富的就够了。也可能是一个外向孤独症患者的表白,伪装很累的,负面情绪的反噬还是很可怕的。光明的背面是永远的黑暗。断断续续的吟唱,可以迅速拉近距离。许哲佩是台湾人,一路走来也陆陆续续得过一些奖项。有天真的儿童风格,单曲里充满着奇思妙想。天才在左,疯子在右。这首歌并不是她的第一首成名曲,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许哲佩,可以去听听《气球》和这首歌。抑郁症的单曲循环,有梦幻的成分在其中。可遇不可求的歌,让人失去希望也是笑着死去的。
她不喜欢你。侧著看和偷看是两回事,何况你已经告白了,她如果对你有意思也不必采用偷看的方式。加上前面的拒绝,现在远处侧看你应该是观察你后续的反应和动作而已,如果仔细观察她的眼神或表情,或许还能发现她可能对你的唾弃和不肖。这种情况放弃比较好,因为难度非常高。
狂人实际上并没有疯,只不过在其他愚昧的群众面前,他的所作所为让大家觉得他疯了。
他对于现在将被食于人的现实正在作出努力,他没有放弃去挖掘事实的真相并且作出分析,他不断想去改变,揭示自己的所见所闻。
狂人实际上是一个站在时代前列的反封建礼教、反封建家族制度的启蒙者。结果是被封建统治者迫害了。
扩展资料:
作品主旨
《狂人日记》整篇作品几乎都是狂人内心世界的表白。
狂人认为周围的人都在吃人,自己也要被迫吃人或被人吃。狂人被关起来,拒绝家人送来的饭菜,拒绝被医治,一直劝说周围人不要再吃人。直到最后狂人发现,也许自己就曾在无意中吃过自己妹妹的肉。绝望中的狂人发出“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的呼喊。
在小说的开头“狂人日记序”中写道:“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狂人病体痊愈暗示的是其他人在精神上的不正常。在众人眼中,狂人是一个患有迫害狂恐惧症的病人,在狂人眼中,其他人才是吃人的人。这样的不同角度和立场,深刻的揭示了病态社会的悲哀。
小说通过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的形象暗示,将矛头直接指向保守的传统文化。“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是狂人对未来社会的幻想和规划;“我也未必没有吃过妹子的肉”,这是狂人对自我的评价和反思,也是自己对前途的绝望,充满了自我忏悔的精神。
小说的结尾“救救孩子”的呼喊是狂人为建立新的社会而进行实践性的探索。在狂人看来,现实中的人都是有罪的,只有孩子是纯洁的,没有受到吃人文化的污染。
因此要想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就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孩子们身上,就只能赶紧救救孩子。《狂人日记》不仅表现了彻底批判封建礼教的勇气,而且还表现了鲁迅“忧愤深广”的人道主义情怀,表现了他以文艺创作来改造社会和人生的总体精神。
--狂人日记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表白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