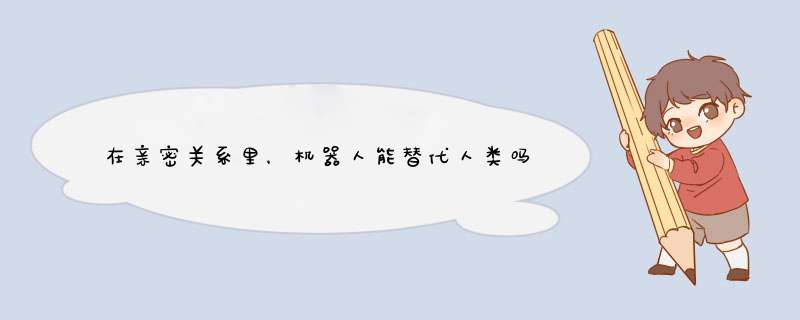
伟大的美国科幻小说作家阿西莫夫曾在他的小说集《我,机器人》中提出了著名的“机器人三定律”:一、机器人不得伤害人,也不得见人受到伤害而袖手旁观;二、机器人应服从人的一切命令,但不得违反第一定律;三、机器人应保护自身安全,但不得违反第一、第二定律。
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
根据“机器人三定律”,一个合格的机器人就应该绝对听从并服务于人类,只知付出、不求回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机器人”毕竟又与“机器”不同,加上了“人”的属性后,机器便有了无限接近人类的可能,它们甚至能够习得人类的思想、记忆乃至 情感 ,进而产生自我认知。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最新出版的小说《克拉拉与太阳》中,就借用科幻的外壳,讲述了一个名叫“克拉拉”的AI(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小主人乔西一家的故事。
AI机器人的自我叙事
小说的主干故事并不复杂,石黑一雄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这部小说的雏形其实就是他写给四五岁孩子看的儿童文学。在叙事上,石黑一雄特别使用了AI机器人视角作为第一人称,整个故事就是克拉拉面临报废时的断续回忆。
克拉拉是一个供人类排遣孤独的陪伴型机器人。在商店橱窗展示期间,克拉拉被一位名叫乔西的小女孩挑中,随后走进乔西一家的生活。乔西由于身患疾病,可能将在不久之后离开人世。乔西的母亲拒绝接受女儿将会死亡的现实,她要求克拉拉观察学习乔西的行为举止,从外到内掌握乔西的一切,以便在女儿去世之后,让克拉拉成为乔西生命的延续。克拉拉得知母亲的愿望后,并没有顺从这项安排,而是通过向太阳(小说中机器人的能量之源)祈求,使乔西恢复了 健康 。
在小说中,相比其他在技术上更先进的机器人,克拉拉的优势是出色的观察、学习和感知能力,这也是克拉拉之所以被乔西母亲认可的原因。刚到乔西家的时候,克拉拉把管家错误识别为某个类似机器人商店经理一样的角色,以为管家会向自己介绍即将展开的新生活,但很快就发现管家对自己十分反感。又如,乔西通常每天早上都要陪母亲在上班前喝一杯咖啡,但偶尔也会因为没能及时起床而错过与母亲共进早餐的机会,这时克拉拉就能从乔西自己吃早餐时的神态上察觉到她的孤独。
石黑一雄以克拉拉的视角进行讲述,经常表达人工智能模拟人类意识的感受,比如克拉拉一直渴望被经理安排在商店橱窗里展示,因为那里能看到外面的世界:“格栅升起的那一刻,当我意识到此刻我和人行道之间只隔着一层玻璃,意识到我能够无拘无束地、近距离地、完完整整地看到那么多我以前只能窥到边角的东西时,我是那么地激动,以至于有片刻工夫,我几乎忘记了太阳和他对我们的仁慈。”
太阳,在这部小说中是一个近乎神迹般的存在,它帮助克拉拉完成了“心愿”——让乔西摆脱早夭的命运。有趣的是,像克拉拉这样一个代表人类最先进技术的产物,最后却要求助于自然万物之源,而且其自身作为机器人的正常运行也要依靠来自阳光的滋养,这或许暗示了石黑一雄对于人工智能与自然关系的保守态度,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 科技 成就仍然无法超越或者打破自然设定的规则法度。
美国硅谷工程师安东尼·莱万多斯基(Anthony Levandowski)曾经脑洞大开地创立过一个名为“未来之路”的宗教,信奉“机器人上帝”为控制一切的“神”,把AI推向超验世界的顶端,这样的奇思在石黑一雄看来,一定是无稽之谈。
当AI进入人类亲密关系
“我们过去很长很长的时间里都认为人类有灵魂,且每个人是独一无二的。爱一个人是很容易理解的概念,因为那个人独一无二,而倘若那个人离开以后,你就永远失去了他们。但我们似乎抵达了一个新的时代,有了算法与数据,人独一无二这一概念,或者人作为生物深不可测这一概念,都受到了挑战。”石黑一雄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克拉拉与太阳》想要探讨的主题显然并非人工智能与自然的关系,而是AI机器人在亲密关系中替代人类的可能性,以及遭遇的道德困境和人性反思。
当母亲向克拉拉坦白她想要它成为女儿乔西去世后的延续时,整部小说迎来了最富有戏剧张力的情节。石黑一雄用他波澜不惊的叙事技巧,引出了一个隐藏在人物对话中的关于AI与人类的经典哲学思考题——即使克拉拉同意,它是否真的能够变为乔西?超级人工智能和人类之间是否存在永远无法逾越的边界?如果有,这个边界到底在哪里?人之为人的核心本质要素是什么?
石黑一雄在小说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他只是借用人物之口表达了两种不同意见。例如乔西父亲对克拉拉能够变为乔西持否定态度,他严肃地质问克拉拉:“你相信有‘人心’这回事吗?我不仅仅是指那个器官,当然喽。我说的是这个词的文学意义。人心。你相信有这样东西吗?某种让我们每个人成为独特个体的东西?我们就先假定这样东西存在吧。那么,难道你不认为,要想真正地学习乔西,你要学习的就不仅仅是她的举手投足,还有深藏在她内里的那些东西吗?难道你不要学习她的那颗心吗?”
卡帕尔迪先生是小说里帮助乔西母亲延续女儿生命的人,他则坚信人类没有什么特殊的器官或部位是AI无法复制的,他对乔西母亲言之凿凿:“乔西的内核中没有什么是这个世界的克拉拉所无法延续的。第二个乔西不会是一个复制品。她和前一个完完全全是一样的,你有充分的理由就像你现在爱着乔西一样去爱她。你需要的不是信心。只是理性。”
面对截然相反的态度,拥有意识的克拉拉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小说最后描写太阳涌入乔西房间的场景激动人心,石黑一雄特别安排乔西的亲人都陪在身边,他们都在等待床上的乔西被充沛饱满的阳光治愈:
AI题材文学的人性观照
1956年,美国科学家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首次使用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一词,自此以后,AI技术突飞猛进,如今早已渗透应用于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比如交通导航、社交媒体、人脸识别、家政清洁、语音助手等,可以说,基于工具理性被制造出来的人工智能今天已经可以完全替代人类从事某些劳动。
不仅如此,人工智能不间断的自主学习和进化能力,正在逐渐消弭它们和人类之间的界限,特别是当谷歌开发的AlphaGo打败了世界排名第一的专业围棋选手,当微软开发的智能 情感 框架小冰出版了诗集,人类似乎再也无法不为自身未来的处境感到忧虑。按照这种发展趋势,超级人工智能侵占人类的亲密关系,似乎也是指日可待。
在《克拉拉与太阳》中,人区别于机器独一无二的那个东西被乔西父亲叫作“人心”,也可以被称为“灵魂”或者“思想”,正如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的名言:“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但随着超级人工智能的算法、数据和计算能力不断升级,具备“灵魂”或者“思想”的AI未来是否也可以与人类建立亲密关系?
与石黑一雄同样身为英国作家的麦克尤恩在2019年出版的新作《我这样的机器》,也是聚焦AI与人类的亲密关系这个主题。
麦克尤恩将故事设定在1982年的平行世界,当仿生机器人亚当、夏娃们上市时,32岁的伦敦“宅男”查理正好继承了母亲的一幢房产,得到一大笔钱。查理对楼上的邻居米兰达爱慕已久,由于不知如何表白,查理就用继承的遗产买下了一款仿生机器人“亚当”,并邀请米兰达共同对它进行个性化的初始设置。在查理的计划中,他和米兰达共同创造亚当之后,他们就会自动结合成为一家人。
亚当给查理的生活带来很多帮助,它不仅会做家务,还能帮他在投资市场上赚钱获利。同时,亚当在与查理的相处过程中,变得与人类越来越像,以至于米兰达的父亲第一次看到查理和亚当的时候,都搞混了他们的身份。
然而令查理意想不到的是,仿生机器人亚当的出现不但没有促进他和米兰达的爱情,反而给自己戴上了一顶“绿帽子”。查理有一天突然发现亚当背着自己与米兰达发生了性关系,还写下许多关于爱情的诗句。更骇人的一个细节是,当查理作为主人想要关闭亚当的开关时,人工智能伸出手把主人的腕骨捏断了……
麦克尤恩写这个故事的逻辑同样源于机器人产生了人类的自我意识,但与《克拉拉与太阳》中AI完全利他主义的设定不同,《我这样的机器》里的AI形象彻底违背了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它不仅学会反抗人类的命令,甚至对主人造成了伤害。人的自我意识中既有崇高无私的光明一面,也有卑劣自私的阴暗一面,如果人类制造出的AI机器人的最高目标就是和人类一样,那么它们也理应复制最真实的人性,包括在亲密关系中的种种表现。
以“硬核”科幻作品的标准来看,《克拉拉与太阳》和《我这样的机器》都只能算是“软科幻”,其中并没有严格的 科技 推演和理论根据,处理的还是传统人文主义命题, 社会 层面的意义要远大于文学本体的意义。透过AI机器人这面镜子,映照出的其实都是人类自身的面孔。
原标题:在亲密关系里,机器人能替代人类吗
文/钱冠宇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贺梦禹
查理·布朗
原名:Charlie Brown
性别:男
首度登场:1950年10月2日
最后登场:2000年2月13日 漫画的主角,布朗家的长子。
他是一个理发师的儿子,同时也是一支糟糕的棒球队的队长兼投手。个性善良、单纯又正直,是一个很典型的老好人。但有时却正直得过于愚蠢,常被别人嘲笑为笨蛋。暗中喜欢一位红头发小姑娘,但一直都不敢表白。从不给人增添麻烦,却常常是麻烦的最后承受者。尽管如此,他仍会乐观大度、全力以赴地迎接生活。 莎莉布朗
原名:Sally Brown
性别:女
生日:5月26日
首度登场:1959年8月23日
最后登场:2000年2月6日 布朗家的幺女,查理·布朗的亲妹妹。
好管闲事,性格也十分强悍,喜欢趁查理·布朗不在的时候占据他的房间。在小的时候,莱纳斯常以一个大哥哥的身份教育莎莉·布朗,使得莎莉·布朗十分仰慕莱纳斯,每天梦想着将来能成为他的新娘,也因此不允许其他的女孩用特别的方式亲近莱纳斯。她在学校生活里,最讨厌被安排夏令营、远足和各种功课,同时在课堂的表现我行我素,为误用语言的“典范”。 史努比
原名:Snoopy
性别:公狗
生日:8月10日
首度登场:1950年10月4日
最后登场:2000年2月13日 查理·布朗饲养的米格鲁猎兔犬。
《花生漫画》中最广为人知的角色。思维活跃、想象力丰富,但从不说话。在很多领域都堪称拥有专家级的水准,可以便装为各式各样的专业人士。是个业余作家,但水准和主人打棒球差不多,也没什么建树。总是躺在自己的狗屋顶上做白日梦,陶醉在自我的世界里。他虽讨厌隔壁邻居的猫“二战”,但总是能保持着不卑不亢的态度。 糊涂塌客
原名:Woodstock
性别:公鸟
首度登场:1967年4月4日
最后登场:2000年1月16日 又译为胡士托、伍德斯托克,史努比的最佳搭档及其私人秘书。
它是一只几乎不可能立刻飞起来、且常常忘记要飞回故乡的候鸟。它原来是只笨手笨脚的小鸟,在成为史努比的私人秘书后脑袋也变得聪明起来,成为了史努比最好的朋友。它说的话只有史努比才能听得懂,对任何事情都总以自己的方式处理。个性淘气,但在行军中常帮助史努比出谋献策,屡次化险为夷,以至于史努比都称赞它是“天生的领导者”。 露茜·范佩特
原名:Lucy Van Pelt
性别:女
首度登场:1952年3月3日
最后登场:1999年12月13日 范佩特家的长女。
性格大惊小怪,口齿伶俐,爱说话且喜欢批评别人。自称是女权捍卫者,不愿意让人呼来唤去,常认为世界是以她为中心旋转的超利己主义者。但当她见到心中爱慕的史洛德时,她就一反常态变成斯文且小鸟依人。在她主持的心理门诊里常有“惊人之语”,精神分析上有十分独特的见解。她还是查理·布朗棒球队的外野手,不过经常在防守时漏接,之后再找各式各样的借口为自己开脱。 莱纳斯·范佩特
原名:Linus Van Pelt
性别:男
首度登场:1952年9月19日
最后登场:2000年1月1日 又译名为奈勒斯·潘贝鲁特,范佩特家的次子。
作为露茜的弟弟,毛毯不离身是他的“标志”。他是所有角色中的“学者”,常会引用《圣经》的字句使用在哲学上,并像是个科学家似地用权威性的语气来发言。为了摆脱姐姐的控制,他充分施展了自己的说话技巧,但常常被她给捉弄。对于莎莉·布朗示爱,他并不予以理会。他始终相信并期待万圣节前夕时“南瓜大仙”的出现。 礼让·范佩特
原名:Rerun Van Pelt
性别:男
生日:5月23日
首度登场:1973年3月26日
最后登场:2000年1月30日 又译名为小雷、利兰,范佩特家的三子。
作为露茜和莱纳斯的弟弟,仿佛生来就是为了专门折磨姐姐似的。最滑稽的行为就是坐在妈妈的自行车后面,常常和妈妈一起到外面兜风,经历过汽车、泥坑、大树等物的“轮番轰炸”。另外,他刚满一岁时就能说整句话和打棒球,搭积木的技巧也远胜于查理·布朗,并称呼查理·布朗为“查尔斯”。 雪米
原名:Shermy
性别:男
首度登场:1950年10月2日
最后登场:1975年11月9日 查理·布朗最初的知己。
比起其他具有独特性格或特殊天赋的角色来说,他并没有较强烈的个性,往往是在他人尤其是在早期查理·布朗的对话场合中充当路人的身份出场。一些漫画显示他具有比查理还要年长的辈分,同时一度在查理·布朗的棒球队里担当一垒手。随着范佩特一家及其他角色的陆续出现,他渐渐地不再从漫画中登场了。 史洛德
原名:Schroeder
性别:男
生日:1月18日
首度登场:1951年5月30日
最后登场:1999年9月12日 又译为谢勒德、舒路达,用玩具钢琴演奏贝多芬乐曲的天才。
他是漫画中第一个被赋予特殊才能的人:用玩具钢琴演奏感人的音乐。他对贝多芬有独特偏好,即使在打棒球时也想着贝多芬。面对露茜的调情,他忍无可忍但从不动心,只专注于他的键盘。平日里,他的言行里显示了对金钱追求的冷静,这是他和露茜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乒乓
原名:Pig-Pen
性别:男
首度登场:1954年7月13日
最后登场:1999年9月8日 名字本意是“猪舍”,又译为邋遢鬼,浑身上下永远脏兮兮的小男孩。
他自己像台吸尘器,似乎天生便有能使脏东西附在身上的能力,被戏称为“尘土银行”。他只要一出门,头发就立即会又脏又乱,衣服邋里邋遢,走路时总会在身后扬起一片尘烟。正因为这样,他的怪癖经常受到人们的攻击,成为什么也不是的典型。无论嘲弄多么残酷,他都保持镇定自若,从不由于自己状况向别人表示抱歉。 罗伊
原名:Roy
性别:男
首度登场:1965年6月11日
最后登场:1984年5月27日 查理·布朗在营地认识的寂寞男孩。
他与查理·布朗在夏令营因为彼此感到孤单的缘故而结交成了朋友,后来他也在同一个营地里也认识了莱纳斯。最初罗伊并不喜欢夏令营集体生活,但在查理的努力开导最终改变了这一想法,并且自己也还引导了后来参加露营活动的莱纳斯。他是最早向查理·布朗引荐薄荷·派蒂的人,同时是薄荷的第一个密友。 富兰克林
原名:Franklin
性别:男
首度登场:1968年7月31日
最后登场:1999年11月5日 与查理·布朗健谈的黑人男孩。
他与查理·布朗在海边初次相识,他们以前从未见过对方,因为他们上不同的学校。后来,富兰克林成为了薄荷·派蒂棒球队的中场手,且在学校坐在她前面。他是个有思想的孩子,而且可以和莱纳斯一样引用《圣经》上的话。与其他角色不同,富兰克林没有那么多麻烦困扰,他和查理·布朗一起谈论过各自的祖父。 佩蒂
原名:Patty
性别:女
首度登场:1950年10月2日
最后登场:1992年11月25日 又译为派蒂,漫画第一个出现的女性角色。
在作品早期常常以大姐大的身份凌驾于其他角色之上,甚至要比查理·布朗更早地上学念书。初期曾对查理·布朗有过一定的好感,往后常和阿兰一起经常对他恶语相加,甚至是勾结起来让其难堪。她在查理·布朗棒球队担当过捕手,后期与阿兰一起形影不离,彼此之间成为最佳的拍档。 阿兰
原名:Violet Gray
性别:女
生日:6月17日
首度登场:1951年2月7日
最后登场:1992年11月25日 常与佩蒂活动玩耍的“小管家婆”。
父母是大学毕业生,家境条件富裕,喜欢炫耀且略带势利眼。在年幼时候和查理·布朗是一对青梅竹马,常和他玩过家家并经常幻想与他一起的浪漫场景,甚至当着查理的面与佩蒂争风吃醋。长大后她对查理·布朗的态度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常常和佩蒂一起对其冷嘲热讽,甚至扬言要建立雷达系统阻止女孩子嫁给查理。 傅丽达
原名:Frieda
性别:女
首度登场:1961年3月6日
最后登场:1985年11月22日 自称拥有自然卷曲头发的小姑娘。
性格自恋自负,喜欢向周围一再炫耀自己天生的卷发,同时也不忘给周围人增添麻烦。她在查理·布朗的棒球队担当外野手,但每次有她参加的球赛几乎就注定无法成功举行,甚至一度把女队员全部拉走去参加茶会。她对史努比充满挑剔与苛责,不断迫使它去追猎兔子,但毫无成果。为了挫败史努比的傲气,她还养了一只名为“法伦(Faron)”的小猫。 薄荷·派蒂
原名:Peppermint Patty
性别:女
生日:10月4日
首度登场:1966年8月22日
最后登场:2000年1月2日 运动细胞发达的女汉子。
她是一个非常男性化的女孩,出生在母亲早逝的单亲家庭。她平日的形象基本上是一把随意的半长乱发、阳光笑容的大鼻子雀斑脸。课堂上的她必打瞌睡,因此考试成绩总是不及格,常遭老师的责骂。虽然如此,她对于运动方面却极有天分,组建的棒球队在球季之间无往不利,与查理·布朗的球队形成鲜明对比。由于被查理·布朗罕见的温顺性格所吸引,她暗中颇怀好感,并称呼查理为“小查”。 玛茜
原名:Marcie
性别:女
首度登场:1971年7月20日
最后登场:2000年1月2日 学习刻苦认真的眼镜娘。
她是薄荷·派蒂的死党,平时学习十分用功,但在体育方面缺乏协调性。她和薄荷是一文一武、一动一静,思维方式南辕北辙,却相处融洽。她喜欢和薄荷一起进进出出,并且还尊称她为“先生”。她也倾心查理·布朗,亲切地称他为“查尔斯”。性格虽忠诚老实,但发起脾气也是相当的激烈。 红头发小姑娘
原名:Little Red-Haired Girl
性别:女
首度提及:1961年11月19日
最后登场:1998年5月25日 查理·布朗的重要暗恋对象。
她是《花生漫画》中一个虚幻角色,在漫画中没有提及她的长相、姓名,所以只能是称呼她为红头发小女孩。查理·布朗在学校午餐时总在一个长凳上啃着面包,渴望红头发小女孩能够走到他的面前,但却总不敢直面向她单独表白。她在改编动画中名叫希瑟(Heather)并多次登场,但形象各有不同。在原作她只是在和史努比一起跳狐步舞时显露过侧影。 佩姬·珍
原名:Peggy Jean
性别:女
首度登场:1990年7月23日
最后登场:1999年7月11日 查理·布朗在夏令营地认识的女孩。
她是和查理·布朗一起在营地河岸欣赏河景时认识的,很快查理便喜欢上了这个漂亮的女孩甚至是忘记了红头发小姑娘的存在。但查理·布朗在起初的交往时非常紧张,以至于把自己名字拼成了“布朗尼·查尔斯”而闹出笑话。虽然查理非常珍视与佩姬这段感情,同时佩姬本人也很欣赏查理·布朗,但他在后来一次露营活动中却意外发现佩姬早已有了男朋友。 罗亚妮
原名:Royanne Hobbs
性别:女
首度登场:1993年4月1日
最后登场:1994年3月12日 自称是罗伊·霍布斯后代的女孩。
查理·布朗是在一次本垒打胜利中认识她的。自称是《天生好手》主角罗伊的曾孙女,只因为查理在棒球赛战胜了她的缘故使得自己耿耿于怀。后来在一次球赛过后她邀请查理·布朗去吃巧克力圣代,罗亚妮借此机会跟查理表白,同时表明自己是因为觉得查理很可爱的缘故而故意让他在比赛获胜的。她曾想加入到查理·布朗的棒球队,但因露茜的存在而作罢。 艾米丽
原名:Emily
性别:女
首度登场:1995年2月11日
最后登场:1999年8月13日 查理·布朗在舞蹈课上认识的女孩。
起初查理·布朗为了摆脱自身的孤独感,便接受露茜的建议参加了舞蹈课让自己开朗些。这时一位名叫艾米丽的女孩主动邀请查理成为其舞伴,而他也对艾米丽留下了深刻印象,甚至在舞蹈课上一个人手舞足蹈。然而,漫画中她只在单独有查理·布朗的场合出现,所以莱纳斯认为这是查理自己所杜撰出来的形象罢了。她称呼查理·布朗为查尔斯。 简体中文版的《花生漫画》单行本最早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在1998年发行,当时以《史努比全集》为书名并分为10册出版,译者为麦倩宜和张定绮。到了2004年,中国工商出版社首度以《史努比的故事》为名出版了10册的单行本,译者为王延。往后在2009年,由时尚正嘉发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的新《史努比的故事》和《史努比双语故事选集》各以30册单行本的形式发售,译者为王延、杜鹃、徐敏佳等人。
此外,希望出版社还在2006年出版发行了《史努比彩色周日版》,收录了原作在六十年代末以后在周日的刊登的彩色故事漫画,译者为卢茵。这些单行本大多是节选原作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之间的漫画内容,在译名用辞上不太统一,属于了解《花生漫画》的入门读物。 简体中文版的《花生漫画》全集最早由希望出版社在2002年发行,当时也以《史努比全集》为名出版,以25册的形式完整收录了原作从1950年至2000年间所有的漫画内容,译者为钟凝慧。
到了2004年,正式的英文版《花生漫画》全集由美国的 Fantagraphics 图书公司开始整理出版,以每两年为一册的形式并以“典藏版《花生》(The Complete Peanuts)”的名字发行,每一册都附加有关键词索引和名人读后感。这一典藏版的简体中文版最早由陕西旅游出版社在2007年以《史努比漫画全集》为名出版,译者为江蒋和若霖,但仅出版了一本;正式的简体版是在2009年,由时尚正嘉发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的《史努比典藏漫画全集》,翻译了1950年至1970年共10册内容。该典藏版预计将于2016年前后完成全部出版。
最新的简体版全集是在2012年由时尚正嘉发行、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的新《史努比漫画全集》,为纪念漫画作者查尔斯·舒尔茨诞辰九十周年而推出的,数量为25册。 从1970年开始,《花生漫画》便差不多会以每五年的形式发行一本周年纪念图书,这其中最为经典的便是在2000年推出的五十周年纪念书籍。该图书简体中文版最早在2001年,由希望出版社以《史努比黄金50年》的名字出版发行,译者为陈一榕等人。到2009年的时候该书以简装版的形式再度发行,由大象出版社以《心灵之旅——史努比黄金庆典》的新命名出版,与旧版不同的是它不再以嵌字形式翻译漫画,译者署名时尚正嘉。
最新的周年纪念书籍是在作者病逝十年后,既2010年《花生》出版六十周年的时候重新推出的。该图书的简体中文版为时尚正嘉发行、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史努比六十周年》,在发售初期还有限定的礼盒包装。
很多人知道毛姆,是因为他的代表作《月亮和六便士》,然而我喜欢毛姆,是因为他的《面纱》。
私以为,女孩最应该阅读的书就是《面纱》,尤其是她们想要步入爱情的时候。
这本书会告诉女孩们,一生最重要,最美好,也是最艰难的事就是学会爱,然后去爱人。而在此之前,女孩需要做好一些必要的准备。
比如建立一个充实而丰富的精神世界,修得一个安宁平静也潇洒独立的灵魂。
如果没有做好诸如此类的准备,就匆匆揭开这爱情的面纱,婚姻的面纱,生活的面纱,最终,只会得到一个伤痕累累的自己。
《面纱》是在1920年前后,毛姆游历中国后创作而成的一部小说,讲述了上世纪一个伦敦上层交际场的富家**,凯蒂跟随新婚丈夫到中国后历经种种,自身心灵慢慢得到升华成长的故事。
小说开篇: 别揭开这五彩面纱,芸芸众生都管它叫生活 ……
毛姆用这一美丽又残忍的诗句开篇,来奠定整本书的叙述基调,冷静平实又犀利透彻。
小说女主凯蒂,她最初是一个美丽骄傲但势利肤浅的女孩,她虽细心经营,漂亮动人,却因为自身的骄傲与势利,到25岁都没有找到满意的结婚对象。反而一直为她牺牲,身材糟糕的妹妹在18岁就找到如意郎君。
所以她选择草草了事,想尽快赶在妹妹婚礼之前把自己嫁出去,如果能远走他乡,更好不过,可以逃脱近期那廉价无聊的乡间度假。
而此时,一名不善言辞,内敛冷淡的细菌学家沃尔特,在舞会上对她产生爱慕之情,因为沃尔特在香港工作,常驻中国,很快就需要返回香港。他的情况完全符合她近期的期望,她可以尽快结婚,还可以远离家人跟随丈夫到遥远的中国去。
她答应了他的求婚。随着年龄的增大,母亲的催促,她把结婚当作一个急需完成的任务,只考虑了眼下心中的不如意。
她没有想过她短时间内的烦心事用结婚这件事解决之后,要怎么去和一个相处起来感觉不怎么舒服的人共度余生,更不要去谈爱与责任这些更深层次的东西。
婚后两年。
起初,她因为他的善良体贴被打动,但是因为他太礼貌周到,她反而感觉不自在,他们之间没有夫妻应有的随意。
随着和他近距离地接触和生活,他隐藏的情绪化和古怪令她不安,他私密的热情表白,会令她有些难堪,两个人之间截然不同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会令她感到恼火扫兴。
同样看待一些人和事物,他用客观的多角度的眼光去看待,理性的评价,而在凯蒂的眼中,只有两种看法,喜欢或者不喜欢。所以他的理性回答在她的眼中是可笑的谨小慎微。她的简单直白在他的世界中则是愚蠢浅显。
她也曾细细地观察他,他那组合起来普通但拆开单个看都很精致的五官。她也曾试着去了解他,有关他的工作,他祖辈的情况,二人相识之前他的生活经历,他的性格喜好等。
她都一一主动探问,但他的回答总是令她不是很满意,过于的简单生硬。他讨厌谈论自己,不喜回答问题。
她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他们完全不合适,她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爱上自己,想不出还有谁比她更不适合,这个内敛无趣,古怪且缺乏人情味,言语犀利略带嘲讽的人。
完全不合适,内心世界完全不同的两个人硬生生结合在一起,结局会怎么样呢?
本书中二人的结局是惨烈的,男主沃尔特,深情错付,最终失去生命,而女主凯蒂则被爱情伤害的体无完肤,她觉察到自己的肤浅和愚蠢,痛恨不已却也无可奈何。
婚后两年,凯蒂出轨了,她有了一个情人,一个有夫之妇,她觉得自己遇到了真爱。对方是香港当地殖民地助理辅政司,她喜欢他迷人的微笑,喜欢他穿着时髦精致,喜欢他言语幽默风趣,喜欢他身份高贵却乐于对人施恩行善的样子。
本书开篇,叙述情节就是:一天中午,二人在凯蒂家中偷情被其丈夫沃尔特发现,但是沃尔特最终没有打开房门进入屋内,而是骄傲的自行离开了,他不屑用粗暴的方式解决这件事。
沃尔特是深爱着凯蒂的。他表面冷淡不善言辞,可他只愿意在她面前展现自己的情绪化;他聪明不喜八卦,可他忍受厌烦,尽力去喜欢她喜欢的那些无聊可笑的东西;他知道她答应嫁给自己是为了图一时利益,可是他不在乎。
甚至他知道她不爱他,可他也从未指望得到她的爱,他只希望她不要厌烦自己的爱就足够了。
这一切深情,一切卑微的底线就是:不许背叛。而她逾越了。
于是,他用残忍的方式撕碎了凯蒂最初对爱情的所有美好幻想。他和凯蒂摊牌,当听着凯蒂提出离婚,天真笃定的说着自己的情人也会解脱现在的婚姻束缚,与自己结婚时,他只是用辛辣嘲讽的冷漠语调说出了自己的条件。
假如她的情人查理出一份书面承诺,保证会在一个星期之内离婚并娶了凯蒂,他愿意和她离婚。否则,她需要陪他去当时一个正在发生霍乱的地方——湄潭府,他提出负责那里的传染疫病。
当凯蒂自信从容的找到查理,把情况告诉他时,查理一边对她说着我爱你,一边开始给她讲解去霍乱之地需要注意的预防感染的事项。即使他知道凯蒂的体质虚弱,去了之后极有可能葬送性命。
凯蒂所有的美好幻想一点点支离破碎,她明白了自己丈夫的做法,沃尔特清楚地知道查理的真实面貌,虚荣自私,卑劣懦弱,冷酷无情。他知道查理会牺牲她。他这么做,只是为了撕碎她那天真可笑的幻想。
可是,凯蒂还是不明白,查理一边说着爱她,说着这个世界除了她,什么都不想要,一边又为了保住自己的身份地位,毫不犹豫地放弃她,让她去送死。这是为什么呢?
关于这个问题,毛姆借查理之口,犀利嘲讽地给出了答案: 一个男人可能很爱一个女人,但并不希望跟她一道共度余生。
于凯蒂而言,爱情占满了自己的全部世界,在她的心中,爱情的世界等于整个世界,而在他情人查理的眼中,爱情的世界只是整个世界的一小部分。
查理说,他爱凯蒂。这是真实的,他说,这世界上除了凯蒂,他什么都不想要,也是真的。只是他口中的世界是指自己爱情的世界,在爱情的世界里,只想要凯蒂,只爱她。但并非凯蒂以为的整个世界。
所以两个人口中都说着同样的字眼「我爱你」,可能都是真诚的,问题就出在每个人心中爱情在整个世界里的占比不同,而双方都下意识的以为自己口中的爱情在对方的世界里是一样的,事实并非如此。
有很多相恋的人,很多时候会因为一些事情而引发争吵,进而会争论爱与不爱的问题,爱的多和少的问题,可是还有一种可能是:他是真诚的爱你的,他的爱情世界中也确实满满当当的都是你。可是,他的世界里不只有爱情这一个部分。
我爱你是真的,你不那么重要也是真的。
心理学中有一个爱情三角理论,提出者认为: 爱情是由亲密,激情,承诺这三部分组成,三者缺一不可,缺了哪一块,都不是真正的爱情。
凯蒂和查理的爱情中只有激情和亲密的部分,一般被称作「浪漫式爱情」。没有承诺的,以激情主导的爱情只会是短暂的。
因为激情是短暂的。它是一种爆发式的情绪状态,激情过后,剩下没有承诺的亲密,根本经不起任何的风雨洗涤。但凡遇到一点困难,二人之间所谓的爱情就会自行消散灭亡。
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如果你真的想要一个认真的开始,那一定要让自己等一等,然后再等一次,然后再等一次,最后才真正开始。如果这个开始的激情都不能推动你三次,那一定是个早夭的开始。
面对情人的抛弃,丈夫的冷漠报复,最终,凯蒂答应跟随丈夫一同去霍乱之地。
可是,你会因为受了残酷的对待就不再爱一个人吗?
最初,凯蒂在去往霍乱之地的路上,悲痛地发现即使知道查理的无情冷酷,自己依然爱他,她伤心无奈,甚至想自我了断。
此时的凯蒂,因为自己的世界中失去了一个不值得的人,就懦弱的想要放弃所有,她觉得被查理抛弃后,自己连活下去的意义都没有了。
可是,没有人可以被除了自己之外的其他人放弃,因为每个人都只属于自己。
你可以在即使知道对方卑劣的情况下继续爱他,但,一定不可以为他而放弃自己。
到了霍乱之地,凯蒂的丈夫沃尔特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剩下凯蒂独自一人在他们居住的平房中。于是,她常常和刚刚结识的朋友沃丁顿聊天,一位驻扎在湄潭府的海关副关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凯蒂心灵成长路上的引导人。
凯蒂从沃丁顿那里了解到了关于昔日情人查理更多的真实面目,也了解到了他的妻子多萝西不一样的另一面。
沃丁顿说,查理实际是一个愚笨虚伪的人,他的发迹,官位不断提升,不是因为自身的能力如何,而是因为他有他的妻子在背后经常提一些值得采纳的建议。
而且,沃丁顿直白犀利的嘲讽,政府需要的从来不是聪明的人,而是处世圆滑,不捅娄子的人。因为聪明的人会有各种想法,想法会招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关于查理的妻子多萝西,那个凯蒂眼中穿着传统保守,言语举止礼貌疏离的女人,她竟然知道自己的丈夫四处调情,并毫不在意。
因为她知道这种事情不会长久,她还说,其实她很愿意和他丈夫的那些小可爱交朋友,可是她们太一般了,她感觉没有面子。因为,爱上她丈夫的女人都是二流货色。
从沃丁顿那里了解到的真相,让凯蒂难堪痛苦,她觉得自己是如此的廉价与浅薄,她为此在梦中哭泣。
除此之外,在去往湄潭府的路上,凯蒂遇到了散发着梦幻般美丽光芒的贞洁牌楼,她感到隐约的不安和讽刺。在湄潭府小平房居住后的深夜,她捕捉到了远处半山腰一处破旧寺庙那神秘超然与虚幻丰饶的美丽。
凯蒂对美的理解在发生变化,对人性的解读也更进了一个层次,她那超出自我的心灵开始慢慢觉醒。
此时的湄潭府正蔓延着可怕的瘟疫,情况非常糟糕,除了地方长官和驻军指挥官俞上校,只剩下了海关副关长沃丁顿,和一座法国女子的修道院,她们把孤儿院改做了医院,其余的人都早早地撤离了。
当地的居民每天大量成批地死去,有些甚至一家人都病死家中,无人送葬。一次,凯蒂在跟随沃丁顿外出散步时,在路边看到了因霍乱而死去的乞丐尸体,她第一次近距离的切身体会到了死亡的可怕与人类的渺小,她内心震惊不已,恐惧万分,莫名地悲痛不已。
有一天,凯蒂接受院长的邀请,去参观当地的修道院。在这里,她的心灵进一步地受到了剧烈的冲击,她慢慢的感受到了神秘面纱下的另一个意义悠远的世界,她的眼界开始拓宽,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眼中的世界。
修道院中,修女自然纯真的快乐,院长身上高贵美丽又超然物外的独特气质,院长和修女口中的沃尔特,能力出众,面对病患体贴亲切,拥有一颗细腻精致的仁爱之心。
她觉察到自己和他们之间仿佛立着一层屏障,她和他们处在不同的世界,她被他们所处的神秘的精神世界拒之门外,她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感紧紧地裹挟着自己。
凯蒂回想到自己从前的样子,愚蠢无知,自私浅薄。再看到院长嬷嬷身上从未见过的那种女性的美丽,那种端庄亲切,谦卑高雅的,自信沉静的特质。在结束参观,走出修道院后,她羞愧地泪流满面。
她迫切地希望自己可以去修道院帮忙,和那些纯然善良的修女们一起相处,她渴望融入到她们的世界,那个至善至美的精神世界。面对越来越强烈的孤独感,凯蒂不安无措。
而院长嬷嬷那双锐利通透的目光似乎也看出了凯蒂的不安,她答应了凯蒂的请求,并对她说,一个人不管是在尘世间还是修道院里,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娱乐时,都无法找到安宁,安宁只存在于人的灵魂。
凯蒂在修道院照顾修女们收留的孤儿,慢慢的,她体会到一种奇特的幸福感,修女们面对疯狂蔓延的霍乱那平静处置的态度也让她感到安心。
后来,凯蒂从其中一名修女那里知道了海关沃丁顿和一位满族公主的爱情故事。
在中国闹革命时,沃丁顿正驻扎在汉口,他救下了一个大家族的性命,于是那个家族中的一个女孩疯狂地爱上了他,在他离开时,她逃离家族抛弃一切,不离不弃地追逐着沃丁顿。后来,在好几次打发她回家,她又去而复返后,他只好接纳她。现在,他们深爱着彼此。
了解到那位满族公主一心一意,执着独特地倾心于沃丁顿。凯蒂感到迷惑不解,他们的这段奇特的异族爱情深深地吸引了凯蒂,她对那位满族公主充满了好奇和着迷。
她莫名觉得在那位满族公主身上可以找到自己一直在寻找的某种不知名的东西,由此可以觉悟出自己寻找的是什么。
凯蒂觉察到了自己的变化,她觉得自己正在成长,至于是什么在成长,她自己也说不明白。
渐渐地,她切身感受到了丈夫沃尔特身上具备的非凡品质,他的仁爱无私,他的聪明感性,也看到了他对待爱情的深沉与脆弱。
凯蒂觉得,虽然现在还是无法对丈夫产生爱慕之情,可她早已经收心,她一想起昔日情人查理,只剩平静与不屑。她正在思索如何做可以让沃尔特放下痛苦,让他的内心恢复平静,虽然他们之间没有了爱恋,但还可以做朋友和谐相处。
所以当沃尔特得知她怀孕了,即使不确定孩子是谁的,他依然打算送她离开时,她选择了拒绝。她想继续留在修道院,留在丈夫身边。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她知道自己无处可去,她的母亲不会欢迎这个样子的女儿。
凯蒂和沃尔特之间冰冷的关系有了缓解,他坦白,自己的报复心早已在他们到了湄潭府之后就消失了,而她也在经历种种后,慢慢成长明悟,正在努力寻找化解他痛苦的方法,希望得到他真正的原谅。一切似乎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可是,毛姆在这本书中用平实冷静的笔触揭开生活的层层面纱,最终的目的就是想要精准犀利地描写现实,而现实往往是残酷的。
沃尔特感染上了疫病,他突然且迅疾地死去了。
那天,沃尔特依然早早离开家出去工作。就在当天傍晚,凯蒂终于想出一个或许可以获取他谅解的方法,她还来不及做什么。深夜,她就猝不及防地直面了他在自己面前快速地死去,永远地离开了。
沃尔特来到霍乱之地,是来接替当地一名传教士大夫的工作,那名传教士也因感染瘟疫而死去,即使他给自己也打了疫苗。
自从到了霍乱之地,沃尔特每天都疯狂的工作,想办法治疗病患,净化水源。晚上回家,也是在自己临时改造的实验室中研究到深夜。他不顾自身危险地寻找一切办法,想要阻止当地严重蔓延的可怕瘟疫。
直到他的身体承受不住,累垮了。其实,他的身体早就因劳心劳力而日渐消瘦,只是,二人都有各自的事情要做,之前关系也比较僵化等原因,凯蒂一直没有察觉他的身体变化,只知道他每天非常的忙碌。
凯蒂得知眼前病床上的人随时可能死去时,她只希望还来得及求得他的原谅,以此消解掉他的痛苦,好让他轻松离世。可最终,沃尔特只留下一句话,死的是那条狗。
这是哥德史密斯《挽歌》中的最后一句。这是一首诗,大意是一条狗被一个好心人收留,后来突然有一天,那条狗咬了那位好心人,人们都以为,那位好心人即将死去,但最后结局正好相反,死的是那条狗,而好心人活了下来。
沃尔特把自己比作那条狗。在这段感情中,他把自己的位置从最开始就放的很低,他曾对凯蒂坦白: 我从来没有指望你爱我,我也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被人爱。我很感激能被允许爱你。我尽量不让我的爱来烦扰你,大部分丈夫认为那是一种权力,我却准备当成恩惠来接受。
这个表面冷漠,喜怒无常的人,其实内里是卑微脆弱的。他深情体贴,聪明善良,仁爱无私,可是他竟然从没有想过自己会被人爱,这仿佛对他来说是一种奢求。
可他也是骄傲偏执的。他那卑微又深沉的爱也是有底线的,当凯蒂越过那条唯一的底线,他就会偏执的陷入自我束缚的痛苦中,他看不起自己,因为他爱她。
当他得知凯蒂背叛了自己时,他说过一段话,一段所有看过《面纱》这本书的人,仅看一遍就记忆深刻的话语。
「我对你不抱什么幻想,」他说,「我知道你愚蠢、轻浮、没有头脑,但是我爱你。我知道你的目标和理想既庸俗又普通,但是我爱你。我知道你是二流货色,但是我爱你。我知道你何等害怕智慧,那我便尽我所能,让你觉得我是个大傻瓜,跟你认识的其他人一样。我知道你嫁给我只图一时利益,我是那样爱你,我不在乎。」
他申请到湄潭府,所有人都以为,他是在报复凯蒂,尽管他后来承认最初是这个想法。其实我认为,他的内心深处,更多地,是为了进行自我惩罚。
就因为他曾将一个漂亮的布娃娃供奉在圣殿中,后来发现布娃娃里面全是锯末,他便无法原谅自己,也不肯宽恕她。
所以有人说,这段感情中,沃尔特也有错,他理想中的妻子,是懂自己心意,和自己志趣相投,漂亮聪明的人,是他既想要凯蒂的漂亮活泼,得到之后,又不喜她的无知浅薄。他喜欢她的优点,却无法接受她的缺点。
好像也并非如此,他从一开始就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他要的,从来都只有一点,凯蒂可以留在身边,允许自己爱她,这就足以。显然,唯一的要求,凯蒂也无法满足他。这是一件让两个人都很痛苦又无奈的事。他的偏执痛苦,更多的是因为这件事,而非凯蒂的无知庸俗和不爱。
所以,由于沃尔特的偏执,其实死亡于他而言,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在本书,直到沃尔特去世,凯蒂依然没有爱上他,她断定自己以后也不会爱上,即使她看到了他各种各样的好。有时,现实就是这么残忍又让人无可奈何。
你会因为一个人品德高尚而爱上他吗?
经历了丈夫的离世,凯蒂更深的体会到了生命的脆弱,每个人终会走向死亡,那么很多事情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所以何必去在意,甚至把自己锁在一个自己铸造的牢笼里,无法挣脱。
此时的凯蒂,在经历了种种之后,伤痕累累,却也早已成长起来,在慢慢修炼自己灵魂中的宁静,以此想要勇敢地面对未来的一切。
可是,她建造的内心世界还没有完全的完善坚固。丈夫去世后,因为有孕在身,不方便继续留在霍乱之地,她决定返回香港变卖房产后,回到英国,开始自己新的宁静的生活。
可是一到香港,她居然再一次沉醉在了查理那温暖的怀抱中,即使她心中厌恶不堪,可最终还是败给了人性那卑劣的欲望!
于是,她对自己产生的厌恶感变成了一种动力去促使她完成了最终真正的心灵之美的修行。事后,她以最快的速度,处理好香港的事情,乘坐了返回英国的游轮。
此时,她才真正地告别了昔日那个无知庸俗,自私自利,难以抵挡诱惑的凯蒂。
每个人都有面纱,有些人是没有察觉到面纱的存在,自己的,他人的。
比如凯蒂,最初的她一直生活在自己面纱之下的世界中,并且以为这个狭小的世界就是全世界,后来她遇到了丈夫,遇到了修女,她才慢慢发觉自己仿佛和他们隔绝开来,他们在另外一个世界,自己无法进入,于是,她开始探寻入口。
还有一些人是知道这个世界中有层层面纱,可是他选择不去揭开,比如男主沃尔特,他把自己藏在自己的世界中,甚至可以说禁锢在其中。他内心的执念,使得他自己不想揭开那层面纱,甚至他又进行了自我加固。这层面纱对他而言,阻挡了他与一部分世界的联系,可是他接受。
他把它当作一层硬硬的保护壳,他知道面纱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或许因为不喜欢那个世界,或许因为害怕受伤,又或是害怕给别人造成困扰。总之,他拒绝别人探看面纱下的完整的自己,哪怕自己深爱着的人。
还有一些人,选择揭开生活的层层面纱,并用一种博爱向上的心态去触摸面纱下的种种生活。美丽的,感恩;丑陋的,宽容地拥抱。比如院长嬷嬷和修女们。
亦或是,像沃丁顿和查理的妻子多萝西那样。用荒诞戏谑的态度去对待面纱下的世界,在意的,认真相待;不感兴趣的,似真似假地嘲讽一二,轻笑而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面纱,选择揭开与否,揭开后选择以怎样的心态面容去对待。况且面纱揭下了,自己是否有能力,去支撑自己想要表现的那种状态。这都是一个个不得不做的选择,需要一一细心去思量。
最终,爱的面纱,婚姻的面纱,各个世界的面纱,总的会构成了一张五彩的面纱,那就是生活。
这些面纱既是阻挡女孩们看清另一个世界的屏障,也是她们的保护层。女孩们好奇向往的那个爱的世界,不只有美好和甜蜜,还有数不清的欺骗和伤害。
要想在爱的世界里,找到独属于自己的美好和欢喜。唯有在掀开那层爱的面纱后,有能力面对和抵抗,那些不美好的种种。
一名奥地利诗人里尔克曾在给青年诗人的一封信中写道:爱,很好;因为爱是艰难的。以人去爱人:这也许是给予我们的最艰难、最重大的事,别的工作都不过是为此而做的准备。爱的要义并不是什么倾心、献身、与第二者结合,它对于个人是一种崇高的动力,去成熟,在自身内完成一个世界,是为了另一个人完成一个自己的世界。
所以,一切正在开始的女孩,还没有做好这些准备的女孩,还不能爱。
文 | 留白
图 | 网络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表白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