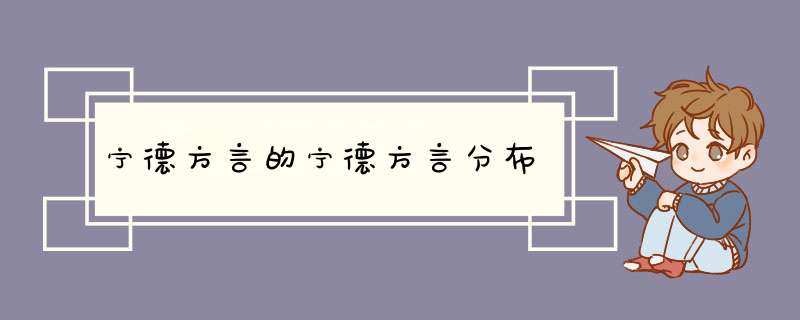
市汉语方言分布情况比较复杂。根据方言内部的异同,宁德方言属闽海方言群中以福州话为代表的闽东方言区。古田、屏南两县属于闽东南次方言南区;蕉城区和福安、周宁、柘荣、寿宁、福鼎、霞浦等7县(市),属于闽东北次方言区。闽东方言福州话在南片区可自由交际,北片区各市(县、区)人也能基本听懂福州话。福安话在北片区的周宁、寿宁、柘荣等县可自由交际,蕉城、霞浦、福鼎人也能基本听懂福安话。
闽东方言北片区各县(市)没有像福州话韵母那样的变韵现象。词汇方面,北片区有些词语说法与南片区不同,如“肚子”叫“腹肚”,“小孩”叫“傀儡”,“饿”叫“饥”,“生孩子”叫“生囝”或“饲囝”,“种猪”叫“猪狮”等。语法方面,北片区有些地方句子结构特殊,如寿宁话把“你先走”说成“你走先”,寿宁话、柘荣话把“再吃一碗”说成“食碗凑”或“食碗添”,福安话把“客人”叫“人客”,“母鸡”叫“鸡母”,“斗笠”叫“笠斗”,“前头”叫“头前”等。这是该方言特有的倒装现象,“热闹”称作“闹热”。这样的提法很常见。在口音方面, 福安话语音浊重,语调偏硬;福鼎话轻清、绵软。
同时,境内有一些地方形成区外方言岛。霞浦县的三沙镇和水门、牙城两个乡镇的部分村庄,以及下浒、柏洋、长春等乡镇的少数村庄(共约7万多人)讲闽南话;福鼎市的沙埕、前岐、店下、白琳、点头、贯岭、箭山、叠石等乡镇的部分村庄(共13万多人)讲闽南话;还有柘荣县的乍洋乡和东源乡的少数村庄(约500多人)也讲闽南话。全地区约有21万多人讲闽南话。闽南话是宁德境内第三大方言。还有少数地区形成汀州话(客家话)方言岛和莆仙话方言岛。古田县风都镇的后溪、珠洋两个村(约5000人)讲客家话,霞浦县柏洋乡利埕村福鼎楼自然村300多人)讲客家话,柘荣县城郊倒龙山村( 100多人)讲客家话。此外,福安市社口镇首笕村、福鼎市磻溪镇赤溪村和点头镇观洋村以及寿宁县西南部边境个别自然村讲客家话。霞浦县溪南镇岱屿村(100多人)讲莆仙话;福安市下白石部分村庄(400多人)讲莆仙话;福鼎市沙坦镇澳腰等村庄(数百人)讲莆仙话。
闽东方言南片的福州话在境内少数地方形成方言岛。福鼎市秦屿镇(1 5万多人)全讲福州话;霞浦县的海岛乡和柏洋乡的北岐村、长春镇的计米村(共1 4万多人)讲福州活。
由于历史原因和地理条件,一些县的边界村庄讲邻县方言。屏南县西北部岭下乡的富竹、上楼、东峰、上梨洋、葛畲等村因与闽北的建瓯市毗邻而讲属于闽北方言系统的建瓯话,周宁县的西北部与政和县接壤的泗桥乡的赤岩、洋尾、洋尾弄、吴厝坑、吴厝坪和纯池镇的前溪等村庄讲属于闽北方言系统的政和话;霞浦县的东冲半岛与罗源县的鉴江镇隔海相望,该县北壁乡的东冲、上岐、下岐 个村讲罗源话。
四五十岁以下的宁德人,多半从小受双语教育长大,能熟练使用两种甚至三种互相不能交流的语言。这在五六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那个时候,外地人进入乡村与民众交流,还要有翻译。
随着社会交往的扩大,宁德人①与外部世界交流越来越多。即便在穷乡僻壤,操普通话交流也没有什么问题的。完全听不懂北方话的人,已很少数。在城区,普通话的普及程度更高。大体上是这么几种情况:从家庭内部来说,二十至三十岁的年青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交流,基本上以普通话为主;二十岁来岁下以的青年与其父母之间的交流,城区以普通话为主,农村以方言为主;同辈年青人之间的交流,城区亦以普通话为主,在乡村普通话也占很大成份。有趣的是,年青人经常使用一种方言与普通话混合的语言。在社会交流方面,不同行业之间方言与普通话的使用范围、频度也是不一样的。较大规模的服务网点的从业人员,基本操普通话;公务员、事业单位从业人员的公务活动、与服务对象交流,基本操普通话。有趣的是,在世俗生活如婚丧喜庆的场合,凡属发布公共信息——如婚礼主持用语——用普通话,而亲友之间的交流,则大部分用方言。这种状态,几乎只在不到四十年内的时间形成。其原因相当简单,就是普通话的的社会交际功能的影响以及移民对宁德当地方言的冲击。
宁德话属于闽东语的一个分支。相对于普通话来说,宁德话可称之为一种“复杂”的语言。汉语字音,由声母、韵母、声调组成。现代汉语声母二十一,韵母三十,声调四声。宁德话声母少,为十五个,其中还包括了直接以韵母为头的零声母,然而韵母却有七十八个之多。并且,声调有七个。除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之外,还有阴入、阳入、阴去阳去之分。因此,用现代拼音法或普通话读音的汉字来注释宁德发音,有许多字音是没有办法表达出来的。声调中的入声使用也十分有趣。年青人听老辈人说普通话,常有入声。如中国之“国”、“打铁”之“铁”等等。
今宁德有后垅村、里垅;有前乾寮(楼)、寮(楼)下村。此外,清人笔记中有“越人指瀑布为氵示”一句①。宁德多处地名称“氵示”,如城关的“南氵示”、八都的“氵示头”等等,这毫无疑义地证明了宁德方言中包含了古百越人的语言成份。至于物件,如宁德人将孛荠读之为“姆梨”,与广东粤语“马蹄”相去不远。有专家考证,曾遍布于古代南方的百越人,将“地”读为“ma”,将“果子”读为“θī”。孛荠正是“地下的果子”。如此说来,宁德话中的这个词汇,存在时间已有二三千年以上的时间了。
以至于口语中宁德方言包含的古越语成份更多。如宁德方言“招手”,读音为衣呀切②,与壮语音近义同;说“傻”,读音近似额安切,与壮语音同义合;“滑落”,读为了噢切,与壮语音义俱同。“滚动”,宁德人一种读音为了因切,与壮语音近义同;“泡沫”,宁德方言读音为扑欧切,与壮语同;“舔”,读音为了椰切,与侗、壮、水族语音近义同。此类对比,在《福建方言》中例举不少。并非英文石头(STONE)、小米(MILLET)、倒(DOWN)等与普通话偶有音义相近之孤证可比,是有科学根据的。
在汉人陆续进入并最终成为福建这片荒蛮土地的主人之前,福建受北面的吴与西面的楚的影响。而吴与楚“同音共律、同气共俗”(《吴越春秋》),因此,在福州(宁德)方言中,有着古楚、吴语的痕迹。由于部分古楚、吴语记录于一些古籍中,专家里就能从中将之搜寻出来,给我们这些能够掌握方言的人,打开一扇饶有兴趣的通往久远历史的门。
古楚音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夥”,读为胡火切。这个字的用法见于《史记》。当司马迁用文学的方法记录一位楚人老乡与陈涉见面的情景时,这样的描述他的满口乡音:“夥颐,涉之为王沈沈矣!”意为,不得了啦,陈涉当王气象不得了啦。“夥”,在其中,指得是“多”,“真多”的意思。而这种说法与语音,就基本上保留在了宁德方言之中。宁德人现在问别人“有多少东西”,语音就是“若夥”?“没有多少”,就是“冇若夥”。
其他见诸于古书中的记载的古楚音,还有指叶子为“箬”;指单独、一为“蜀”;指“击打”为“扌忽”;指丢在一边为“拌”,指深且静的水为“潭”;都可以在宁德方言中找到近似甚至完全相同的读音与用法。
古吴音中最为明显的就是“侬”、“澳”的读音与用法。现在吴地——苏州等地已将“侬”变成了“你”,而宁德人现在仍称“人”为“侬”、保持着古藉相同的用法。有水的弯处称“澳”,也仅见于福建。如宁德的三都澳。再如岙村、南澳、城澳等地名。在这些地方,我们都能看到“水湾”的地形地貌。还有指食物纳热汤中一沸而出为“渫”(入声,思阿切);指衣袖为“衤宛”,长袖称“长宛”;称水中浮萍为“漂”(音皮优切)等等。
还有一些在古藉中为楚吴通用的词,如“氵靓”( 读音近似 七焉切,去声),指寒冷;“木希”指瓠瓢(读音为喝椰切,阴平),宁德人早年常的“鲎 木希”等。更值得一提的是“濑”字。此字读为“赖”,现代汉语中少用,在字典中标明白是“水大”的意思。但是古书中表明此为吴音,指“水流湍急,滩”的意思。在宁德,就有两个相当有名的地方与之有关。一是大泽溪。在现在的宁德人方言中,此溪仍然称为“大濑溪”。此溪水势湍急,溪谷中多为急流与危岩暴露,与古代吴人用法,是一致的。据说,七十年代初,水电站测绘人员在此测量时,嫌地名太土,改“濑”为“泽”。似乎“濑”字太可怕。其实,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不够。另外,霍童溪上多处地名称为“某某濑”,如九都云气(红贵)的“乌猪濑”。在当地人的称呼中,读音为“乌猪罗”。 这“罗”宁德人专指急流处,河中碛滩,与古人的用法是完全一致的。而“罗”,可能就是“濑”的变异。
“解(读音近似国际音标中的e)不”。这“解”在宁德方言中的常用程度甚至影响了具有一定文字水平的人。因为“解”相当于今口语中的“会”、“能”等,因此有的记者进行采访时,常提问“这个技术你会掌握得了吗”、“这个字你会写得来吗”等不太规范的句子。还有“去”,在唐诗宋词中用法是表示动作的完成,而非表示趋向。如“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中的“去”,是“了”的意思。这在宁德人中,是很容易理解的。宁德人言及一事了结或不可收拾,如失手将碗打碎,往往惊呼“去”、“去”,正是古风遗韵。此外,还可一提的是“故”字。唐宋时口语为“还、尚、犹”的意思,这在宁德方言中,仍然大量地使用。如宁德牧童唱山歌戏谑对方,“白鹤岭头一丘田,除来除去除一爿,若无叔伯(我)养你大,你大大小小故(尚、还)不知”。这“故”字,在宁德人所谓“盘诗”中,大量存在,几乎成了衬字。还有“底(何,哪)”、“底(里面)”、“着(在、应当)”、“斗(竞相)”、“泥(软缠硬磨之软缠)”等等,这些词都能在唐诗宋词中找到出处,以现代汉语来解释,十分费解,而以福州(宁德)方言为母语的人,却很容易在方言中找到相应的解释,读来兴趣盎然①。
从方言中寻找古音古词,是精深的学问。这涉及多门学科,特别需要对十分晦涩的古代音韵著作进行研究,通读大量古人之诗词、笔记等等。即使如此,古代著作也并非记录了闽人当时全部的音、词,因此,当今在宁德方言中,仍然还有大量的读音词汇、甚至还语法结构与现代汉语不同,在宁德方言中有太多不解之迷。这正是有兴趣者寻幽探秘的对象
专家认为。宁德方言,定型于唐末与宋初。然而,这种语言,并不等于王审知等河南光洲固始的数千军人以及此后大批中原民众商绅带来的语言。由这些统治者或上层人物所带来的语言,不可能完全替代原来民间早已通行的语言。并且在他们到来之前,数百年里,福建已接受了中原汉人的一次次进入。据《福建通史》,中原汉人进入闽地,大规模的就有三次,时间跨度为公元六世纪到十世纪,而此前此后零星的“渗入”,则难以计数。然而,唐末这次中原人的进入,对闽东语系的影响巨大,以至于有人认为现在的福州话可以与当今之河南固始县的语言相通,前往河南实地验证等等。孰不知今之中原人所操语言与千年前相比,早已变化;而王审知等所操语言亦融于福州当时语言之中,经过交汇,才形成现在以福州话为标准音的方言区。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表白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