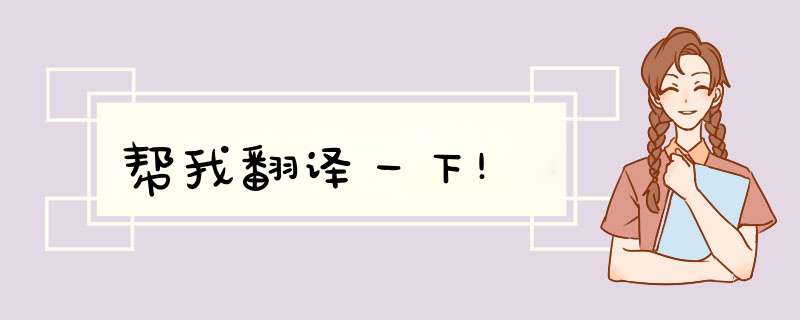
文天祥的诗歌创作,以宋恭帝德佑元年(1275)为界,一般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这前后两个阶段的诗歌创作,内容很不相同,艺术成就也是极不平衡的。1979年出版的黄兰波先生的《文天祥诗选》是文天祥著作的第一部选注本。在该书《前言》部分,黄先生论道:“……(文天祥)德�以前,是一般文人的诗,虽然期间有一些诗篇是抒发忧时之感或揭露统治集团的矛盾和罪恶的;但更多的却是题咏匆匆、酬应琐琐之作,无以别于一般调弄笔墨的文人之所为。从德�起,每篇有一定的内容,大都皆有为而发。它的内容,便是热爱祖国的思想和斗争到底的决心,它的有为而发,便是为了坚定抗战意志,鼓舞抗战情绪”。这一看法,是较为客观、中肯的,它大体代表了学界一种普遍的意见。
令我们感兴趣的是,文天祥的前期诗歌创作何以大都是“题咏匆匆、酬应琐琐”之作其内容的贫弱和艺术上的平庸,与他的状元出身及当时的一般社会风气有无关系尤为重要的是,这一现象蕴含着怎样的学理等等,都值得我们认真探究。钱钟书先生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出版的《宋诗选注》中,就曾对文天祥前期诗歌作过精辟分析:他在这个时期里的作品可以说全部都是草率平庸的,为相面、算命、卜卦等人做的诗比例上大得使我们吃惊。比他早三年中状元的姚勉的《雪坡山人稿》里有同样的情形,大约那些人都要找状元来替他们做广告(参看《翰墨大全》壬集卷八任翔龙《沁园春·赠谈命许文》:“办一封好纸,觅状元诗。”)这段论述,为我们进一步的探研提供了更为宽阔的视野。可以断言,文天祥前期诗歌创作与当时一般的社会风气及其状元出身有着密切关系。
《文山先生全集》(四部丛刊本)一、二卷所收录的诗歌,即为其前期所作。单从诗题,就可看出其题赠应酬的无聊之作多得令人吃惊。据统计,在前期创作的二百四十多首诗中,赠相士、谈命、太极数、银可数、丹士、道士,及庆吊、送别、题赠等应酬之作,就占去五分之三。(黄兰波《文天祥诗选·前言》)
唐宋时期,随着进士科的抬头,形成了崇尚进士,尤其是状元的社会风气,这就构成了文天祥前期诗歌创作的宏观科举文化背景。北宋文学家尹洙曾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千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也不可及也。”(宋·田况《儒林公议》卷上)这里,以“状元登第”与“恢复幽蓟”相比,甚而荣宠有以过之,可见状元之尊。这种状元之尊,还远及异邦。
《宋史》卷三百一十八《王拱辰传》云:至和三年,复拜三司使。聘契丹,见其主混同江,设宴垂钓,每得鱼,必酬拱辰酒,亲鼓琵琶以侑饮。谓其相曰:“此南朝少年状元也,入翰林十五年,故吾厚待之”。《宋史》卷三百四十三《许将传》亦载:许将出使契丹,“及至北境,居人跨屋栋聚观,曰‘看南朝状元’。”其状元之尊,深入于社会人心,一至于此。
文天祥于理宗宝佑元年(1253)参加州试,成绩优异。理宗宝佑三年(1255),入吉州白鹭洲书院读书;同年,与其大弟文璧成为吉州贡士。将赴次年春天在京城举办的省试前,庐陵地方长官李迪举亲为贡士们设宴送行。文天祥赋《次鹿鸣宴诗》:
礼乐皇皇使者行,光华分似及乡英。
贞元虎榜虽连捷,司隶龙门幸缀名。
二宋高科犹易事,两苏清节乃真荣。
囊书自负应如此,肯逊当年祢正平。
诗中主要写了二人同时成为吉州贡士的喜悦之情。“二宋高科犹易事,两苏清节乃真荣”两句,用北宋事典,而慕“两苏(苏轼、苏辙)清节”,是很有标格的。
文天祥省试通过后,宝佑四年(1256)的五月八日,于集英殿参加殿式。这次殿试,理宗把文天祥的卷子擢为第一。殿试主考官王应麟谓:“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今传《宝佑四年登科录》中,有理宗《赐状元文元天祥已下诗》一首:
道久于心化末成,乐闻尔士对延英。
诚惟不息斯文著,治岂多端在力行。
华国以文由造理,事君务实勿沽名。
德贤功用真无敌,能为皇家立太平。
理宗欲得贤才而为皇家立太平,用意为好,但其实已难挽回南宋灭亡的历史命运。所幸的是,此一榜中除文天祥外,还出了谢枋得、陆秀夫两个孤忠劲节的人物。谢枋得为此榜第二甲一名进士,于宋亡后拒做新朝的官,不食而死。陆秀夫为此榜第二甲二十七名进士,帝赵�死后,与张世杰等复立赵�为帝,徙驻�山,坚持抗元。�山破,驱妻子入海,自负帝�投海而死。
文天祥殿试抡元,大魁天下,自然成为“公众人物”,也自然难于免俗,“题咏匆匆”“酬应琐琐”的无聊之作随之产生。其中赠相士之作,可为代表。如《赠梅谷相士》、《赠�湖相士》、《赠赵神眼》、《赠刘矮跛相士》等。这些诗作,大多从名字着眼,敷衍成诗,且多杂以游戏口吻。如《赠镜斋徐相士》:邹忌不如徐公美,引镜自窥得真是。门下食客才有求,昏昏便以妻妾比。徐家耳孙却不然,自名一镜京师市。世人无用看青铜,此君双眼明秋水。君以无求游公卿,勿令此镜生瑕滓。堞子太面何难知,从今光照二百里。这首诗以《战国策》之《邹忌讽齐王纳谏》中的城北徐公来比镜斋徐相士,夸说徐相士的神异相术,如此而已。
这种现象的出现,如上所言,是文天祥难以免俗而不得不为。而这种世俗之力,确也难以对抗。《武林旧事》卷二《唱名》载状元等游街情况,似可看出此中消息:皆重戴绿袍丝鞭,俊马快行,各持敕黄于前。黄幡杂沓,多至数十百面,各书诗一句于上。呵殿如云,皆平日交游亲旧相迓之人。或三学使令斋臧辈。若执事之人,则系帅漕司差,到状元局祗应。亦有术人相士辈,自炫预定魁选,鼓舞于中。自东华门至期集所。豪家贵邸,竟列彩幕纵观。其有少年末有室家者,亦往往于此择婿焉。金文京先生谓:“如此热闹显眼简直跟现代人看明星人物无异。这样,状元郎之成为舞台上的主角,可谓顺理成章之事了。与此同时,从上文也可看出’术人相士辈’和应举士人的相互依赖的关系。相士或看风水的人预言某人命中必定中考的事,像《夷坚志》中颇多。”(《南戏和南宋状元文化》)。
另一方面,文天祥本人“以诗为戏”的观念也必然影响到他的早期诗歌创作。其《跋萧敬夫诗稿》云:“累丸承蜩,戏之神者也;运斤成风,使之神者也。文章一小伎,诗又小伎之游戏者。”文天祥自称“幼蒙家庭之训”、“长读圣贤之书”(《谢丞相》),是在宋代理学盛行的背景下接受的儒学教育,因而大多数理学家的重道轻文的思想,不会不对他发生作用。他把文章看成小伎,更把诗歌看成“小伎之游戏者”,即多少是这一观念的反映。文天祥参加殿式时的策题,及其所对策,就带有道学气。
对诗文应酬,文天祥其实也有自己的苦衷。他在给欧阳巽斋老师的信中说:“先生昔者于应酬亦苦之,今犹若此否尝蒙见示:每许人作一文,如置一针胸次。今某畏为文词,亦类此矣。”在另一封信里又说:“某寻常于术者少所许可,而江湖之人登门者日不绝。彼诚求饱暖于吾徒之一言;吾徒诚悯其衣食之皇皇,则来者必誉,是故不暇问其术之真何似也。”这里所说的“畏为文词”因悯江湖术士而有求必誉不问其真,确为其夫子自道式的真实表白。但这种苦衷只是停留于表面的为状元声名所累的苦闷上,而未作深刻反省,且有强作辩解意味,那么其表白也就显得有些轻描淡写了。文天祥的前期诗歌也仍有一些较好的作品,如《题碧落堂》、《山中感兴三首》、《生日和谢爱山长句》、《夜坐》等篇,或“近来又报秋风紧,颇觉忧时鬓欲斑”,或“但存松柏心,天地真茫茫,”或“夜阑抚剑”、闻鸡起舞,感时报国之情,仍时有些许展露。如果不是世事板荡,国难当头,性喜豪华、声伎满前的文天祥可能会像大多数平庸的状元一样,度过平庸的一生。德�勤王,慨然奋起,流离幽囚而终成大节,其诗其文遂为天地间一大奇观。清林昌彝《海天琴思续录》卷二云:“科名以人重,人不以科名重。凡道德、勋业、学问、文章可传于世者,乃功名,非科名也。”文天祥不但以其功名,而且以其惊天地泣鬼神的诗文名重后世。“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人间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正气歌》)这些浩然诗章,不仅见其为人,而且还诠释着一个道理:“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题元遗山集》)。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表白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