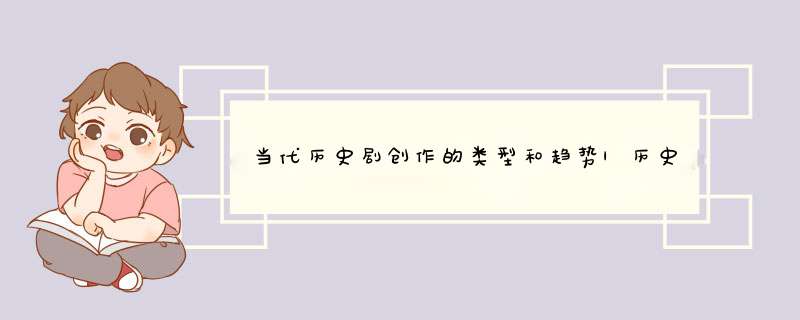
历史是一个巨型文本,因阐释者气质、经验、性别、视角的丰富多彩,呈现出可塑性强、蕴含深广的风姿。从历史叙事的可能性的角度,笔者认为可将当代历史剧分为四大类型: 第一种是“传统历史剧”,严格遵守原生历史的真实性,力求真实再现历史上的真人真事甚至细节,虚构只允许来弥补局部史料的欠缺,更有甚者说“无一字无来历,无一事无出处”。传统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是一个客体,是不可转移的客观存在,历史剧必须有史可查,再现历史的文本真实,如建国初期的京剧《闯王进京》、话剧《文成公主》等历史剧,主要人物姓名、形象及其基本情节、走向就是以信史为依据的。
第二种是“新编古代剧”,在不变动历史基本框架的前提下,允许大幅度的艺术虚构和塑造典型,切近历史的本质真实,后来出现的一些历史传奇故事剧,不再考虑信史与野史、历史与文艺作品的区别,凡是前朝往世的野史笔记、稗闻传说、小说诗歌的题材都作为表现历史存在的改写材料,如京剧《野猪林》、豫剧《花木兰》、昆曲《十五贯》等虚构、编造成分较多,但它们仍然遵循历史真实、典型化、可然律与或然律的创作原则。
第三种是“新历史寓意剧”,虚构历史时空,将历史意味转换成符号化的历史结构和话语,舞台上展现的是人物的心灵史,或是作者对历史的一种抽象把握,是一种“准历史”和“泛历史”。新时期以来,历史剧创作越来越倾向于全面虚构,不讲历史背景、典型环境,有意虚化具体的历史时空和人物,即所谓“古装戏”(当然是其中有深度模式、有历史感的一部分,后面着重论述)。
第四种是“后历史剧”,力图超越所有历史剧的习见话语和经验,往往运用“波普”技术将各种历史性片段拼贴起来,张扬个体的生命意志,荒诞感、游戏感浓厚。如川剧《潘金莲》是古今中外一些人物关于女人的讨论会,话剧《中国孤儿》系元杂剧《赵氏孤儿》和伏尔泰《中国孤儿》的拼凑,越剧《孔乙己》由鲁迅的几篇小说组合杂糅而成。
后历史剧基本上是“先锋戏剧”的一部分,但在目前探索性历史剧中,新历史寓意剧是主体,是其厚重的部分,相比起来较容易为观众普遍接受。可以说,传统历史剧是历史学家心目中的历史剧,新编古代剧是广大观众心目中的历史剧,而新历史寓意剧、后历史剧则是诗人智者心目中的历史剧。莱辛就说:“诗人需要历史并不是因为它是曾经发生过的事,而是因为它是以某种方式发生过的事,和这样发生的事相比较,诗人很难虚构出更适合自己当前的目的的事情。”①这已经具有“诗比历史更真实”的意味、鉴于历史的不可还原性和某种不可确定性,它们都可统称为新编历史剧或新创历史剧②。这种分类法与其说是迎合了中国式矛盾解决的平分秋色心理,不如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历史剧创作释放出应有的巨大艺术能量,已经形成多元化发展的格局,它将戏剧观众群体差异性的本来面目揭示了出来,令施发者和接受者必须在历史观与戏剧观及其融合上作出自己的文化选择。
在此,笔者想以湖北省京剧院的新创剧目《膏药章》为个案,来深入分析当前势头看好的新历史剧创作现状。京剧《膏药章》以寓喜于悲的方法演绎一个小人物的悲惨命运,侧面反映一个动荡飘摇的大时代。它的人物和故事都是虚拟的,在历史背景和典型环境上尚未走向完全虚拟的程度,而是某种再现和“模仿”,因为该剧的创作初衷在于纪念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在于发掘武汉地区的历史文化特色。生动真实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关系就成为其必要的历史依托,与“真人真事”、“真人假事”、“假人真事”一样达到了历史真实。剧作家依托史实而不拘泥于史实,是从历史剧的“剧”的角度统筹安排全局,人物充分性格化、主题高度意态化,从而使戏剧文本具有较高叙事功能、认识功能和审美功能。历史剧总是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倾向,对于剧作家来说,用理解充实历史生活,用个性激活历史情境,才能使历史和主体之间构成真正的对话关系,创作主体才能灵活把握历史,在任何创作题材上都具有一定超越性和自由度。通过对京剧《膏药章》的艺术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当代新历史剧的探索具有以下三个趋势:
第一,在当前异彩纷呈的戏剧创作中,有些探索性的新历史剧对历史文本采取抽象化的虚构方式,通过一系列隐喻性语义符号构筑起来,如京剧《膏药章》、湘剧《山鬼》、川剧《田姐与庄周》、淮剧《金龙与蜉蝣》等,它们在内外结构上被一些经过历史长期积淀、反复印证而活泼发达的历史认知符号组装起来,追求的不是表层的教化,而是深层的寓意,充分表达当代剧作家对悠长的历史人生的独特见解。在这类历史剧中,历史人物不再是生活中的真实个体或文艺中的典型形象,而是代表某种历史文化特性的隐喻符号,如同可以克隆的历史文化基因。如《山鬼》中的屈原不再是历史上作为一代大诗人、政治理论家的屈原,而是古代巫祝人格的象征,其言行只符合古代礼乐文化的原始思维。这是一个全新的、具有楚地巫风色彩的大巫形象,比起《楚辞》和郭沫若《屈原》中的屈原来,或许有许多“亵渎”之处,却将屈原所体现的历史文化精神予以夸张放大了。《金龙与蜉蝣》设定为“西周以降,华夏某诸侯国,大体上楚流裔一脉”,《田姐与庄周》标明是“一个大男人与小女人无从稽考的故事”,有的干脆只提示是“古代”,人物不仅是虚构的,而且连具体姓名都没有,泛化得只以性别、身份、绰号代替,以凸现人物的符号特性。如《金龙与蜉蝣》中的金龙、牯牛、蜉蝣、孑孓,《膏药章》中的膏药章、小寡妇、革命党、大师兄等,它们在一种约定俗成的审美机制下,只代表人物的一种身份和生命状况,成为一种类型化人物,被赋予该类人物一般赋予的历史人生和文化形象。抽象化的处理,将戏剧中变圆的人物又压扁,以放大、突出人物性格的文化蕴涵,使历史关系简化成一系列文化符号,这些似乎更能清晰地表达剧作家对历史人生的总体把握。
第二,这些探索性的剧目在情节、主题和意象上往往追求一种隐喻和象征,让结构主义的形式充分发挥意义传达的作用。在《曹操与杨修》中,曹操与杨修猜谜斗智,打赌败者为胜者牵马,最后在法场平等对话,这些情节在传统历史剧中是不可想象的,它们在该剧中却是二人人格较量的形式象征,具有扣人心弦的画面效果和审美力度。《山鬼》中,屈原受灵蛇的指引,拿着代表权力的青铜钺,到原始部落中代理族长,以实现自己的美政。当他用美酒招待偷薯人时,偷薯人却将薯与钺偷梁换柱,神圣的仁政思想遭到世俗小人的轻易消解。屈原还渴慕与富有诗意的美女娱情交欢,上下求索,相思成疾,当美人山鬼自动投怀送抱时,他却屡次迟疑不决,败下阵来,喻示着楚文化想像力与现实逼迫性、精神理想与物质现实之间的复杂矛盾。在《膏药章》中,几根柱子勉力支撑头顶的天空,大厦将倾、山河破碎、群魔乱舞,民不聊生的时代背景得以突显,舞台上弥漫着混乱、压抑、虚伪、腐败、死亡的气息。大清衙门上下纷纷将一剂狗皮膏药贴在脸上,分明是对病态社会的精辟呈现。小寡妇坟前上吊,走投无路,是身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调戏与压迫。膏药章的遭遇带有较强的偶然性与随机性,体现出当代探索性历史剧作者深刻的艺术观念,其偶然性与随机性也体现出该剧强烈的“寓悲于喜”以及膏药章“小”的特性,小而处处碰壁,朝不保夕,恍若空中微尘盘中餐。膏药章最后被胡乱送上法场,如猪狗般坐在箩筐里,那几声“�咕”、“咔嚓”,让人领略到铡刀随意切割人类骨肉生命的“低级模仿”的残酷,一种更纯态的历史真实。在这里“假如……”属于台上的戏剧,也属于台下的观众,答案如何却是观众审美心理学的问题。结尾小寡妇再次上坟,完成了创作者悲天悯人的圆形思维,而男、女主人公生死互换的最后一转将舞台杂乱的影像和声音再次清空,观众的注意力再次被导向不可言说的深层,形式的象征达到令人敬畏的程度。
第三,以上这些是“寓言”的写法与读法,借用戏剧导演的形式理念来表达剧作家的某种深意,其情节大都呈现为一种沉淀于人们集体无意识中、易为信息符号唤起的原型结构。荣格强调集体无意识的先天性和普遍性:“它并非来源于个人经验,并非从后天中获得,而是先天地存在的。我把这更深的一层定名为‘集体无意识’,选择‘集体’一词是因为这部分无意识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它与个性心理相反,具备了所有地方和所有个人皆有的大体相似的内容和行为方式。换言之,由于它在所有人身上都是相同的,因此组成了一种超个性的心理基础,并且普遍地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③弗莱在运用原型理论建构文学发展模式的过程中,进一步明确了原型(archetype)的文学特征。他认为,原型是“一种典型的或重复的意象,我用原型指一种象征,它把一首诗和别的诗联系起来从而有助于统一和整合我们的文学经验。而且鉴于原型是可交流的象征,原型批评主要关注于作为社会事实和交流模式的文学”。④原型作为一个“独立的交际单位”,它在文学艺术演变的过程中,自身具有意义上的传承,既在中国与世界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形成文化积淀,也与特定时代的社会心理密切相连,它不是孤立地出现在一个文艺作品中,而是在不同的作品中不断重复出现,从而扩大它的表现内涵。原型作为可以换置的单位,显示出与以往的文学艺术之间的渊源联系,是人们洞悉历史文化和社会人生的经验性符号。这种情节原型在清代长篇弹词《再生缘》(后改编为戏曲《孟丽君》,各地竞相移植上演)中早已大放光彩,集之大成,是我国古代文艺创作、特别是古典戏曲创作成熟发达后的经验性预设,如比箭招亲、女扮男装、描容上路、中魁招婿等众多流传的情节模式。这些情节模式环环相扣、曲折离奇,并在《女驸马》、《谢瑶环》等作品中反复出现,蕴涵着被逐渐铸就的民族审美情趣,极大地适应了市民今人的文化氛围,其复述性与增殖性往往鱼龙混杂。
为了超越前人的创作成果,显示当代人的新思维,贴近人们对各种媒介反复出现的历史影像的条块认识,这种浸透集体无意识的情节模式和叙述程式在当代历史剧创作中得到自觉的张扬,如《曹操与杨修》中的牵马坠镫、法场对话、张榜招贤等,《金龙与蜉蝣》中的亲友相残、接种xx、以小胜大等,呈现原型化的冲动和趋势,表达了创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历史新一轮重估的强烈意愿。《膏药章》中无疑聚合着民间和人文传统的武请治病、光棍娶妻、寡妇上坟、狗皮膏药、刽子手自白、不准革命等几种经典故事的原型,用通俗的话和作者的话说,是“点子”,是“文化遗产之借鉴”⑤。它们按照一定的序列拼贴起来,构成不间断的动作性、戏剧性和可看性,也有利于导演在舞台构图、调度和节奏等方面驾轻就熟,花样翻新,它们在篝火的映照下极为生动受用,甚至被引以为表达了劳苦人民生活的痛苦、理想、智慧和阶级意识,而该剧主要是沿用了民间传统中生活气息浓郁的部分,将主人公设定为一个行走江湖、精明狡黠、唯唯诺诺、窝囊透顶的光棍,在纷乱动荡、人事复杂的年代,他敢于讲道理,更多的却是对外界各种力量的屈从。在创作者的知识分子战斗传统的观照下,武请治病、光棍娶妻的故事被赋予强大的人文精神和历史反思,而且膏药章是在历史浪潮的裹挟中展现剧烈的性格冲突和命运变化的,这种被动的裹挟式的卷入具有历史的穿透力,至今看来仍然似曾相识,逃不脱这个巨大的“历史原型”的调控。他要娶小寡妇的关键所在,不是他的善良品格,而是一种与命运抗争的现代精神,而且这种抗争不是所谓随波逐流、为人牵引,而是出于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这也正是小寡妇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作为我们集体的回忆与经验,它展示了人类挣脱那个巨大的原型宿命的不懈努力,具有浓厚的民间趣味和思想魅力。原型是个容器,使汩汩而流的生活之水有了可供欣赏的形状,然而在神性与人性的时代冲突下,合乎“自然的和理性的类比”的“高级模仿”日益消退其光环,偏于日常生活意象与心态的“低级模仿”以四条腿行走在舞台上。原型结构具有普遍性,但如何反映原型取决于创作者的个人环境,可以说这种历史剧的写作方式绝不会遮蔽创作者的个体经验性和创造性。弗莱甚至断言:“文学的模式越往后发展,来源于实际社会生活条件的诗歌意象也就越多。”
应该说,京剧《膏药章》、川剧《潘金莲》和湘剧《山鬼》等剧目是新时期以来我国历史剧创作领域的重要收获,它们不仅艺术上大气圆熟,而且触入了我们的精神底层和时代文化心理,让人常看常新,它们的意义不能仅仅局限于版本学上。无论是传统修辞手法的运用,还是现代结构方式的借鉴,中国的戏剧要有自己的艺术特性,要将形式和内容的探索与充分戏剧化结合起来,才能有效避免造作的痕迹和空落的席位,使浑然一体的艺术品成为街谈巷议的事物。在艺术表达方式丰富多彩、谁都敢于一戏一招的今天,包括历史剧在内的戏剧创作如何贴近原汁原味的社会人生,如何面对人生和精神的苦难,如何表现人的欲望要求和意志力量,如何体现文学艺术的“此在”原则,反倒是我们更应该警醒和努力的东西。正如谢有顺在《终止游戏与继续生存》一文所说:“作为一个精神事务的劳作者,我们没有理由回避现实的苦难,回避当代面临的生存境遇。用所谓的当代体验去写作历史,是很难传达出我们时代生存深处的声音的。回到当代,并不是简单的题材转换,而是要对当下现实掩盖下的精神本质作出反映。因为我们既不能逃避生存,也不能逃避生存环境,回到当代,就是说要站在自己所处的生存现实上,出示一种写作的勇气―――一种直面生存的勇气。”
注:
①《汉堡剧评》,莱辛著,《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第4期。
②在概念运用上,新编历史剧无疑有广义的与狭义的之分。广义的新编历史剧即习惯上统称建国以后“此在”的历史剧创作,如《海瑞罢官》作为传统历史剧,当时仍称新编历史剧。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个人的看法。
③《集体无意识的原型》,《荣格文集》第39、40页,荣格著,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④《批评的剖析》第99页,弗莱著,陈慧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⑤《镜子・点子・路子―――<膏药章>创作札记》,谢鲁著,《剧本》l991年第1期。
《大司命》和《少司命》也是姊妹篇。大司命是男神,一位主宰人类生命的神;少司命是女神,一位主管人们的后代和少年儿童命运的神。大司命和少司命是一对爱神,少司命苦苦地追求大司命,把神仙之间的恋爱写得缠绵排恻。郭沫若却认为大司命爱的是云中君。金开诚则认为《少司命》所表现的是人和神之间的友谊关系,不是人和神的恋爱关系,少司命一手抱着幼儿,一手提着长剑,成为少年儿童的保护神,这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光辉的形象。陆侃如等又认为,《九歌》所祭祀的神大都与生产有关,日神、云神、山神、水神等。因为《九歌》来自民间,所以里边有人与神恋爱的痕迹。人神间的悲欢离合,实际上是我们祖先对于生产的热烈追求的另一表现。不管谁与谁恋爱,不管谁爱谁,这两篇作品对爱和爱情的描写是真挚感人的,也是健康向上的,用特殊的形式反映了百姓生活。
“云中君”、“少司命”、“湘夫人”、“山鬼”。
屈原的《九歌》是取材于楚地原始的祀神乐曲。所祀之神有4位是女神,即“云中君”(月神)、“少司命”(爱神)、“湘夫人”(湘水女神)、“山鬼”(山林女神),她们又分别是“东皇太一”、“湘君”、“大司命”、“河伯”的配偶神。这其中特别值得关注与研究的是山鬼,在三峡中出了一个巫山神女,又出了一个山鬼,这两位女神之间有何联系最先将她们联系起来的是清代学者顾天成,他在《九歌解》中认为山鬼同南楚神话中的巫山神女相似,《高唐赋》“通篇辞意似指此事(山鬼)。”郭沫若在《屈原赋今译》中进一步论证:“於山”即是巫山,“山鬼乃是楚地巫山之神女。”推想山鬼与巫山神女的神话在三峡一带曾经广泛流传,而且有着各种不同的“版本”。正如矛盾先生所说:“巫山神女的传说,在当时一定也是洋洋大观,可惜现在我们只能在宋玉的《高唐赋》里找到一些片断。”
当年韩寒的《独唱团》中, 收录了周云蓬写的《绿皮火车》,后来成了一个同名文集。
周云蓬出生在东北铁西区,青光眼,九岁失明,本来注定了要当个按摩师,却不服天命般当了吟游诗人。他的《中国孩子》、《不会说话的爱情》,都曾经深深地感动过那个时代。
文集中,他写了很多自己的故事,这事情要是发生在你的身上,绝对会让你苦大仇深, 但在他身上,在经受过这一切之后,已经云淡风轻。
他可以随意地出国、买吉他、刷微博、走过大街小巷,还能不怕藏獒,徒步西藏。
他很会比喻,写胡德夫,说他琴声如海水,歌声如巨钟;写某个歌手,说她声音像是飘在风中的丝绸。
他交游广阔,有一段他住在绍兴,依然门前鸿儒不绝,柴静、冯唐、罗永浩、李志……都是好友。
这样的人,也很会谈恋爱,眼盲心亮,如宝剑刺破叠嶂。
几年前,他们到成都来演出,我在旁。看到当时她的女友绿妖跟他在一起,一个在台上唱,一个在台下望。
我去找绿妖签名,她笑笑,不写字,我只好说,恩,我看过你很多书,《阑珊纪》我都看过,于是绿妖拿起笔,端端正正写了俩字。用了一个破纸片,现在再找也找不到了。
绿妖为什么跟周云蓬在一起呢,因为她说,王小波说, 人这一生,还是要找一个有趣的在一起。
然后呢,他们就分手了,到今年,应该是分手五周年了吧。
原因呢,很狗血,男人的通病就是如此啊,有趣不有趣,都不能阻挡。
也没法谴责,因为这是人家的选择,未婚未嫁,述诸法律,无用,诉诸道德,呵呵。
艺术家与诗人,有上帝的眷顾,但终究也是凡人。
周云蓬说,有一次去参加活动,周杰伦,孙燕姿都去了。还没吃饭,跟主办方拿了个盒饭,结果要走红毯了,又怕盒饭放到那里丢了,于是像拿着奖杯一样拿着盒饭走过了红毯,到现场了,放到椅子下面,听上面的光鲜。
光鲜总会散去,能饱肚的,才是饭。吃下去的,才是饭。必须吃的,只有饭。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表白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