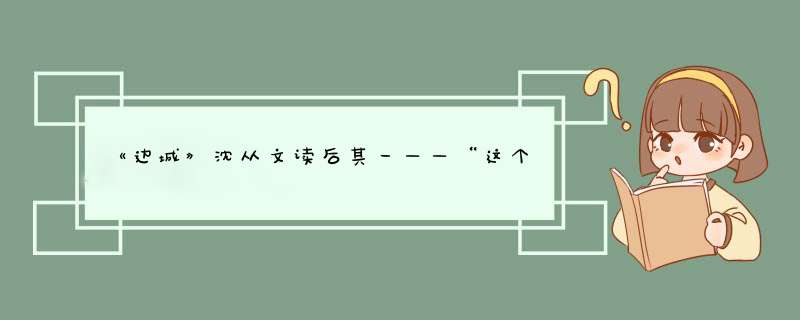
我想傩送也许永远不回来了。
茶峒是湘西边境的一个小山城,凭水依山筑城,近山一面,城墙俨然如一条长蛇,沿山爬去。转身就面着酉水,也叫作白河,前后都是险滩,上游下游行船无不冒着点风险的。两省接壤处,十余年来主持地方军事的,注重在安辑保守,处置极其得法,并无变故发生。水陆商务既不至于受战争停顿,也不至于为土匪影响,一切莫不既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了生。
既然无外扰惊乱,那么在茶峒这个小山城里人与人的感情和气便更是被看重。想将新碾坊做陪嫁,把女儿嫁给傩送二老的王团总是中寨人,住在高山砦子上,为了这门婚事专门在河街一带置了产业。而船总顺顺常年在河街一带专管租赁买卖船只,代人装货在茶峒与辰州之间来往贸易,少不得常常与王团总有生意上的交割买办,再加上顺顺为人豪爽,少不得私情上拿大兴场上的好烧酒互相请的。中寨一方或许也对这桩喜事颇有些信心,至于端午节看龙船时,待嫁的王大娘子也少不得自说来看看龙船,坐在船总顺顺吊脚楼中间的悬窗,好让别人看看她,也意在凿实这门婚事。可二老在两年前就从心里欢喜了翠翠,不为那中寨的碾坊和新娘所动心,即使是要守在白塔下撑一辈子渡船,为着心爱的女子也是愿意的。只是二老明白若为父亲着想,家里多座碾坊多个人,可以使他快活,父亲与王团总素来有交情,有了这门婚事更是亲上加亲。然而若是为了翠翠去撑渡船,为中寨所知,少不得一番猜忌,若是引出些“宁要渡船不要碾坊”的言语,好像对中寨颇有些轻视的意味,以后两边来往都不好看。二老于此无法可想,既不愿意误了父亲和中寨的人情关系,又不愿放弃心爱的翠翠,一走了之,此事未定,才不会引他入两难的境地。
再而是因为天保大老的死。天保大老一直以来也心恋着翠翠,对老船夫面前提过,也曾托人带话去打探老船夫的意思。老船夫希望翠翠能嫁给自己欢喜的男子,又不知翠翠对天保大老是什么样的心思,于是便告诉大老两条路:若走车路,便请自家父亲请保山来说亲;若走马路,便在崖上唱歌来博得翠翠的爱情。大老请保山来提亲,老船夫问翠翠对大老的亲事是否应允,翠翠赧然不语,却透露出一种不乐意的神气,最终老船夫只得婉拒了这门亲事。大老走车路不成,只得走马路,夜里到山崖上为翠翠唱歌。可是得知二老也爱着翠翠,知道走马路唱歌终不是自己弟弟的敌手,大老为着忘却这上边的一切随着货船下桃源去了。苦恋不就的心情和争而不得的不甘交织在大老的心里,一连沉默了数日,终于在茨滩船触了礁,原本神情木然的大老猝不及防,随沉船淹死在了河里。老船夫听闻心知是为着他没能得到翠翠的爱情,对此事多加关心,反而引起了船总顺顺和傩送二老的反感,萌生了“大老是因为他的缘故才死的”的想法。于是船总顺顺便不愿意再将这间接将大老弄死的女子再娶作二老的媳妇,二老和翠翠的爱情遭到了家人的反对,为儿女说亲的老船夫为顺顺所冷落,他们的亲事难以敲定。二老心中怀有对老船夫的不满和愤懑,两人再难相处,也成为了二老和翠翠结成婚姻的阻碍。二老的离开,一是为着寻死去哥哥的尸首,或许也是对这门婚事失去了信心。
其三就是二老对翠翠心意的误解。虽然打从第一次端午节的相见,二老心中就开始恋着翠翠,却一直没能够相互表白心意。翠翠是个感情朦胧而腼腆的女孩,心中怀着对二老的爱情,可是见着二老时却时时退避,因为害羞而不言语。这也是因为翠翠家庭的原因,父亲母亲相继的死去,让翠翠成长当中没有父母的陪伴,让她对爱情既怀着向往,又带着一些害怕,所以她不能像其他女子那样大胆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再到后来老船夫也猜出些许翠翠的心思,先是时时问问翠翠对二老的心意,再到后面有意撮合,翠翠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直到后来大老去世,两家人来往更是稀少,顺顺也不愿意再与老船夫家结亲。二老拒绝了中寨人的婚事,提出要再考虑。及到后来二老与家中一个长年在河边喊过渡,翠翠跑出来见着二老,却转身就躲进竹林当中。二老见着,虽然老船夫的话里不断带着“这事有边”的意味,翠翠的躲避却让二老对她的爱情感到不太自信。或许也是因为疑心自己或许得不到翠翠的爱情,二老选择了离开。
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朴素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故事中充满了五月中的斜风细雨,以及那点六月中夏雨欲来时闷人的热和闷热中的寂寞。
边城主要内容:
生活在湘西古城茶峒的翠翠和爷爷摆渡为生,当地船总顺顺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同时喜欢上了翠翠。但翠翠却钟情于两年前龙舟赛上看到的老二傩送。
兄弟两个以唱山歌来向翠翠表白,让翠翠自己决定。天保不敌傩送,愤而独自驾船远行做生意,却不幸出事身亡,傩送为此深深自责,便只身去了桃源不再回来。
船总顺顺因为两个儿子的事情不再与翠翠爷爷交好,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翠翠爷爷安静地离开人世,自此,翠翠独自在江边摆渡,等待傩送的归来。
人物形象分析:
1、翠翠
翠翠是个天真善良、温柔清纯的小女孩,是作者倾注“爱”与“美”的理想的艺术形象。翠翠来到人间,便是爱的天使与爱的精灵。
她爷爷把她领大,一老一少相依为命。她既是爱情的女儿,又是大自然的女儿。在她身上“天人合一”,她是美的精灵与化身。
2、爷爷
爷爷保有着中国传统的美德,他对孙女翠翠亲情无限。为翠翠的亲事操心担忧,尽力促成翠翠爱情的实现。在生活上,对翠翠也是无比关怀,不让翠翠坐热石头,惟恐翠翠生病。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边城》成书于1931年,那正是沈从文爱情事业双丰收的季节。1931年社会虽然动荡不安,但总体上还是稍显和平,这个时候中国有良知的文人,都在思考着人性的本质。
沈从文自然是走在前沿的,于是,他希望通过自己对湘西的印象,描写了一个近似于桃花源的湘西小城,给都市文明中迷茫的人性指一条明路。人间尚有纯洁自然的爱,人生需要皈依自然的本性。
赏析:
翠翠的爱情故事,作者所表现出的似乎是一个“谁也没有错”的爱情悲剧,作者只是有意识的在人性层面上叙述故事,无意发掘悲剧产生的人为的、社会等方面的因素。
我们不妨来看看在这篇小说中天保和傩送所选择的求爱方式:天保所选择的车路—托人做媒,这种婚配方式是汉族人的传统,在天保的婚俗观念中还是汉人的“父母之命”。
因此在他一厢情愿地托媒求婚失败后,他反而怨恨老船夫:“鬼知道那老的存心是要把孙女嫁个会唱歌的水手,还是预备规规矩矩地嫁个人!”可见他把老船夫看成是翠翠婚事的主权人。
而且他的弦外之音嫁个会唱歌的水手,就不是“规规矩矩”的了。傩送所选择的马路—站在山头唱歌,这是苗族人的传统。苗族人是青年男女自由恋爱成婚。
然而自清雍正年间在湘西这边实施“改土归流”以来,伴随着对苗民反抗的武力剿灭,一种无形的东西正慢慢渗透到这片准乎自然的人生天地里,古朴的民风也在日渐消失。
翠翠和这些上层人物相比,是这般的清纯与美丽,天真与善良。她烛照着上流社会的腐朽生活,反衬着城里人的“庸俗小气自私市侩”。
沈从文也借此揭露都市“现代文明”培育的虚伪、自私、怯懦……总之,翠翠是一位清纯可爱的乡村女孩,是美的化身。她的爱情故事是一首凄美的歌。
她是作者乡恋情感与怀旧思想孕育起来的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作者也通过翠翠这一艺术形象表现出了对“现代文明”的无情批判。
-边城
以山清水秀、充满人性美和人情美的茶峒小山城为背景,叙述了美丽纯朴的湘西少女翠翠如何在“现代”文明之风的浸浴下以及爱情的折变磨难下,逐渐从半原始的自然状态成长蜕变为“成人”、“社会人”的故事。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篇关于“成长”的小说。在行文中,作者多处以“长大成人”“大了”“成长”“长大”等词,昭示翠翠走向“成人化”和“社会化”。从《边城》的文本解读出发,翠翠的“成长”处在三个“变化”之中。
一是社会环境的变化。翠翠出生的湘西茶峒小山城,风俗淳厚、人情质朴、重义轻利,“一切总永远那么静寂,所有的人每个日子都在这种不可形容的单纯寂寞里过去”。即使河街吊脚楼里的妓女,也还保持着某种“生命的严肃感”。然而,这里毕竟不是原始洪荒的“世外桃源”,“大都市随了商务发达而产生的某种寄食者”开始落户于此。“现代”的入侵,对未经金钱、实利污染的朴质民风造成冲击。翠翠耳濡目染,“现代”的观念也悄悄在她的心里扎下了根。当她和傩送的爱情由于团总女儿的介入,直接呈现为“渡船”与“碾坊”的对立时,她第一次感到了金钱力量的可怕。“他又不是傻小二,不要碾坊,要渡船吗”乡民关于傩送是选择她还是团总女儿,是选择渡船还是碾坊的议论,以金钱为衡量标准(碾坊的收益顶十个长工干一年),使她“小小心腔中充满了一种说不明的东西”。在第八章里她无所谓地唱着:“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显然是她潜意识里对金钱观念至上的反抗。这是社会大课堂在翠翠的成长路上所上的第一课。
二是祖父心事的变化。纯朴大方、热情豪爽的祖父老牛护犊,使翠翠在没有父母的呵护爱惜下,也能无忧无虑、快乐健康地成长。随着翠翠的长大,祖父开始“有点心事,心子重重的”。原因有二:一是翠翠的长大直接使他忆起翠翠母亲的悲剧,害怕翠翠重蹈覆辙;二是翠翠人已长大了,证明自己也真正老了,必须要把翠翠交给一个可靠的人。这些有分量的心事沉沉地压在祖父的心上,也迫使翠翠开始思索自己的未来。小说在第七章写道:“我想的很远,很多。可是我不知想些什么。”不懂得翠翠心思的祖父,在面对选择大老天保还是选择二老傩送作为翠翠的终身依靠人时,提出了走车路和走马路的方式。走车路就是包办婚姻,即请媒人提亲,一切由双方家长做主;走马路是指原始的自由婚姻,以向对方唱歌的方式求爱,一切由男女双方自己做主。大老选择走车路,遭到翠翠的拒绝后(祖父还是以尊重翠翠的意愿为主,没有再作主张),自知走马路不是傩送的对手,避走下水在茨滩出事淹坏了,酿成悲剧。整个悲剧发生的过程中,翠翠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祖父的心事变化,碍于传统文化观念的束缚,苦于不能亲口说出自己爱的是二老不是大老。之后,虽然“一切依旧,惟对于生活,却仿佛什么地方有了看不见的缺口,始终无法填补起来”。而这一切直到祖父猝然而卒,翠翠才从杨马兵的口中得知事情的原委。不过,正是这种与祖父的心理对抗和磨擦中,翠翠逐渐成熟起来。这是翠翠成长历程中的第二课。
三是翠翠自我的变化。天真单纯的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使她“从不发愁,从不动气”,终日与祖父、渡船、黄狗相依生活,这时她的自我处于一种蒙昧状态。换句话说,她从未意识到自我。翠翠自我意识觉醒源于她的情窦初开,两年前的端牛节与二老傩送相遇,文中这样写道:“但是另外一件事,属于自己不关祖父的,却使翠翠沉默了一个夜晚。”朦胧的爱使她第一次意识到自我的存在。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波伏娃曾指出:在以男性意识为中心的社会里,女性在成长过程中是以社会(男性)的需要为基点建立起所谓女性的理想范式,这就使女性将原是社会的、男性的要求内化为女性的自我选择,将原是外在的、文化的压抑内化为女性的自我压抑。因而,女性一旦觉醒,其反叛的对象不是外在的压迫力量,而是女性与自我的抗争。翠翠在意识到自我之后,就开始了与自我的抗争。这里有两个最显著的表现:一是翠翠的自我非常喜欢傩送,但已经将社会道德、伦理规范内化为内在品质的她却死死压抑住自己的情感(社会认为不能表白),不给自我以充分表现的机会,导致自己也不知为何而哭,为何“在成熟中的生命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这样,就造成自我的释放只能借助于梦了。小说第十八章特意写到翠翠在睡梦里尽为山鸟歌声所浮着,做的梦也常是顶荒唐的梦,而她却“从这份隐秘里,便常常得到又惊又喜的兴奋”。二是面对大老天保的走车路,同样甚懂社会操作规范的翠翠不敢以言语表达自我的意见(拒绝),她身上各种所谓“好”的品质(社会强加于她的)与自我由此产生强烈的冲突,导致自我只能产生逃避的念头,“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但她马上意识到如果真的这样做了,爷爷会拿刀杀了她!自我的变化打破了翠翠单纯快乐的生活,给她带来了无尽的忧伤、烦恼与痛苦。然而,正是这种变化,使翠翠真正成熟起来,开始用成人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
翠翠的成长与其他“成长小说”所表现的主人公成长有着极大的一致性,即成长的过程就是展示人生悖论的过程,就是呈现人生痛苦的过程,或者说,成长本身就是悖论,就是痛苦。翠翠因“现代”观念的入侵、祖父微妙心事的重压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就是一种烦恼而痛苦的过程。其所处的客观环境的变化影响着其主观意识的变化,并催使其在自我的变化中痛苦地成长。可见,沈从文在《边城》中对翠翠的形象采用的是一种动态性、渐进式的塑造方法。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表白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