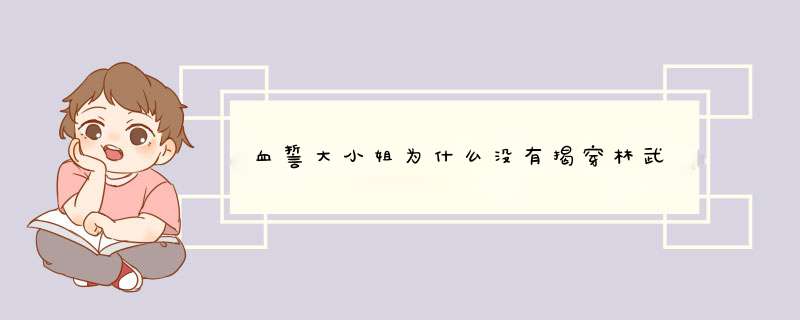
最近看到很多关于《血誓》里关于林武 、龙秀、覃岚三人之间的种种争论。
个人从开始到结尾都没有怎么纠结过这些个问题,比如林武是不是喜欢覃岚、覃岚是不是对林武动过心、林武对龙秀是不是一开始就有爱、林武和覃岚经过种种波折素不素走到了一起等等。。。。我只纠结过一个问题,那就是林武大哥和龙秀最后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每次林武大哥和龙秀单独在一起或者龙秀以那种泰山压顶之势强行表白的时候,就会出现那种土家族特别空灵的背景音乐。就因为这个音乐,所以一开始我就知道这林武大哥最后还是逃不过龙秀姑娘的手掌心的。面对龙秀姑娘浓烈的爱,我们林武大哥虽然老是吱吱呜呜或者以各种什么大仇未报誓不娶妻这种大义忽悠来忽悠去,不过看他那害羞状以及不知所措状还有不拒绝状,我也更加坚信,林大哥这样的绿林好汉,最终和龙秀这样子的女中豪杰才是绝配。
而有人又说了,那为什么林武总是帮助覃**。为什么覃岚屡次遇险,最后林武都会来个英雄救美呢?各位,这绝对不是爱。为什么呢,因为林武救覃岚不过是本着江湖道义,有仇报仇,有恩报恩罢了。请不要已偶像剧的思维来看待这部电视剧的感情线好么, 人家是绿林好汉,有江湖道义,除了整天儿女私情,他们更多的是为着自己的誓言或者地。哎,可惜的是,在这个世道,像林大哥这样仗义的人已经很少了,如果有人像林大哥这样老是为你挺身而出,要么就是暗恋,要么就是明恋。
他站在办公室的一扇玻璃窗前,向窗外望去时,一个少女从一块绿茵茵的草地的一条椭圆形的小径走了过来,低着头,看不见她娇羞的脸庞,但扎着的一根马尾辫子,一甩一甩的富有节奏。他心思绸密的想,在风里,长出了一双明亮的眼睛,他的视线就像可以放飞一只风筝。他确信,她会是一只风筝,可,他越往下想,心里就越不安,这一个少女,已侧了一下身,走向另一条路,连一个完整的背影都没留给他。
他太恨自己不争气。那一块草地,只有一个她,只有薄如羽翼的风,只有草在茂盛,只有一天的蓝,或者,在不惹眼处,只有一只蝴蝶在万绿丛中发现了一朵花,只有一只低低掠过草地的蜻蜓,只有一小片的时光,可以给他一个妙不可言的追求。
那是六九年的矿山。
一月,广东省计划战线革委会于十四日,以(69)粤计革12号《关于大宝山铁矿设计方案的批复》,指出:“大宝山矿综合利用会议,已经确定建设总规模年产铁矿石200万吨,以供应湘潭钢铁厂和韶关钢铁厂,在着手进行200万吨/年建设的同时,应优先狠抓矿体南部50万吨/年采矿场的建设工作。矿山今明两年内,铁矿建设计划和各项施工先后等,均应本此精神,分别轻重缓急,安排落实,要求今年基本建成年产50万吨设计能力,提早供应矿石,以保证韶钢和支援外省铁矿石的迫切需要。”
他在采场,当技术员,却跟矿工们很“铁”,可以称兄道弟,可以滚一身黄泥,实在累了,挤一张床睡。他从矿业大学一毕业,卷一床棉被,在工区的一间临时的办公室住了小半年,才分到一间竹搭棚里的一张床位。他一点都不计较,“来矿山,就不要怕苦”,这一句是他的口头禅,却更像“墓志铭”。
每一块矿石都可以写下他的青春,火热的,沸腾的,斗志昂扬的。但,他习惯了沉默。只有在矿工们遇到难题,他前去解决,有打破砂锅问到底时,他才不厌其烦的,孜孜不倦的讲述。偶尔,也眉色飞舞。
这是一份沉重的礼物。在年初,大宝山遭到了百年罕见的大冰冻,给矿山建设带来了严重损失,刚投入运转的沙凡35千伏线路,结冰至碗口粗,由于经不起超载负荷,造成断线,断杆。上山公路不能通车。
多么严峻的春天。他知道:好事多磨。他知道:劲往一处使,就没有办不到的。他知道:愚公可以移山,宝山人,就可以开天辟地。
果然,在五月,冶金部批准了矿山建设规模及开拓运输方案以后,为加速矿山建设步伐,冶金部和广东省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以实施矿山建设计划。
为加强矿山的领导班子力量,任命武正之为矿革委会主任兼革委会党的领导核心小组组长,先后任命于进福,刘思明,周宽,蔡耿丰,林武森,郭训之,刘少力,李海涛等为矿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并从地区“五七”干校,省霄雪岭干校,曲江县干校调来了大批干部和专业管理人才,以加强矿山建设的领导。
借这一股东风,在采场当技术员的他挤进了铁矿办公室。生产科,从大门进去,一楼,往右拐,第三间,有他的一张办公桌。所以,他恨自己太胆小了,为什么不冲出去,再挡住她的去路,把要表白的一股脑儿塞给她。
但他相信,在纷纷扰扰的尘世,如果可以相知相识,相遇相爱是需要缘分的。所以,他相信这是一种严峻的考验,需要耐心和坚持,需要等待和期盼。可现在,她从眼皮底下溜走,干巴巴的,像上齿扣着下齿,软弱无力的说:不!
此时,有一位领导吩咐他上采场。五月的采场,浓雾早已散去,只有烈日,只有风沙漫卷,只有矿工们挥汗如雨的开采。他走向了采场,如果以此为背景,获得的爱情,是不是有些悲壮?
一块块矿石都可以自由,阳光,才有了呼吸的味道。
他走进了采场的值班室,碰巧,只有一个女矿工在。在采场一年有余,他,没有哪一个不认识的。这女的,是电焊班的。一个土生土长的矿子弟,常带有几分野性。她朝他浅浅的笑了笑,然后,一本正经的说,她的爸爸想见见他。其实,她的爸爸也在铁矿办公室,二楼。只要一见面,他总主动的上前打招呼,暗地里,给人的印象是会拍。
他思索了片刻,看了挂在墙上的生产任务报表,签了字。才拒绝。
他的脑海里只有一根马尾辫子。
第二天,上午。一个少女从草地的一条小路走了过来,那么朝气,蓬勃。他看见了她的脸庞,和莞尔的一笑。他走了出去,可,她又消失了。
这多像一列火车,不知所踪的消失了。他决定不再寻找。
第一回王教头私走延安府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乱自下生,不可训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作者之所深惧也。一部大书七十回,而开书先写高俅,有以也。
高俅来而王进去矣。王进者,何人也?不坠父业,善养母志,盖孝子也。
吾又闻古有“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之语,然则王进亦忠臣也。孝子忠臣,则国家之祥麟威凤、圆璧方珪者也。横求之四海而不一得之,竖求之百年而不一得之。不一得之而忽然有之,则当尊之,荣之,长跽事之。必欲骂之,打之,至于杀之,因逼去之,是何为也!王进去,而一百八人来矣,则是高俅来,而一百八人来矣。王进去后,更有史进。史者,史也。寓言稗史亦史也。夫古者史以记事,今稗史所记何事?殆记一百八人之事也。记一百八人之事,而亦居然谓之史也何居?从来庶人之议皆史也。庶人则何敢议也?庶人不敢议也。庶人不敢议而又议,可也?天下有道,然后庶人不议也。今则庶人议矣。何用知其天下无道?
曰:王进去,而高俅来矣。
史之为言史也,固也。进之为言何也?曰:彼固自许,虽稗史,然已进于史也。史进之为言进于史,固也。王进之为言何也?曰:必如此人,庶几圣人在上,可教而进之于王道也。必如王进,然后可教而进之于王道,然则彼一百八人也者,固王道之所必诛也。
一百八人,则诚王道所必诛矣,何用见王进之庶几为圣人之民?曰:不坠父业,善养母志,犹其可见者也。更有其不可见者,如点名不到,不见其首也;一去延安,不见其尾也。无首无尾者,其犹神龙欤?诚使彼一百八人者,尽出于此,吾以知其免耳,而终不之及也。一百八人终不之及,夫而后知王进之难能也。
不见其首者,示人乱世不应出头也;不见其尾者,示人乱世决无收场也。
一部书,七十回,一百八人,以天罡第一星宋江为主;而先做强盗者,乃是地煞第一星朱武。虽作者笔力纵横之妙,然亦以见其逆天而行也。
次出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盖檃栝一部书七十回一百八人为虎为蛇,皆非好相识也。何用知其为是檃栝一部书七十回一百八人?曰:楔子所以楔出一部,而天师化现恰有一虎一蛇,故知陈达、杨春是一百八人之总号也。
第二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此回方写过史进英雄,接手便写鲁达英雄;方写过史进粗糙,接手便写鲁达粗糙;方写过史进爽利,接手便写鲁达爽利;方写过史进剀直,接手便写鲁达剀直。作者盖特地走此险路,以显自家笔力,读者亦当处处看他所以定是两个人,定不是一个人处,毋负良史苦心也。
一百八人,为头先是史进一个出名领众,作者却少于华山上,特地为之表白一遍云:“我要讨个出身,求半世快活,如何肯把父母遗体便点污了。”
嗟乎!此岂独史进一人之初心,实惟一百八人之初心也。盖自一副才调,无处摆划,一块气力,无处出脱,而桀骜之性既不肯以伏死田塍,而又有其狡猾之尤者起而乘势呼聚之,而于是讨个出身既不可望,点污清白遂所不惜,而一百八人乃尽入于水泊矣。嗟乎!才调皆朝廷之才调也,气力皆疆场之气力也,必不得已而尽入于水泊,是谁之过也?
史进本题,只是要到老种经略相公处寻师父王进耳,忽然一转,却就老种经略相公外另变出一个小种经略相公来,就师父王进外另变出一个师父李忠来,读之真如绛云在霄,伸卷万象,非复一日之所得定也。
写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孔子云:“诗可以兴。”吾于稗官亦云矣。
打郑屠忙极矣,却处处夹叙小二报信,然第一段只是小二一个,第二段小二外又陪出买肉主顾,第三段又添出过路的人,不直文情如绮,并事情亦如镜,我欲刳视其心矣。
第三回赵员外重修文殊院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看书要有眼力,非可随文发放也。如鲁达遇着金老,却要转入五台山寺。
夫金老则何力致鲁达于五台山乎?故不得已,却就翠莲身上生出一个赵员外来,所以有个赵员外者,全是作鲁达入五台山之线索,非为代州雁门县有此一个好员外,故必向鲁达文中出现也。所以文中凡写员外爱枪棒、有义气处,俱不得失口便赞员外也是一个人。要知都向前段金老所云“女儿常常对他孤老说”句中生出来,便见员外只是爱妾面上着实用情,故后文鲁达下五台处,便有“好生不然”一语,了结员外一向情分。读者苟不会此,便自不辨牛马牡此矣。
写金老家写得小样,写五台山写得大样,真是史迁复生。
鲁达两番使酒,要两样身分,又要句句不相像,虽难矣,然犹人力所及耳。最难最难者,于两番使酒接连处,如何做个间架。若不做一间架,则鲁达日日将惟使酒是务耶?且令读者一番方了,一番又起,其目光心力亦接济不及矣。然要别做间架,其将下何等语,岂真如长老所云“念经诵咒,办道参禅”者乎?今忽然拓出题外,将前文使酒字面扫刷净尽,然后迤逦悠扬走下山去,并不思酒,何况使酒,真断鳌炼石之才也。
第四回小霸王醉入销金帐花和尚大闹桃花村
智深取却真长老书,若云“于路不则一日,早来到东京大相国寺”,则是二回书接连都在和尚寺里,何处见其龙跳虎卧之才乎?此偏于路投宿,忽投到新妇房里。夫特特避却和尚寺,而不必到新妇房,则是作者龙跳虎卧之才,犹为不快也。嗟乎!耐庵真正才子也。真正才子之胸中,夫岂可以寻常之情测之也哉!
此回遇李忠,后回遇史进,都用一样句法,以作两篇章法,而读之却又全然是两样事情,两样局面,其笔力之大不可言。
为一女子弄出来,直弄到五台山去做了和尚。及做了和尚弄下五台山来,又为一女子又几乎弄出来。夫女子不女子,鲁达不知也;弄出不弄出,鲁达不知也;和尚不和尚,鲁达不知也;上山与下山,鲁达悉不知也。亦曰遇酒便吃,遇事便做,遇弱便扶,遇硬便打,如是而已矣,又乌知我是和尚,他是女儿,昔日弄出故上山,今日下山又弄出哉?
鲁达、武松两传,作者意中却欲遥遥相对,故其叙事亦多彷佛相准。如鲁达救许多妇女,武松杀许多妇女;鲁达酒醉打金刚;武松酒醉打大虫;鲁达打死镇关西,武松杀死西门庆;鲁达瓦官寺前试禅杖,武松蜈蚣岭上试戒刀;鲁达打周通,越醉越有本事,武松打蒋门神,亦越醉越有本事;鲁达桃花山上,踏匾酒器,揣了滚下山去,武松鸳鸯楼上,踏匾酒器,揣了跳下城去。皆是相准而立,读者不可不知。
要盘缠便偷酒器,要私走便滚下山去,人曰:堂堂丈夫,奈何偷了酒器滚下山去?公曰:堂堂丈夫,做什么便偷不得酒器,滚不得下山耶?益见鲁达浩浩落落。
看此回书,须要处处记得鲁达是个和尚。如销金帐中坐,乱草坡上滚,都是光着头一个人;故奇妙不可言。
写鲁达蹭匾酒器偷了去后,接连便写李、周二人分赃数语,其大其小,虽妇人小儿;皆洞然见之,作者真鼓之舞之以尽神矣哉。
大人之为大人也,自听天下万世之人谅之;小人之为小人也,必要自己口中戛戛言之,或与其标榜之同辈一递一唱,以张扬之。如鲁达之偷酒器,李、周之分车仗,可不为之痛悼乎耶?
第五回九纹龙剪径赤松林鲁智深火烧瓦官寺
吾前言,两回书不欲接连都在丛林,因特幻出新妇房中销金帐里以间隔之,固也;然惟恐两回书接连都在丛林,而必别生一回不在丛林之事以间隔之,此虽才子之才,而非才子之大才也。夫才子之大才,则何所不可之有?
前一回在丛林,后一回何妨又在丛林?不宁惟是而已,前后二回都在丛林,何妨中间再生一回复在丛林?夫两回书不欲接连都在丛林者,才子教天下后世以避之法也。若两回书接连都在丛林,而中间反又加倍写一丛林者,才子教天下后世以犯之之法也。虽然,避可能也,犯不可能也,夫是以才子之名毕竟独归耐庵也。
吾读瓦官一篇,不胜浩然而叹。呜呼!世界之事亦犹是矣。耐庵忽然而写瓦官,千载之人读之,莫不尽见有瓦官也。耐庵忽然而写瓦官被烧,千载之人读之又莫不尽见瓦官被烧也。然而一卷之书,不盈十纸,瓦官何因而起,瓦官何因而倒,起倒只在须臾,三世不成戏事耶?又摊书于几上,人凭几而读,其间面与书之相去,盖未能以一尺也。此未能一尺之间,又荡然其虚空,何据而忽然谓有瓦官,何据而忽然又谓烧尽,颠倒毕竟虚空,山河不又如梦耶?呜呼!以大雄氏之书,而与凡夫读之,则谓香风萎花之句,可入诗料。
以北《西厢》之语而与圣人读之,则谓“临去秋波”之曲可悟重玄。夫人之贤与不肖,其用意之相去既有如此之别,然则如耐庵之书,亦顾其读之之人何如矣。夫耐庵则又安辩其是稗官,安辩其是菩萨现稗官耶?
一部《水浒传》,悉依此批读。
通篇只是鲁达纪程图也。乃忽然飞来史进,忽然飞去史进者,非此鲁达于瓦官寺中真了不得,而必借助于大郎也。亦为前者渭州酒楼三人分手,直至于今,都无下落,昨在桃花山上虽曾收到李忠,然而李忠之与大郎,其重其轻相去则不但丈尺而已也。乃今李忠反已讨得着实。而大郎犹自落在天涯,然则茫茫大宋,斯人安在者乎?况于过此以往,一到东京,便有豹子头林冲之一事,作者此时即通身笔舌,犹恨未及,其何暇更以闲心闲笔来照到大郎也?不得已,因向瓦官寺前穿插过去。呜呼!谁谓作史为易事耶!
真长老云:便打坏三世佛,老僧亦只得罢休。善哉大德!真可谓通达罪福相,遍照于十方也。若清长老则云:侵损菜园,得他压伏。嗟乎!以菜园为庄产,以众生为怨家,如此人亦复匡徒领众,俨然称师,殊可怪也。夫三世佛之与菜园,则有间矣。三世佛犹罢休,则无所不罢休可知也;菜园犹不罢休,然而如清长老者,又可损其毫毛乎哉!作者于此三致意焉。以真入五台,以清占东京,意盖谓一是清凉法师,一是闹热光棍也。
此篇处处定要写到急杀处,然后生出路来,又一奇观。
此回突然撰出不完句法,乃从古未有之奇事。如智深跟丘小乙进去,和尚吃了一惊,急道:“师兄请坐,听小僧说。”此是一句也。却因智深睁着眼,在一边夹道:“你说!你说!”于是遂将“听小僧”三字隔在上文,“说”
字隔在下文,一也。智深再回香积厨来,见几个老和尚“正在那里”怎么,此是一句也,却因智深来得声势,于是遂于“正在那里”四字下,忽然收住,二也。林子中史进听得声音,要问姓甚名谁,此是一句也,却因智深斗到性发,不睬其问,于是“姓甚”已问,“名谁”未说,三也。凡三句不完,却又是三样文情,而总之只为描写智深性急,此虽史迁,未有此妙矣。
第六回花和尚倒拔垂杨柳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此文用笔之难,独与前后迥异。盖前后都只一手顺写一事,便以闲笔波及他事,亦都相时乘便出之。今此文,林冲新认得一个鲁达,出格亲热,却接连便有衙内合口一事,出格斗气。今要写鲁达,则衙内一事须阁不起;要写衙内,则鲁达一边须冷不下,诚所谓笔墨之事,亦有进退两难之日也。况于衙内文中,又要分作两番叙出,一番自在林家,一番自在高府。今叙高府,则要照林家,叙林家则要照高府。如此百忙之中,却又有菜园一人跃跃欲来,且使此跃跃欲来之人乃是别位犹之可也,今却端端的的便是为了金翠莲三拳打死人之鲁达。呜呼!即使作者乃具七手八脚,胡可得了乎?今读其文,不偏不漏,不板不犯,读者于此而不服膺,知后世犹未能文也。
此回多用奇恣笔法。如林冲娘子受辱,本应林冲气忿,他人劝回,今偏倒将鲁达写得声势,反用林冲来劝,一也。阅武坊卖刀,大汉自说宝刀,林冲、鲁达自说闲话;大汉又说可惜宝刀,林冲、鲁达只顾说闲话。此时譬如两峰对插,抗不相下,后忽突然合笋,虽惊蛇脱兔,无以为喻,二也。还过刀钱,便可去矣,却为要写林冲爱刀之至,却去问他祖上是谁,此时将答是谁为是耶!故便就林冲问处,借作收科云:“若说时辱没杀人。”此句虽极会看书人亦只知其余墨淋漓,岂能知其惜墨如金耶!三也。白虎节堂,是不可进去之处,今写林冲误入,则应出其不意,一气赚入矣,偏用厅前立住了脚,屏风后堂又立住了脚,然后曲曲折折来至节堂,四也。如此奇文,吾谓虽起史迁示之,亦复安能出手哉!
打陆虞候家时,“四边邻舍都闭了门”,只八个字,写林冲面色、衙内势焰都尽。盖为藏却衙内,则立刻齑粉;不藏衙内,则即日齑粉,既怕林冲,又怕衙内,四边邻舍都闭门,真绝笔矣。
第七回林教头刺配沧州道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此回凡两段文字,一段是林武师写休书,一段是野猪林吃闷棍;一段写儿女情深,一段写英雄气短,只看他行文历历落落处。
第八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
今夫文章之为物也,岂不异哉!如在天而为云霞,何其起于肤寸,渐舒渐卷,倏忽万变,烂然为章也!在地而为山川,何其迤逦而入,千转百合,争流竞秀,窅冥无际也!在草木而为花萼,何其依枝安叶,依叶安蒂,依蒂安英,依英安瓣,依瓣安须,真有如神镂鬼簇、香团玉削也!在鸟兽而为翚尾,何其青渐入碧,碧渐入紫,紫渐入金,金渐入绿,绿渐入黑,黑又入青,内视之而成彩,外望之而成耀,不可一端指也!凡如此者,岂其必有不得不然者乎?夫使云霞不必舒卷,而惨若烽烟,亦何怪于天?山川不必窅冥,而止有坑阜,亦何怪于地?花萼不必分英布瓣,而丑如榾柮;翚尾不必金碧间杂,而块然木鸢,亦何怪于草木鸟兽?
然而终亦必然者,盖必有不得不然者也。至于文章,而何独不然也乎?自世之鄙儒,不惜笔墨,于是到处涂抹,自命作者,乃吾视其所为,实则曾无异于所谓烽烟、坑阜、榾柮、木鸢也者。
呜呼!其亦未尝得见我施耐庵之《水浒传》也。
吾之为此言者,何也?即如松林棍起,智深来救,大师此来,从天而降,固也;乃今观其叙述之法,又何其诡谲变幻,一至于是乎!第一段先飞出禅杖,第二段方跳出胖大和尚,第三段再详其皂布直裰与禅杖戒刀,第四段始知其为智深。若以《公》、《谷》、《大戴》体释之,则曰:先言禅杖而后言和尚者,并未见有和尚,突然水火棍被物隔去,则一条禅杖早飞到面前也;先言胖大而后言皂布直裰者,惊心骇目之中,但见其为胖大,未及详其脚色也;先写装束而后出姓名者,公人惊骇稍定,见其如此打扮,却不认为何人,而又不敢问也。盖如是手笔,实惟史迁有之,而《水浒传》乃独与之并驱也。
又如前回叙林冲时,笔墨忙极,不得不将智深一边暂时阁起,此行文之家要图手法干净,万不得已而出于此也。今入此回,却忽然就智深口中一一追补叙还,而又不肯一直叙去,又必重将林冲一边逐段穿插相对而出,不惟使智深一边不曾漏落,又反使林冲一边再加渲染,离离奇奇,错错落落,真似山雨欲来风满楼也。
又如公人心怒智深,不得不问,才问,却被智深兜头一喝,读者亦谓终亦不复知是某甲矣,乃遥遥直至智深拖却禅杖去后,林冲无端夸拔杨柳,遂答还董超、薛霸最先一问。疑其必说,则忽然不说;疑不复说,则忽然却说。
譬如空中之龙,东云见鳞,西云露爪,真极奇极恣之笔也。
又如洪教头要使棒,反是柴大官人说且吃酒,此一顿已是令人心痒之极,乃武师又于四五合时跳出圈子,忽然叫住,曰除枷也;乃柴进又于重提棒时,又忽然叫住。凡作三番跌顿,直使读者眼光一闪一闪,直极奇极恣之笔也。
又如洪教头入来时,一笔要写洪教头,一笔又要写林武师,一笔又要写柴大官人,可谓极忙极杂矣。乃今偏于极忙极杂中间,又要时时挤出两个公人,心闲手敏,遂与史迁无二也。
又如写差拔陡然变脸数语,后接手便写陡然翻出笑来数语,参差历落,自成谐笑,皆所谓文章波澜,亦有以近为贵者也。若夫文章又有以远为贵也者,则如来时飞杖而来,去时拖杖而去,其波澜乃在一篇之首与尾。林冲来时,柴进打猎归来,林冲去时,柴进打猎出去,则其波澜乃在一传之首与尾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凡如此者,此所谓在天为云霞,在地为山川,在草木为花萼,在鸟兽为翚尾,而《水浒传》必不可以不看者也。
此一回中又于正文之外,旁作余文,则于银子三致意焉。如陆虞候送公人十两金子,又许干事回来,再包送十两,一可叹也;夫陆虞候何人,便包得十两金子?且十两金子何足论,而必用一人包之也?智深之救而护而送到底也,公人叫苦不迭,曰却不是坏我勾当,二可叹也;夫现十两赊十两便算一场勾当,而林冲性命曾不足顾也。又二人之暗自商量也,曰“舍着还了他十两金子”,三可叹也;四人在店,而两人暗商,其心头口头,十两外无别事也。访柴进而不在也,其庄客亦更无别语相惜,但云你没福,若是在家,有酒食钱财与你,四可叹也;酒食钱财,小人何至便以为福也?洪教头之忌武师也,曰“诱些酒食钱米”,五可叹也;夫小人之污蔑君子,亦更不于此物外也。武师要开枷,柴进送银十两,公人忙开不迭,六可叹也;银之所在,朝廷法网亦惟所命也,洪教头之败也,大官人实以二十五两乱之,七可叹也;银之所在,名誉、身分都不复惜也。柴、林之握别也,又捧出二十五两一锭大银,八可叹也;虽圣贤豪杰,心事如青天白日,亦必以此将其爱敬,设若无之,便若冷淡之甚也。两个公人亦赍发五两,则出门时,林武师谢,两公人亦谢,九可叹也;有是物即陌路皆亲,豺狼亦顾,分外热闹也。差拨之见也,所争五两耳,而当其未送,则满面皆是饿纹,及其既送,则满面应做大官,十可叹也;千古人伦,甄别之际,或月而易,或旦而易,大约以此也。
武师以十两送管营,差拨又落了五两,止送五两,十一可叹也;本官之与长随可谓亲矣,而必染指焉,谚云:“掏虱偷脚”,比比然也。林冲要一发周旋开除铁枷,又取三二两银子,十二可叹也;但有是物,即无事不可周旋,无人不顾效力也。满营囚徒,亦得林冲救济,十三可叹也;只是金多分人,而读者至此遂感林冲恩义,口口传为美谈,信乎名以银成,无别法也。嗟乎!
士而贫尚不闭门学道,而尚欲游于世间,多见其为不知时务耳,岂不大哀也哉!
第九回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陆虞候火烧草料场
夫文章之法,岂一端而已乎?有先事而起波者,有事过而作波者,读者于此,则恶可混然以为一事也。夫文自在此而眼光在后,则当知此文之起,自为后文,非为此文也;文自在后而眼光在前,则当知此文未尽,自为前文,非为此文也。必如此,而后读者之胸中有针有线,始信作者之腕下有经有纬。
不然者,几何其不见一事即以为一事,又见一事即又以为一事,于是遂取事前先起之波,与事后未尽之波,累累然与正叙之事,并列而成三事耶?
如酒生儿李小二夫妻,非真谓林冲于牢城营有此一个相识,与之往来火热也,意自在阁子背后听说话一段绝妙奇文,则不得不先作此一个地步,所谓先事而起波也。
如庄家不肯回与酒吃,亦可别样生发,却偏用花枪挑块火柴,又把花枪炉里一揽,何至拜揖之后向大多时,而花枪犹在手中耶?凡此,皆为前文几句花枪挑着葫芦,逼出庙中挺枪杀出门来一句,其劲势犹尚未尽,故又于此处再一点两点,以杀其余怒。故凡篇中如搠两人后杀陆谦时,特地写一句把枪插在雪地下,醉倒后庄家寻着踪迹赶来时,又特地写一句花枪亦丢在半边,皆所谓事过而作波者也。
陆谦、富安、管营、差拨四个人坐阁子中议事,不知所议何事,详之则不可得详,置之则不可得置。今但于小二夫妻眼中、耳中写得“高太尉三字”
句,“都在我身上”句,“一帕子物事,约莫是金银”句,“换汤进去,看见管营手里拿着一封书”句,忽断忽续,忽明忽灭,如古锦之文不甚可指,断碑之字不甚可读,而深心好古之家自能于意外求而得之,真所谓鬼于文、圣于文者也。
杀出庙门时,看他一枪先搠倒差拨,接手便写陆谦一句;写陆谦不曾写完,接手却再搠富安;两个倒矣,方翻身回来,刀剜陆谦,剜陆谦未毕,回头却见差拨爬起,便又且置陆谦,先割差拨头挑在枪上;然后回过身来,作一顿割陆谦富安头,结做一处。以一个人杀三个人,凡三四个回身,有节次,有间架,有方法,有波折,不慌不忙,不疏不密,不缺不漏,不一片,不烦琐,真鬼于文、圣于文也。
旧人传言:昔有画北风图者,盛暑张之,满座都思挟纩;既又有画云汉图者,祁寒对之,挥汗不止。于是千载啧啧,诧为奇事。殊未知此特寒热各作一幅,未为神奇之至也。耐庵此篇独能于一幅之中,寒热间作,写雪便其寒彻骨,写火便其热照面。昔百丈大师患疟,僧众请问:“伏惟和上尊候若何?”丈云:“寒时便寒杀阇黎,热时便热杀阇黎。”今读此篇,亦复寒时寒杀读者,热时热杀读者,真是一卷“疟疾文字”,为艺林之绝奇也。
阁子背后听四个人说话,听得不仔细,正妙于听得不仔细;山神庙里听三个人说话,听得极仔细,又正妙于听得极仔细。虽然,以阁子中间、山神庙前,两番说话偏都两番听得,亦可以见冤家路窄矣!乃今愚人犹刺刺说人不休,则独何哉?
此文通篇以火字发奇,乃又于大火之前,先写许多火字,于大火之后,再写许多火字。我读之,因悟同是火也,而前乎陆谦,则有老军借盆,恩情朴至;后乎陆谦,则有庄客借烘,又复恩情朴至;而中间一火,独成大冤深祸,为可骇叹也。夫火何能作恩,火何能作怨,一加之以人事,而恩怨相去遂至于是!然则人行世上,触手碍眼,皆属祸机,亦复何乐乎哉!
文中写情写景处,都要细细详察。如两次照顾火盆,则明林冲非失火也;上拖一条棉被,则明林冲明日原要归来,今止作一夜计也。如此等处甚多,我亦不能遍指,孔子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矣。”
第十回朱贵水亭施号箭林冲雪夜上梁山
旋风者,恶风也。其势盘旋,自地而起,初则扬灰聚土,渐至奔沙走石,天地为昏,人兽骇窜,故谓之旋。旋音去声,言其能旋恶物聚于一处故也。
水泊之有众人也,则自林冲始也,而旋林冲入水泊,则柴进之力也。名柴进曰“旋风”者,恶之之辞也。然而又系之以“小”,何也?夫柴进之于水泊,其犹青萍之末矣,积而至于李逵亦入水泊,而上下尚有定位,日月尚有光明乎耶?故甚恶之,而加之以“黑”焉。夫视“黑”,则柴进为“小”矣,此“小旋风”之所以名也。
此回前半只平平无奇,特喜其叙事简净耳。至后半写林武师店中饮酒,笔笔如奇鬼,森然欲来搏人,虽坐闺阁中读之,不能不拍案叫哭也。
接手便写王伦疑忌,此亦若辈故态,无足为道。独是渡河三日,一日一换,有笔如此,虽谓比肩腐史,岂多让哉!
最奇者,如第一日,并没一个人过;第二日,却有一伙三百余人过,乃不敢动手;第三日,有一个人,却被走了,必再等一等,方等出一个大汉来。
都是特特为此奇拗之文,不得忽过也。
处处点缀出雪来,分外耀艳。
我读第三日文中,至“打拴了包裹撇在房中”句,“不知趁早,天色未晓”句,真正心折耐庵之为才子也。后有读者,愿留览焉。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表白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