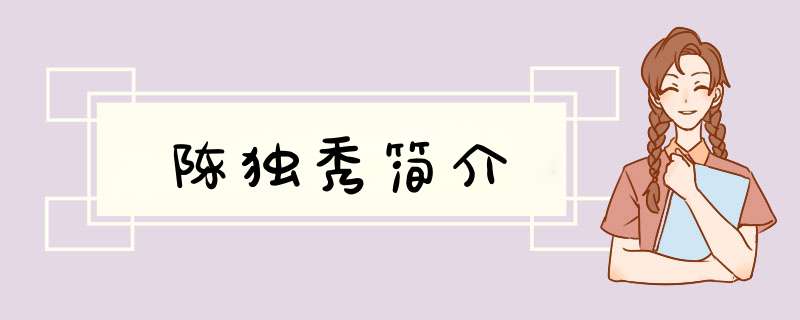
陈独秀简介
钟繇,1879年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北的一个小家庭,中国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他也是中国***的创始人和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之一,五四运动的领袖。陈独秀是中国文化启蒙的先驱。我们先来看看陈独秀的介绍。
陈独秀
陈独秀的一生比较坎坷,经历了非常丰富的传奇人生。两岁时,父亲早逝,他由爷爷和大哥抚养。他在家自学了《四书》和《五经》。曾经有人说,陈独秀不长大就会变成一条蛇。这句话也成为了事实,印证了他一生的辉煌。17岁的陈独秀在1896年成为了一名学者,但是他没有考上。次年考入杭州求是书院,学习造船技术和法语。同年,与高晓岚结婚。
1901年,陈独秀赴日本留学,1902年回国,组织青年励志会。同年9月,陈独秀再次赶赴日本求学从军。陈独秀留学期间,受西方社会主义影响,陈独秀等人强行剪掉辫子,遣送回国。
陈独秀文学方面也有不少成就。1904年,陈独秀等人创立白话文《安徽俗话报》。之后,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陈独秀等人开始研究社会主义,宣传社会主义。1927年,陈独秀被剥夺了在中国***的领导地位,两年后被开除党籍。晚年,陈独秀长期隐居,低调行事。1942年,他因病去世,享年63岁。这是陈独秀的简介,这是陈独秀的生平。
陈独秀留给后人的生活如何?
陈独秀有四个妻子。虽然有一个潘兰珍没有为陈独秀生孩子,但其他三个都为陈独秀生了很多后代,他的后代又生了后代,所以陈独秀的后代也很多。陈独秀的后代包括他的五个儿子和三个女儿,虽然梅直到去世才承认陈独秀的儿子。
陈独秀后裔——陈乔年
陈红,陈独秀的后代,也是陈独秀的孙女和她最小的儿子陈鹤年的女儿。当陈红描述他们后代的生活时,他用一个简单的句子来总结:无尽的悲伤。北京中医药大学生物学教授陈红,说话时举止温柔,透露着知识女性的内涵。
从她的口述中我们知道,陈独秀的后人并没有因为父亲是伟人而提高自己的地位。相反,正是因为他们的父亲有这样的地位,他经常被诽谤和冤枉。据她说,陈独秀从小没有父亲,不知道什么是父爱。所以他和陈乔年一出生,就没有给他们很多父爱,又长年奔波,这让陈独秀和他的孩子很奇怪。陈独秀与高君曼私奔一事,直接影响了陈延年的婚姻观。后来因为陈独秀的关系,陈家被开除,兄弟不得不离家去上海。但是,因为他们的父亲不能背叛他们的母亲和姑姑在一起的事实,他们决定独自住在外面,晚上睡在图书馆的地板上,白天工作。生活很惨淡。
陈松年,陈延年和陈松年同父异母的兄弟,一生悲惨。他出生不久母亲就去世了,父亲也没怎么管教他。他仅有的两个兄弟,陈延年17岁英年早逝,陈乔年26岁去世。然后受到各种打击。
所以陈独秀的后人过得很苦。
陈独秀传记探索与解密
是图文并茂,精选了30多张陈独秀不同时期的照片。作者以流畅的笔触,再现了陈独秀昔日的风貌。这本书不仅包括他的政治观点和学术建设,还包括他的日常生活,爱情事务和他的朋友。这本书是关于陈独秀的第一手资料。
陈独秀传
这本书出版于2009年。它使用平装本和16开设计来装订这本书。这本书在查阅大量资料后,以翔实的史料和扎实的写作功底,生动地叙述了陈独秀的一生在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举世闻名,反复无常,充满大悲大喜。这本书的内容包括叛逆性格的发起者、慷慨大方的年轻人、中国***的创始人和第一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指挥、***内的反对派以及其他不同身份的陈独秀。
的内容都是围绕陈独秀写的。陈独秀是中国***的创始人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也是五四运动的总指挥。陈独秀曾被指责为汉奸、反共产国际、反革命等。并成为党内最早也是最大的负面人物。这一事件被称为CCP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大的冤案,直到后来才被拉平。
这本书的作者是陈黎明。陈黎明,1938年出生于湖南,中共党员,国家一级作家。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当过报社编辑、记者。现在是世界华人文化协会副会长。他有许多作品,《陈独秀传》是其中之一。
1、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充满了强烈的革故更新的精神,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战斗口号,不容许任何人对文学革命进行匡正,没有丝毫的温和忍让的色彩。
并“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愿“拖四十二生大炮,为之前躯”,表现出彻底的革命坚定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2、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不仅注意语言形式的改革,而且十分重视文学内容的革新。他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即有文学革命的内容问题,又有文学革命的形式问题。
既不仅主张反对旧文学的形式上的雕琢、铺张、艰涩等弊病,并且反对阿谀、陈腐、迂晦的封建文学内容,积极主张以白话文学为“正宗”,建设以平易、抒情、新鲜、立诚、明了、通俗为特征的“国民”、“写实”、“社会”、的新文学。
3、陈独秀把文学革命和政治革命结合起来,认为中国政治界的革命之所以虎头蛇尾,主要因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漠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
所以“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这不仅说明了文学革命同政治革命关联着,而且也说明了文学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必要准备。
4、到了一九一九年底,随着陈独秀的世界观的转变,他的文学革命主张也增进了新的因素。他进一步认识到文学改革同时代进步的关系,提出了“应该以现在及将来社会生活进步所需要的文学道德。
便不得不抛弃因袭的文学道德中不适用的部分”,使文学适应“民众运动的社会改造”的需要和表现“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的需要。
扩展资料
简介: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今安庆)人。
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革命家与改革家、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伟大的启蒙思想家。
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五四运动的思想指导者,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
是中国***最重要的创始人。是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最主要的***,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深刻总结、反思苏联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人。
―陈独秀
http://wwwjiaodongnet 2007-10-17 14:33:02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一个历史上少有的东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碰撞、融合时期。保持着文化开放心态的鲁迅此时也走近了佛教,他以“拿来主义”以我为主的精神和勇气研读佛经,这对他的诸多人生观念乃至艺术创作都产生了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有人说他“在通往地狱的通路上……成为佛教的圣者”,是“深山苦行的一位佛神”。
(一)
佛教自东渐以来,不断与东方固有文化相冲突融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世俗化宗教。步入近代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衰亡与危机大乘佛教以能促进民众道德,为“普渡众生”而不惜牺牲、勇于抗争的精神,深深地吸引着正在苦苦思索中国社会出路的一代民主志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无不受到大乘教义的启发与影响,各自建立起了相对进步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
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鲁迅也走近了佛教。在其幼年,他就被家人送入长庆寺龙祖和尚处做徒弟法号“长庚”,在这里,鲁迅初步接触了完全世俗化的佛教。东渡日本之后,鲁迅又受到章太炎的影响进一步理性地认识了佛教。1907年前后,章太炎曾在《民报》上长篇连牍地发表了论佛教的文章,从革命的实际需求出发,对大乘教义做了合乎逻辑的生发他宣称:“华严宗所说,要在普渡众生,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于人,在道德上最为有益。这法相宗所说,就是万法唯心,一切有形的色相,无形的法尘,总是幻见幻想,并非实在真有……要有这种信仰,才得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可干得事来”。他还认为:“佛教最恨君权,大乘戒律,都说,‘国王暴虐,菩萨有权,应该废黜’”,“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的东西,必要除去”,因此,他坚持提倡佛教,“为社会道德上起见固是重要;为我们革命军的道德上起见,亦是重要。”这些闪烁着革命光彩的思想深深打动了鲁迅影响着他对佛教的认识。他曾说:“佛教崇高,凡有识者所同可,何怨于震旦,而汲汲灭其法。若谓无功于民,则当称自省民德之堕落;欲与挽救,方昌大之不暇,胡毁裂也”。鲁迅也正是立足于佛教能影响国民的精神素质,能提高民众道德去高度评价佛教的,这种认识几乎和章太炎如出一辙。然而,鲁迅对佛教的这种认识并不完全同于章太炎。在鲁迅早期思想中,“立人”是其基本目标,他认为“生存两者,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求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由这种“立人”的目标出发,鲁迅此时思想的兴奋点始终集中在那些能满足人们所必有的“形上之需求”,且能够担负起启蒙民众任务的文艺和宗教上。他认为“宗教由来,本向上之民所自建,纵对象有多一虚实之别,而充足人心向上之需要则同然”。因此,他十分看重佛教,就更是必然的了。
辛亥革命之后,整个社会形势并未取得实质性变化,“内骨子是依旧的”,而且,“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鲁迅日益陷入了悲观和凄苦的煎熬。这种悲观和凄苦不仅源于社会形势的恶化,痛苦的人生境遇,无望的婚姻和多病的身体都深深地加深了他的失望。“鲁迅那时自号俟堂,本来也就是古人的侍死堂的意思,或者要引经传,说出了‘君了居易以俟命’亦无不可,实在却没有那样曲折,只是说‘我等着,任凭什么都请来吧’”。他的这种悲观心态恰好和主张解脱人生痛苦的佛教又一次获得了契合,由这种深刻的情感动力驱使,鲁迅在“民三以后,开始看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考其日记,1914年他即购得佛经八十余种,数量相当惊人,1917年9月22日,其日记还有“往图书分馆借《涅般木经》”的记录,此次读经对鲁迅影响极为巨大,它成为一种深刻的文化因素深深地积淀在他的思想深处,持续地发挥着影响。这在鲁迅的前期思想中表现尤为突出。
(二)
鲁迅曾对许寿裳说:“释伽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这正是鲁迅研读佛经的彻悟与心得,也是我们理解鲁迅与佛教关系的切入点。由此出发,我们才能全面而准确地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更深刻理解佛教思想在鲁迅思想中所起的特殊作用,更充分发掘一代“文化巨人”所具有的丰富内涵。
人生最重要的莫过于生命的生存与死亡,这既是人类永恒的母题,也是佛教产生的动因之一。在佛教看来,生存即是“苦”,这是佛法的根本出发点,是其“首谛”。老苦、病苦、死苦、怨憎苦……真是“苦海无边”,这种生即“苦”的观念对鲁迅的思想是有影响的,他曾说:“我想,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如果说,佛教的生即“苦”是引导人们出世的理由,那么在鲁迅这里则直接引发了他对人间苦的“诅咒”。考察鲁迅一生的斗争历程,可以说痛苦一直伴随他,然而生存的痛苦并没有使其长期消沉。幼年家道的中落,使其更清醒地认识了世态炎凉,积累了他对旧社会的否定性情绪。正是首先深刻经验和品味了人生的诸种痛苦,鲁迅才以一种异常冷峻的心态去观察世道人心,才激发出抗争的力量和生命的战斗光芒开始了他与现实抗争的“圣者”之路。
佛教不仅认为“一切皆苦”,而且认为“我法”也“两空”,即无论是客观事物还是自己的生命皆不是实有,只是’空”而矣。这种生命即是“空”,即是“无的观念也曾一度占据了鲁迅的心灵,常常感到惟“虚无”才是实有。他曾这样表白自己的心态:“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种在痛苦中深深体验生命的至“空”与至“无”,在至“空”与至“无”之境中痛苦而无奈地咀嚼自己的灵魂所达到的哲学境界,就非佛教莫属。可以说,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真正通过体验这种生存的虚无而去反思个体生命的真正意义,并不断作出很难的选择,以摆脱这种生命的生存处境鲁迅还是第一人,这不能不说他是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
尽管鲁迅常常感到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去肉博黑暗“执着现世,而求精进”,是他评价别人的话,也是其一生的生动写照。“精进”思想是佛教“道谛”的核心是通向涅般木的正道:“但为断一切烦恼故,而行精进但为知一切众生界故,而行精进……”。熊十力先生在总结佛教的“精进”思想时说:“经说精进,略有五种。一被甲精进,如着甲入阵,即无所畏,有大威势次加行精进,坚固其心,长自策励。三无吓精进,谓不自轻蔑,亦无怯惧。四无退精进。谓遭苦不屈,坚猛其志。五无足精进,虽功已成,更祈胜进,无有止境容肩故”。这种“精进”思想在中国近代影响巨大,它深深地塑造了一代革命志士勇于牺牲的品德和敢于抗争的意志,如谭嗣同杀身取法,章太炎数次被捕而斗志昂扬。同样,这种“精进”思想也毫不例外地影响了鲁迅,成为其终生抗争、奋斗的一个思想支点。他在《这样的战士》中所塑造的在无物之阵中大踏步走,高举投枪的勇士,尽管老衰,寿终却“加行精进”,“无有止境”,高举着他的投枪;《过客》中匆匆前行“遭苦不屈”的苦行者形象,无不带着作者的影子,体现了这种“精进”的精神。
在死亡的问题上,佛教认为普通生命的死亡之路仅是一种“六道轮回”,就是生命的天堂、地狱等六道中不停流转、循环,而难脱诸种劫难。鲁迅曾说;“大家所相信的死后状态,更助成了死的随便。穷人们是大抵认为死后就去轮回的,根源出于佛教。佛教所说的轮回当然手续繁重,并不这么简单,但穷人往往无学,所以不明白,这就是使死罪犯人绑赴法场时大叫‘二十年后又一条好汉’,而无惧然的原因”。“二十年后又一条好汉”正是阿Q临死之前的喊叫,然而阿Q却不可能升入天堂的,他的死仅仅是生命的消失。“轮回”观念在《阿Q正传》中却具有更多的历史内容和悲剧内涵,暗示出生存于近代社会中的生命个体无路可走的悲剧。于是,死亡便变成一种不可回避的选择。当鲁迅理性地审视中国历史的时候,他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所谓的历史只是一种循环,一种“轮回”,难有进步可言,“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因此,他深为生存于此种历史“轮回”中个体不可逆转的悲剧命运感到焦虑,《故乡》中水生和宏儿就难免会重复闰土和“我”的悲剧命运,《孤独者》中魏连殳的死,并不代表着进步或抗争,仅仅是其祖母“死”的重复,是悲惨命运的又一次“轮回”罢了。所以,尽管鲁迅小说刻画的仅是近代中国的社会历史,但作品的深层所指却超越了特定的时空局限,完成了对向来如此的历史与文化的整体反思,具有深邃的文化内蕴和丰富的历史内涵。也因为此,鲁迅小说对个体悲剧命运的思考达到了一种本体性的哲学高度。
“六道轮回”是不能真正摆脱人世的诸种劫难的。那么,真正的超脱之路是什么呢佛教认为是“涅般木”,即此岸现实生命与意识的寂灭,是自我的终解,也是一种永恒境界的开始。鲁迅曾在《野草》中不止一次地提过“大欢喜”,这种“大欢喜”就是对现实生命的否定,对死亡的向往,是他对“涅般木”的渴望。在佛教那里,“涅般木”是由此岸到达彼岸理想境界的必由之路,而鲁迅则通过领悟“涅”思想透悟了生命的本质与“死亡”的意义,使其不惮于前驱,能够不断地否定旧有的自我,深刻地进行自我解剖。可以这样认为,在鲁迅这里,“涅般木”即是一种“更生”。也由于这种独特的“涅般木”观念的存在,便塑造了鲁迅思想中深刻的自虐意识,而一个未曾真正品味旧有生命“死亡”之独特意义的人,是绝难产生这种自虐情绪的。
鲁迅自己曾说:“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不难看出,这些自虐意识正是鲁迅深刻体验生命“涅般木”之后的产物,是他通向“涅般木”的心灵之路,因而这些自虐意识同时也就具有了“精进”的含义。鲁迅的自虐意识并不仅是表面上的“生命从速消磨”,而是深刻体现了他的自我反醒,不断反抗,乃至勇于复仇的精神,《死火》中以“死”相抗争,《墓碣文》中“择心自食,欲知本味”的创痛酷烈无不体现了“死亡”即抗争,即复仇、即更生的特点。正是这种独特的自虐意识使鲁迅成为现代历史上的一个复杂的存在,它不断迫使鲁迅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对旧有的价值观念进行近乎残烈地反思、否定、更新,使他的每一步前进都充满了生命的严酷与悲壮。
(三)
马克思曾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但他同时又说:“宗教是人们的鸦片”。宗教的这种两重性就决定了对其进行价值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接受者自身的思想状况和实际需求。因此,随着鲁迅思想的发展与认识的深化,他对佛教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20年代中期以后,鲁迅基本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于这种思想认识的变化,鲁迅更加全面辩证地认清了佛教的价值与历史作用,他一方面充分肯定和吸取了佛教思想中诸多的积极性因素,另一方面则自觉地对佛教思想中消极乃至倒退的因素加以否定和排斥。
首先,鲁迅否定了佛教的出世思想。作为一种宗教,佛教在本质上则是出世的,它所追求的亦是远离现世的理想彼岸,而这恰好和鲁迅所一贯坚持的积极入世抗争的现实主义精神是相左的。因此,在鲁迅看来,佛教的出世思想是虚幻的,缥缈的,不足取的,是不能适应现实的斗争的。他曾对别人说:“其实,偌大的中国,即使一月出几本关于宗教学的书,那里算多呢。但这些理论,此刻不适用。所以我认为,先生所研究的宗教学,恐怕暂时要变成聊以自娱的东西。无论‘打倒宗教’或‘扶起宗教’时,都没有别人会研究”,就深刻反映了上述思想。也因为此,鲁迅对反动统治阶级大肆宣扬出世思想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对他们一味求神拜佛而借以自欺欺人来逃避责任,回避现实斗争的社会现象进行过深刻的揭露和猛烈的批判,这在《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等文中都有鲜明的体现。他认为:“一到求神拜佛,可就玄虚之极了,有益或是有害,一时就找不出分明的结果,它可以令人更长久的麻醉自己”,在这里,鲁迅已清醒地看到,佛教的出世思想正是引导人们逃避斗争的根源。因此,批判佛教的出世思想已经势在必行。这也正是鲁迅为什么反对章太炎晚年所倡导“佛法救国”的根本原因。
其次,鲁迅还以深刻的见地批判了“三教同源”。和其他宗教一样,最初的佛教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下层民众对“现实的苦难的抗议”,然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却不断受到统治势力的干涉,佛教自身也不断改变以适应政治权力的要求。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情况更是如此,中国历史上大规模地灭佛事件就是对它进行强制改造,而儒、释、道“三教”的合流则是对佛教进行的最深刻改造,合流的结果使佛教和儒、道一样,更易于为统治者所利用,成为控制人民的思想工具。鲁迅正是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他才特别指出:“佛教初来时便大被排斥,一到理学先生谈禅,和尚作诗的时候,‘三教同源’的机运就成熟了。听说现在悟善社里的神主已经有了五块: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耶稣基督,漠哈默德”。鲁迅对佛教认识的深化还进一步表现在他对主张通过自我的严格的道德自律、苦修苦行以获得个体解脱的小乘佛教作了更充分地肯定。他说:“我对于佛教先有一种偏见,以为坚苦的小乘倒是佛教,待到饮酒食肉的阔人富翁,只要吃一餐素,便可以称为居士,算为信徒。虽然美其名曰大乘,流播广远,然而这教却因为容易信奉,因而变为浮滑,或者竟等于零了”。他又说:“释迦牟尼出世以后,割肉喂鹰,投身饲虎的是小乘,渺渺茫茫地说教的倒是大乘……”这当然不能断定是鲁迅对“大乘”的否定,他主要是对那些假“大乘”之名的投机者、无特操者进行辛辣的抨击和否定。然而在“大乘”与“小乘”之间,鲁迅越来越推崇“小乘”,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这是有深刻的根源的。首先,鲁迅对小乘佛教的这种高度评价是和他一贯注重严格的道德自律相联系的。小乘佛教是以严格的道德自律而著称的,它认为只有通过个体的苦修苦行才能脱离苦海,因此,它要求信徒们必须不断地进行自我道德反醒,并严格律己,以期达到“净心”。而中国文化传统中恰恰缺少这种严格的自律精神,所具有的仅是一种“他律”。人们道德观念的形成靠得不是自我道德反醒,而是外在伦理的强制, 这就造成中国国民道德观念以外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此一时彼一时”,阿Q、高老夫子,莫不如此——缺少诚实,在鲁迅看来,这正是国民性最大的病症之一。不仅如此,也因为缺乏这种道德自律精神,中国国民便难形成坚定的道德信念,从而也难以形成独立的道德品格,最易产生一种从众心理,鲁迅曾经感慨地说:“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便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正是深感这种道德自律的重要性,鲁迅才十分推崇小乘佛教。其次,鲁迅对小乘佛教的推崇和其自我牺牲精神是相一致的。小乘佛教非常注重自我牺牲精神,其最著名的自我牺牲的故事即鲁迅所提的释迦牟尼“割肉喂鹰”和摩诃国王子“舍身饲虎”。早在’五四”时期鲁迅就曾说:“几位读者怕要生气,说,‘中国时常有将性命去殉他主义的人,中华民国以来,也因为主义上死了多少烈士,你何以一笔抹杀吓!’这话是真的。我们从旧的外来思想说罢,六朝的确有许多焚身的和尚,唐朝也有过砍过臂膊布施无赖的和尚”。在这里,与其说是鲁迅对自我牺牲精神的高度赞扬,到不如说是他对自我牺牲精神的积极认同,这是鲁迅伟大人格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其一生不渝的道德信念,也是他和小乘佛教发生共鸣的一个思想基础。
在谈到自己的思想时,鲁迅曾说:“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如果说,大乘佛教“普渡众生”的精神接近于鲁迅思想的“人道主义”,那么,小乘佛教的苦修苦行则更倾向于鲁迅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可以说,鲁迅对小乘佛教的高度评价,是和他思想深处的“个人主义”相沟通,相契合的。这是他肯定小乘佛教的另一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鲁迅的精神气质和人格特点的许多方面和小乘佛教有着深刻的联系,这也是内山完造称鲁迅为“苦行的佛神”的主要原因。当然,我们说鲁迅与小乘佛教有着深刻的联系,并不是指鲁迅是完合接受小乘佛教的,是无条件的。实际上,鲁迅对小乘佛教的接受是有所选择,有所批判的,极为明显的是他批判了小乘佛教的“地狱说”和“因果报应说”,他说:“我常常感叹,印度小乘教的方法何等厉害:它立了地狱之说,借着和尚,尼姑,念佛老妪的嘴来宣扬,恐吓异端,使心意不坚定者害怕。那诀窍是在说报应并非眼前,却在将来百年之后,至少也须到锐气脱尽之时。这时候你已经不能动弹了,只好听别人摆布,流下鬼泪,深悔生前之妄出锋头;而且这时候,这才认识阎罗大王的尊严和伟大”。鲁迅认为:“这些信仰,也许是迷信罢”。他又指出:“这些老玩意,也只好骗骗极端老实人”。这就表明,鲁迅对佛教的态度是辩证的,以“我”为主的,他与佛教的关系也应作如是观。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表白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