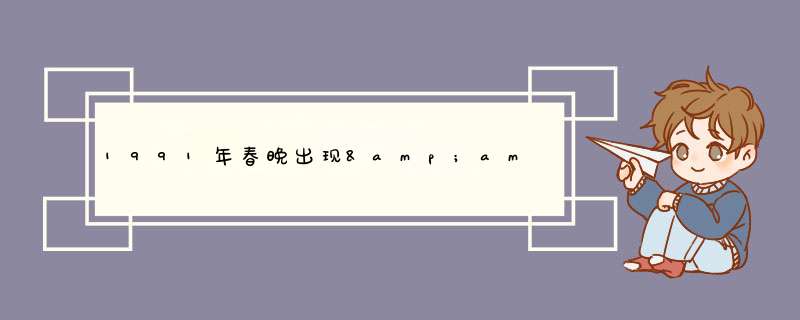
时光追溯到1989年,那时倪萍还年轻,只有29岁。
因为表现出色,倪萍从山东话剧院调到了央视工作,准备主持一档全新的节目《文艺天地》(后综艺大观)。
倪萍第一次走进中央电视台,经历并不愉快。
因为没有进门条,在电视台东门口硬生生等了两个多小时。
从进入央视的那一天起,压力就一直伴随着她。
倪萍初次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房间里有11位同事。
当主任向大家介绍倪萍的时候,这11个人只有两个人回头看了她一眼。
一个人指了下屋角的桌子,说你坐在这里吧。
她当时心里非常压抑,怯怯的坐在自己的位置,静静的翻看着报纸,怕影响其他同事,不敢弄出一丝声响。
倪萍离开熟悉的青岛、熟悉的家,初到北京,在新的环境遇到新的同事。
她开始有点怀念在山东工作的日子,在央视会怎么样,未来会怎样,她心里忐忑不安。
只知道有眼泪悄然滑落腮边,滴到报纸上,湿了一片。
当时倪萍的形象确实不敢让人恭维。
因为倪萍在外站了两个小时显得十分狼狈,头绳的皮筋又断了,她就匆忙系了个疙瘩,头发也显得凌乱不堪。
同事们回过头一瞬间以为是一个农村大嫂走错了房间。
此时的倪萍心中充满了自卑,眼泪“哗”地掉了下来了。
确实比起当时同时进入央视的漂亮大气的杨澜来说,土里土气的倪萍就像一场灾难。
难怪大家都如此不屑和不信任。
这个时候倔强的倪萍悄悄擦去眼泪,决心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
在那一刻她就暗暗发誓,自己一定要努力,做一名好的主持人。
到了下午录制节目,倪萍画上精致妆容,换上靓丽的衣服,开始了在央视的第一次试播。
当她从容大方的出现在演播大厅时,倪萍自信的侃侃而谈。
让台里的编导和其他人都震惊了:倪萍一点不像一个新人啊,主持功底如此的厉害而且亲和力,大家真是以貌取人了。
在最近一次倪萍参加某访谈节目中,谈到了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
1991年,倪萍第一次参加春晚的直播。
晚会中有很多国际友邻,海外华人发来恭喜贺电,工作人员把贺电交到主持人手里时,根本连看一下的机会都没有就要上场。
接近零点时,导演临时递给倪萍四封信件:这是四封电报,抓紧宣读。
倪萍走上舞台,正准备给大家宣布几封贺电,打开四封信件:竟然是四张空白纸!
倪萍当时“嗡”的一下,脑子里一片空白,身上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浑身直打冷战。
那个年代,没有多少电视台,更没有网络平台,每到春晚大家都齐刷刷的围着这一个频道看,总不能这个时候出丑吧。
这四张白纸真的是对倪萍职业的一大挑战,她佯装镇定。
对着空白纸,急中生智现场造句:“此时此刻,我们在红其拉甫守卫着祖国的边疆,希望祖国人民幸福安康。”
“我们是驻守在南沙群岛的海军官兵,虽然我们远在天边,但联欢晚会把我们紧紧连接在一起了。”
“一线工作人员向全国人民问好,孩子们向爷爷奶奶问好”等等。
四张白纸内容全部是她自己凭空编造出来的。
整段“电报”词句优美,头头是道。
因为毕竟是临场发挥,在读到“哨卡”时候,倪萍读成了shao ka。
北大的一个教授就这个问题给她写信:“你必须要向全国人民道歉,你这是误导孩子,你作为主持人怎么能把哨卡(shao qia)读错呢?”
在之后的节目中,倪萍诚恳的在电视上道歉了。
一下台,黄慧群台长一下子就激动的冲上来抱住了倪萍。
多亏了倪萍的临危不乱,那一届的春晚才没能出现纰漏。
从此央视也开始重用倪萍,这一用,倪萍整整主持了13年的春晚。
而在这次访谈结束后,网上随即出现很多不同的见解,曾是人大代表的博士生导师王全杰也在微博中批判倪萍“造假”。
另一位知名大V也点评道:
其实平心而论,倪萍做法是妥当的,毕竟在那样一台非常重要的晚会上,倪萍完美的随机应变,避免了一场直播事故。
我们没有必要纠结倪萍当初是否说了谎话,更应该看到她身上的闪光点。
如果倪萍的这次瞒天过海的“欺骗”,带给了我们一场完美的除夕夜春晚。
那么这种“谎言”又何妨?
妇女队长晓兰
前年,78岁的省级“劳模”晓兰患上癌症,在县城和镇上的医院里,滴滴拉拉治疗了一年多,去年秋天去世了。
咽气时,陪她生命最后一程的隔壁吴爹俯下身子,嘴贴在她耳朵边,大声告诉她,她儿子和孙子的农村“低保”终于办下来了,两个人的生活最终有了着落,等她自己的后事办完,村委会就可以把他们父子俩送到镇上的养老院去,由公家养起来,让她放心上路。
如游丝般的一口气,在嗓子眼里落下去,晓兰终于满意地闭上了眼睛。
晓兰是1961年嫁到给公婆家这个村子的。
当年,在泰州帮厨的公公带着她来到这个家时,她才十九岁,扎着两根羊角辫,虽然身子骨单薄,脸上因营养不良一脸菜色,但是她圆润的脸庞,俊俏的眉眼,薄薄的嘴唇,嘴角两个浅浅的酒窝,在一帮土生土长的农村大嫂姑娘中间,一看就能让人眼睛一亮。
来时,她背着一个蓝布包袱,跟在她公爹老君头后面,躲躲闪闪的,一脸的羞涩与无措。进入村口,一路上,她的公爹逢人便告诉,这是他从泰州城郊领来的儿媳妇,名字叫晓兰,以后就在本村,跟大伙儿一起出工下地,还请一众乡邻帮衬照应。
一路上,他要晓兰与众人打招呼。
晓兰脚踏生地,眼望生人,虽然略显张惶,但是一经她公爹介绍,在生人面前便大方了许多,她遇到人颔首点头,根据不同乡邻的性别年龄,分别以“爹爹奶奶”、“叔叔伯伯”、“娘娘婶婶”“大哥大嫂”相称,应付得简洁而又得体。她那嗓音,清脆圆润,更是惹得村里一帮姑娘媳妇羡煞。
公媳俩个从村口一路走到家中,家中早就准备了一桌饭菜,算是过门的酒席。那年月,大家饭都吃不饱,那有什么钱粮办迎亲的酒席?她公爹预先托人带信回家,算好了时辰日脚,请了自己堂弟夫妻,买了一斤猪肉,一斤半斤豆腐,温水发了二斤豆芽,再在田边上割了两把韭菜,就把一桌饭办成了,难得一次吃上肉,“肥水不落他人田”,老君头请自家堂弟两口子过来,做个见证。
村里见过晓兰的人,私下里都叽叽喳喳地议论。这么好的一个娃儿,他们家领回去做儿媳妇,这姑娘可惜了。也有人说道,有个人嫁过来,这一家子就有了希望,不然,他们家那儿子,到哪里去找到老婆,这一门香火也就从此断头了。
老君头的儿子,诨名“癞宝小”,在本村讨不到老婆,因为他有一种村里人弄不明白的怪病,一到农历闰年柳树飘絮的时候就发作,大半年后才不医自愈。一旦发作起来,“癞宝小”就不下地干活儿,整天在村前村后转悠,口中念念有词,见谁都不理睬,神神叨叨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到吃饭的时候,他会自己跑回家吃饭,吃了饭再出去闲逛,家里谁也劝不回。这病从他十七八岁开始发作,老君头也曾带他到外地求过医,终究没有好转起来,渐渐也就失去了信心,不再外出寻医问药。老君头见医院治不好儿子的病,也曾找过一些巫医神汉做过“法”,想请他们帮着驱除“邪魔”,多次尝试过后,仍然不见好转,也就听之任之了。
所好的是,“癞宝小”这病,不是闰年并不发作。不发作的年头,他下地干活儿与健康人一样,肯卖力气,只要没人提起他的病,他也从不与人生气。还有,即使是发病期间,他也不偷拿或损坏人家的东西,不打人骂人,只要旁人不捉弄他,他也一直与别人相安无事。
时间长了,他一家只把希望寄托在给他娶房媳妇上面,希望他娶了媳妇,能“冲”掉这个令全家人头疼的“魔障”。
领回媳妇前的这些年,老君头一直是在泰州做帮厨的。几年当中,在城里租不起房子,就通过熟人介绍,一直寄住在城郊的晓兰家里。离家一百多里路程,一年四季,老君头平常难得回一趟老家,就寄住在晓兰家,不付房屋租金,隔三差五的,他从饭店里带些残饭剩菜,晓兰爸妈孩子多,粮食不够吃,一家大小沾他这点光,度过了几年春荒,晓兰一家十分感激。
老君头住在晓兰家,对晓兰父母说,自己在泰州城里谋生,把老婆孩子留在家里,终究不是长远之计。现在到处粮食紧张,饭店的生意越来越清淡,都快关张了,他想回老家,一家人团在一起,重操种地营生。自己家里就一个儿子,有三间房,居住宽敞,没有吃闲饭的孩子负担,再找个媳妇回去,一家四口,全是壮劳力,不愁口粮不得到家,年终队里还会有些分红,总比一家人常年分居两头强些。儿子二十好几了,媳妇还没找好,耽着心思。
他向晓兰父母讲明,想带晓兰回家嫁给自己的儿子。
晓兰父母子女多,劳动力少,这几年受过老君头的一些恩惠,看到老君头人很精明,有门手艺,做人还厚道,家里又只有一个儿子,还有三间房子住,在农村算也是一个家道不错的人家,就同意了。
晓兰看到老君头这人还像是个靠得住的人,料得他的儿子也差不到哪里,也就顺从了父母的安排,跟着老君头来到了婆家。
一家人吃了顿迎新饭,晓兰就在老君头家安顿下来了。房间是现成的,床铺被褥收拾收拾就有了。这一年农历不是闰年,晓兰新婚丈夫没有发病,一切都很正常,晓兰觉得丈夫比较老实,有点儿“憨”,平日里话不多,干活儿倒是很卖力气,人长得也还说得过去,也就听从命运的安排,来到婆家没歇上几天,就到生产队出工过日子。
老君头带媳妇回家后,暗下里与左邻右舍都打了招呼,央求旁人在晓兰生孩子之前,别把他儿子有病的事告诉晓兰。乡里人厚道,大家也都同情“癞宝小”生病的不幸,都希望他能够在结婚后把这病根“冲”掉,也就没有人与晓兰说三道四。
老君头一家对晓兰关怀备至,一家四个壮劳力,没有负担,加之原来老君头在城里做过工,多少还攒下了几个零钱,他家隔三差五就到街上买点荤素,回来做给媳妇吃,晓兰也体会到全家对自己的关心爱护。生活安定,饭食改善,晓兰脸上渐渐漾起了红晕。
第二年农历还不是闰年,“癞宝小”仍然没有发病,初春时节,晓兰怀孕出怀了。入秋,晓兰生了个儿子。有了儿子,晓兰生活的根就实实在在地扎下来了,满月后不久,晓兰自己就正常出工了。晓兰适应了村里的环境,人头也熟了,劳动积极,正值年轻,人长得俊,又能说会道,还有个小学三年级的文化底子,春节一过,村里就有人提议,让她当上了妇女队长,带着一个年轻妇女组成的劳动班子,专门在村里干那些需要年轻人突击的农活。
1963年,农历闰4月,又是柳絮飞花的时候,“癞宝小”发病了,照例是不再下地干活,神神叨叨地四处游走。
晓兰吓坏了,怎么规劝他都无济于事,“癞宝小”一下子又进入了自己的“魔障”世界,一副针刺不进、水泼不进的模样,面对老婆也视同路人。晓兰忙与公爹商量,要送丈夫去医院查看。谁知她公爹一脸城府,满腹心事。他在心里盘算,原来想儿子娶上媳妇会“冲”掉他的病症,看来这个想法落空了。他在盘算着怎样才能稳住媳妇,把她和孙子留下来。
她公爹劝她:“孩子,我早先在你家住了好几年,你看我老头子为人怎样?”
晓兰不知道他为啥要扯出过去的事,便随口答应:“你住我们家几年,对我们帮衬不少。”
“你说你嫁到我们家也快两年了,我家这儿子干活儿算不算一把好手?”
晓兰摸不着头脑:“这我知道。就是不知道他得了这病,什么时候才会好起来?”
老君头不接她的话题,继续说:“你来我们家,我和你婆婆待你怎样?”
“这没得话说。你们待我如亲闺女一样,这两年日子过得也比我们家好得多。”
有了这样的垫铺,老君头终于告诉晓兰实话:“孩子,事到如今,我们也不瞒着你了。我这儿子十几岁时得的这个怪病,每到闰年三春头上柳絮飘起来的时候就发。我也多方求医问药,总是好不起来。”
晓兰听到这些,不禁流下眼泪,原来老君头是瞒了自己儿子的病情,把她哄骗来的。她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指着公爹的鼻子,大声怒斥:“你当初为什么瞒着我一家,把我骗到你们家来!”
老君头也不还嘴,只是一个劲儿地叹气。略略停顿,他接着说:“他这病也怪得很,发病时,不偷不抢,不惹事生非,吃饭睡觉一如往常。等到秋粮下来时候,自己也就好了。”
晓兰将信将疑。饭也不吃,孩子也不奶,工也不出,一个劲儿地哭天抹地。
老君头没办法,值得央求了邻居的大嫂陪着晓兰。一连几天,晓兰看到发病的丈夫晚上一如既往的回家,回家就闷头吃饭,饭后也不再出门,上床到头便睡,果真与老君头说的情况差不多。
几天过去,老君头看看晓兰的情绪平复了一些,便以央求的口气对晓兰说:“闺女,你看,你到我们家,等于是救了我们一家子。事到如今,孩子也生了,生米熟饭,你就将就着点,在我们家把儿子带大吧。”
老君头继续开导她:“现在这年头,缺吃少穿的,你到哪里,还不是干农活过日子。今后我们这个家,就交给你当,家里大事小事,全听你的,一切由你说了算。”
晓兰看看襁褓中未满一岁的儿子,再看看对她亲如父母的两个老人,陷入了久久的沉默。
左邻右舍看到“癞宝小”又一次发病,也纷纷前来劝慰。大妈大嫂陪着晓兰一起抹泪,最终总是归结到劝说她留下来,并且告诉她,她丈夫的病症一到上秋,就会不治而愈,一如往常,希望晓兰留下来支撑这个家。
生产队和大队的干部得知情况,也赶来晓兰家做她的工作。让她安心留在村里,继续当好妇女队长,并且鼓励她好好守着这个家,将来大队还要进一步培养她,都说她是个很有潜力的女干部。
晓兰想回泰州娘家一趟,公公和婆婆都没有同意,说是一个人带着吃奶的孩子出远门,太不方便,心底下也怕她带着孩子从此一去不返。她没有办法,便托队里的保管员再帮她给父母写了一封长信,诉说她目前遇到的情况。
结婚后,晓兰总共托人给远在泰州的父母写过两次信。第一次是刚刚跟随公爹来到这里后写的,信中介绍了到婆家的情况,表达了初次离家对一个陌生环境的新奇和对娘家人的思念,总体上是要让父母亲放心。第二次是几个月前生儿子后写的,向父母亲报了喜讯,想请父母亲来看看外孙。第二次去信后父母亲不仅仅回了信,还寄来了给孩子做毛衫褂儿的三尺红洋布,来信解释,泰州到她婆家一百多里,水路旱路舟车劳顿,一天无法到达,路上还要寄宿旅店,盘费太大,无法成行。晓兰沉浸在刚生儿子的喜悦之中,对父母不能前来,也很体谅理解。
这一次,她希望父母无论如何一定要来一趟。面对现在的情况,她实在无法独自面对,需要父母帮她拿拿主意。
她父亲接到来信后,从泰州坐了大半天轮船,在县城住了一宿旅社,再坐汽车从县城到镇上,然后步行十多里,傍晚来到了村里。
父亲来到村里,她那发了癔病的丈夫还不知云游在什么地方。她公爹领着泰州来的亲家,家前屋后、村前村后到处看了看,非常不安地给亲家赔了不是,让亲家无论如何要劝女儿留下来,带大孙子。
晚上她癔症在身的丈夫回家后,面对从未谋面的岳丈,照样上桌吃饭,从头到尾却是旁若无人,饭后父女俩只有抹泪叹气。
第2天, 晓兰父亲又在村里走了走,向村上的人了解“癞宝小”女婿正常年景的情况,左邻右舍和村干部的说辞,印证了亲家对他儿子病况的说法。
第3天, 他支开亲家和亲家母,独自做他女儿的工作。“老话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如今已经跟他过了两年,儿子也生了,还想怎么样?他这病,我已经打听好几家了,不是闰年并不发病,平常没病的时候,在村上他也是个壮劳力。你现在带着一个孩子,可不比前两年,谁还能要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啊?闺女,你就认命吧,兴许,再过上几年,他这病就会慢慢好起来呢!”
晓兰权衡再三,最后答应了父亲的要求。
到了秋粮上场的时候,“癞宝小”的病果然好起来了,照常下地出工。晚上晓兰问她丈夫病中的情况,丈夫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晓兰掐指算算,每隔上两三年,才有一个闰年,就他这个病症,勉勉强强也能凑合着跟他过上一辈子。
晓兰对妇女队长名分下的工作更加上紧了,接下来的几年,她连续几年受到镇人民公社的表彰。以后几年里,时不时还到镇上开会。最值得一提的是,小孩子三四岁时,还被选做妇女代表,到县里参加了一次全县的妇女代表大会。
1967年,她作为大队里的代表,出席了全镇“活学活用”讲用会,大队里安排人员替她准备了讲话稿,让她念熟,着重介绍她几年来关心生病丈夫,孝敬公婆,带着全家积极参加劳动,同时在农村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的事迹。政府安排她到各村巡回“讲用”,对她为人称道的道德情操和爱集体爱家庭的行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转眼晓兰三十多岁了,生活按照它本来的逻辑和节奏向前发展。只是“癞宝小”的癔病还是一如往常,并没有因为晓兰的悉心照顾而好转起来。幸好,晓兰出身贫寒,知人甘苦,忍辱负重,心态平和,一家人太太平平,日子过得还算顺畅。
自从参加过全县妇女代表大会和在全镇巡回“讲用”以后,晓兰在全镇的名气渐渐大了起来,村党支部培养晓兰入了党,县妇联派人到村里总结了典型材料,登载在地区一级的报纸上,全县各地都知道晓兰这样一个既能在农业生产一线敢打敢冲,又能践行社会公德、照顾生病老公的典型。
时光进入到七十年代中期,晓兰儿子渐渐长高,在村里读完小学后,又进入邻村的初中读书了。读到初二,这孩子开始窜高个头,嗓子也渐渐沙哑起来。晓兰明白,这孩子开始进入发育年龄了。
这一天是个星期天,儿子没有去上学,晓兰在门外的场地上翻晒粮食,无意间发现儿子一个人坐在一旁窃窃私语。晓兰心头一震,这不与他爸爸发病时一个样子?只见她儿子双眼发直,嘴里念念有词,旁若无人。晓兰连忙放下手中的活儿,一把抱住儿子,着急慌忙地问儿子怎么啦,可是,儿子好像不认识她似的,只是不由自主地自言自语。
晓兰这下子心慌了。儿子是她这些年来生活的依托和希望,遇到“癞宝小”丈夫发病的年头,她不在多去顾及她,一心全部寄托在孩子身上,对这个长像和自己差不多的孩子关心备至。今天,看到这种情形,她一屁股坐在地上,止不住嚎啕大哭:“我怎么这么苦命啊!”
晓兰不死心,抱着趁早求医寻药的想法,向队里干部告假,和她公爹当年一样,踏上了儿子的求医之路。镇上医院的水平是不指望了,第一步就跑到县医院,几次下来不见效果后,她又东拼西凑,借钱跑省城医院。
半年跑下来,儿子的病情并不见好转,晓兰的心渐渐死了。
儿子也与他老子一样,到了秋粮上场时,这孩子的病也好起来了。儿子休学一年后,又继续到校读书,勉强读到初中毕业,这书再也无法读下去了。
自从儿子发病后,晓兰的脸上失去了往日的阳光和活力,在地头和大伙儿一起干活儿时,往往沉默寡言,一个人想着自己的心思。
正当晓兰情绪低落的时候,组织上及时做她的工作,给予关心,也对她做出提醒。大队支部书记专门找到她家,鼓励她振作精神,维护新时代农村妇女典型的形象,克服家庭困难,继续带领妇女突击队,发挥好妇女“半边天”的作用。书记承诺,如果确因家庭生活困难,无法提拔到大队工作,将来有机会一定让她评“劳模”,让她享受到相应的政治经济待遇。
面对家庭这样的状况,晓兰对提拔干部和评不评“劳模”,倒也不大在意。她只是想,公婆年事日高,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摊上这样的丈夫和儿子,这样一个家庭,如果自己再不振作起来,领着丈夫和儿子往前过日子,这个家将无法支撑下去。
晓兰继续担任妇女突击队长,只是每逢儿子和丈夫发病的年头,她的付出比常人更加艰辛。
就这样,晓兰熬过了十几年的时光,公公婆婆先后生病卧床,晓兰精心料理,服侍尽孝,直到入土为安。
这些年,各级政府对晓兰的付出,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她于1975年评上了县级劳模,1979年又被评上了省级劳模。
岁月的风刀霜剑,在晓兰的额头上刻下了一道道皱纹,她的满头秀发,先是两鬓染上了霜花,继而满头变得灰白,五十岁多一点,已经满头白发了。
进入八十年代,农村已经天翻地覆,早年的妇女突击队早已解体,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体制改革后,农村各家各户包干种地,农业生产结构深刻调整,市场农业蓬勃兴起,晓兰所在村已经成了南方大城市的蔬菜基地。
晓兰一家,在不是农历闰年的正常年景,也和村里其他人家一样,种植蔬菜,晓兰领着丈夫和儿子,合理安排结构,不误农时,抢种抢收,收入与左邻右舍相差无几。到了有闰月年份,晓兰则早早做出安排,只种上费工少的粮食作物。当然,逢上这样的年景,收入自然也就比旁人要少上许多。还有,现在人家的孩子,都能到城里去打工,收入远远高于种田,晓兰就不做这种指望了,她不放心儿子外出。
时光荏苒,转眼儿子三十多岁了,还没有成亲,他的癔病也发作得比老子要频繁多了。现在老头子的病还是每年到闰月就发,可是儿子经常不是闰年也发病。儿子不能成家,成了晓兰无法治愈的心病,成了她每天入夜后无法排解的伤痛,她害怕有朝一日,自己年老力衰后,儿子发病没人照料。这件事,与她那八棒打不出一个闷屁的丈夫无法商量。她一直在心里盘算,怎样才能为儿子讨到一房媳妇,让儿子将来也人照顾。可是,她又不忍心让一个好人家的女孩子,像她自己一样生活,不忍心害了人家姑娘。在这种矛盾中,她常常夜不成眠,辗转反侧。
寒来暑往,又是几年过去了。
1天, 邻村来了一个与晓兰熟悉的老婆婆,说是他们那里有大龄男人从贵州讨到了老婆,给人家娘家人一点养老的钱,花费的也不是很多,远远不如娶本地农村姑娘花费的彩礼钱多,打听晓兰是不是也替她儿子考虑考虑。
晓兰动心了。
几个月后,经邻村那贵州媳妇介绍,婆婆果真领来了一个贵州女人,看上去三十来岁年纪,那女子诉说自己的身世,前年她丈夫在山上采石不幸摔死了,跟着别人来到江苏,看看这里的日子远远比她家乡好过,愿意过来看看老婆婆介绍的这户人家。
晓兰看看这个女人,身材瘦小,面庞黝黑,一副老实相。从外貌上看,这个女人与她儿子实在是不太般配。不过,她心知肚明,就他儿子这样子,也就只能将高将低罢了。晓兰表现出巨大的热情,招待吃饭,又送礼物,还答应,如果这女人留下来,她会把这些年来家里的积蓄寄给女人娘家赡养父母。
那女人留下来了。
一年多以后,黑瘦女人为她家生了孙子。晓兰对这个媳妇也就更加放心,又给对方的父母汇去一笔款子,为的是进一步稳住这个女人的心。
晓兰想领着这个女人下地干活,可是这个贵州女人说她家原来住在山里,做不惯这里的农活,整天抱着个小孩,走东家窜西家,就是脚板不往地里踩。晓兰拿她没法,只是感叹,如今的年轻人与过去不同了,吃不得苦,远远比不上自己当年。
就在她孙子快要过周的时候,有一天,她和丈夫、儿子下地回来,突然发现她的儿媳妇不知去向,把小孩一个人留在家里无人照料。
这下晓兰慌神了。
连忙赶到邻村去找媳妇的那个同乡,那个先来一步的贵州媳妇。到哪里才发现,那个贵州来的媳妇也不见了,那一家人正在着急、四处寻找呢!回来央求几个邻居到附近乡镇、县城的车站去找,可是,哪里还找得到媳妇的影子!
从此,晓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一家三代人的生活,里里外外,全是她一个人承担。
作为省级劳模,晓兰过了六十岁的时候,镇上每月发给她一些生活补助,她自己侍弄的几亩地收入还不错,日子一天天往前过。过了几年,她的“癞宝小”丈夫也生病离他而去。
她总是担心,有一天自己百年以后,她儿子和孙子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下去。
她多次找到村里和镇上的干部,把这些年为儿子看病的材料向上级呈送,邻居吴爹也动用了不少社会关系,到处找人,村里干部积极为她说话,镇县两级先后派人前来调查核实,在方方面面的关心下,儿子和孙子的农村“低保”终于得到了批准。
晓兰九泉之下终于可以瞑目了。
2020331
盛_
东北著名二人转演员,出生于1973年5月14日,吉林长春人,现就职于吉林省吉剧院。2002年,吉林省首届二人转艺术节被评为“四大名旦”。
2009年,参演乡村环保剧《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同年,参演农村喜剧片《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2》。2011年参演现代喜剧片《能人冯天贵》。2014年参演物传记《马向阳下乡记》。
2017年,参演喜剧**《村嫂》。
中文名:盛_
外文名:ShengZhe
国籍:中国
民族:汉
出生地:吉林长春
出生日期:1973年5月14日
职业:二人转演员、主持人
主要成就:2002年吉林省首届二人转艺术节被评为“四大名旦”
代表作品:《逗你乐翻天》
性别:女
星座:金牛座
单位:吉林省吉剧院
居住地:吉林长春
演艺经历
2009年,参演由潘长江执导,孙宁,姜超,潘阳主演的乡村环保剧《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在剧中饰演大玲子;同年,参演由潘长江执导的农村喜剧片《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2》,在剧中饰演大玲子。
2011年参演由潘长江执导,潘阳,宋佳宁,梁爱琪主演的现代喜剧片《能人冯天贵》,在剧中饰演毛丽。
2014年参演由张永新执导,吴秀波,王雅捷,李洪涛主演的人物传记《马向阳下乡记》,在剧中饰演刘玉娇。
主要作品
参演电视剧
马向阳下乡记-2014-9-17,饰演刘玉娇
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2009,饰演大玲子
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2-None,饰演大玲子
能人冯天贵-None,饰演毛丽
二人转剧目
获奖经历
2002年吉林省首届二人转艺术节被评为“四大名旦”。
表白女生只是一种表明方式,最重要的是你表白之前的沟通和相处。
在你选择表白之前,需要和女生建立一个良好的沟通关系,通过沟通一些共同的话题,达到彼此思想上的契合和精神的共鸣。
表白女生并不是简单地说一句“我爱你”或者“我喜欢你”就结束了。面对心仪的女生表白,需要精心的准备。不能打无准备的仗。
表白前的准备需要确定:时间,方式,场景。关于表白的时间,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见解。像周日,情人节,生日,这都是比较适合表白的日子。或者可以选择一个彼此都觉得比较轻松愉快的时间。
大衣哥儿子朱小伟,跟陈萌定亲的消息,早就在网络上传开,人人都知道“地主家的傻儿子”,又要娶媳妇了。大衣哥的新儿媳出身农村,本科学历,在当地小学当老师。
老师和护士,都是正当且稳定的职业,备受大众尊重。朱小伟跟陈亚男离婚后,大家都以为他娶不到更好的女孩,谁知人家还不到5个月,就立马找到了新女友,气人不气人?
为了尽快将婚事定下,大衣哥前几天已经跟大衣嫂上门,跟女方父母见面了。出于对陈萌的尊重,大衣哥提出给他们家50万彩礼,还附赠县里一套房,毕竟小伟已经是二婚了。
订婚当天,朱小伟就带着陈萌去手机店买手机,还揽着未婚妻的肩膀,别提多亲密了。不知道陈亚男和她的父母,心里是什么感受,他们曾经享受过的风光,现在已经属于别人。
不过陈萌跟陈亚男不同,她不会为了赚钱,放弃自己的职业,也不会直播带货。大衣哥特别看好这个新儿媳,媒体采访的时候一直夸女孩性格好,是个老实本分的人,格外讨人喜欢。
而陈萌也不拘束,在社交账号上晒出了订婚的婚书,一看就是特别重视这场亲事。其实感情本就该这样,不管双是否有所图谋,只要决定在一起,就说明她已经认可了那个人。
陈萌通过文案表白朱小伟,一句:始于初见,止于终老,以爱之名,余生为期,让网友们为之赞叹。看得出来,女孩是个有文化的人,连表白都这么官方,不由让人期待他们的婚礼。
朱小伟是个特别憨厚的人,用一个“傻”字来形容,应该再合适不过。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在父亲的影响下成为香饽饽,难免会遭到别人的嫉妒,大衣哥已经习惯被人当成话题了。
刚得知陈萌要嫁给朱小伟时,不少网友都曾调侃,说女孩是为了钱卖了自己。而大衣哥的搭档袁庆,则在直播中表示,她认识陈萌那个孩子,说她根本不图钱,就是相中了小伟这个人。
话说得很好听,可事实究竟如何,还得等两人居家过日子,一起生活过才知道。陈亚男嫁给朱小伟时,不也曾说过不图钱吗,后来不还是为了钱,一直在网上折腾,惹人厌烦?
农村女孩找媳妇,都有一个不变的要求,男生至少得勤劳能干,能为这个家撑起一片天。而朱小伟除了父亲有钱,似乎一条都不符合,说女孩不是为了钱,大家肯定也不相信。
可不管陈萌图什么,她对朱小伟的现状,肯定都非常清楚了。有陈亚男作为前车之鉴,她也明白嫁过去之后,应该如何当一个好儿媳?陈萌也答应大衣哥,结婚后跟小伟立马要孩子。
其实年轻女孩,都不愿意太早生孩子,最好的年华只有那几年,怎么能放任自己变成妇女呢?嫁到朱家这样的人家,陈萌早就做好了打算,她表示自己现在没怀孕,也不会奉子成婚,但他们肯定会尽快要孩子,让二老放心。
如今朱小伟也到了结婚的年龄,过段时间两人就可以领证了,希望他们结婚以后,能好好过日子,不要再出幺蛾子了。
抖音里大春和二明子是同事关系。抖音里大春、二明子演的是情景剧,不是真的情侣,也不是真的名字。抖音咱们村里的的大春、二明子、三哥三嫂都是剧情需要的人物形象,不要演员本身份,是同事关系。
这是一个读者在评论区留言的故事。
我深有感触。因为去年我去农村走访的时候,也遇到了这样不讲理的嫂子。
我走访的那个农村,没有什么自己的工厂产业,男人大部分都是在外地打工。女人和公婆就带着孩子,在家过日子。我问过那些女人,为什么不跟着丈夫一起出去打工。
她们说:“一家子都去,男人挣的钱,还不够花的。老婆孩子都在家,花销就小,男人在外边挣一年钱,就还能存下点钱。”
那个村里只有一条街是买衣服吃食的。但是因为地方穷,人们都不富裕,小买卖也不怎么好做。
有一个女人男人出去打工了,她跟自己的哥哥在老家合伙做生意。前几年,赚了不少,但是这些钱都在她嫂子手里攥着。她要了好几次,她嫂子也不肯松手。后期的时候,赔了很多钱,她嫂子就说了这样的话:“赚了是我们的,赔了就是你的。你哥哥要是敢帮你还债,我就跟他离婚。”
我深觉这样的女人,真的是完全不讲道理。但即使这样,女人的父母都求着女人忍下这口气,他们的说辞是:“现在农村娶个媳妇太难了,怎么也不能让你哥哥离了婚。你哥哥要是离了婚,他家的两个孩子怎么办。”
我听人们说这件事的时候,很气愤。
我说:“万一这个女人的丈夫也要离婚怎么办。他辛辛苦苦在外边挣钱,结果都成了这样。”
那些老人跟我说:“男人不会离婚的。离婚了,他的孩子怎么办。再说了,现在农村二婚的女人也好嫁。”
有些人因为思想的贫瘠,连是非对错都不分了。这样贪婪自私的人,又能教出多好的孩子。谁不讲道理,谁占便宜,这是一种多无知的思想。
我总以为这样的人,少之又少。但是,今天我在自己的后台,又看到了一个这样不讲道理的嫂子。
“我同学结婚的时候,婆家给了18万的彩礼。我们那边都是这个数。然后,我这个同学的嫂子,就把那18万块钱扣下了,她说她要买车。
周围的人都问她,凭什么拿着小姑子的彩礼钱买车。她说,我要买车,她有钱,我就该用。这是天经地义的。
我这个同学的哥哥和父母都不同意,她嫂子就闹着要离婚。我这个同学的哥哥刚开始也没同意离婚。他跟自己的妻子说,你结婚的时候,我也给了你18万的彩礼,都在你手里呢。你要是想买车,就用你自己的彩礼买,为什么一定要扣下我妹妹的彩礼钱。
结果女人说,你妹妹的钱,就是你家的钱。我买车,就该你们家出这笔钱。
男人为这个跟自己的妻子吵了很多次。最后,男人的父母,男人都同意了跟女人离婚。但是前提是,女人必须把18万的彩礼退回来。”
“女人不想离婚了,但也不想退彩礼,也不想把扣下的彩礼钱还给小姑子。她就是不讲理了。她觉得反正钱在我手里,你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最后男人家里还是打了官司,才跟这个女人离了婚。这个女人的彩礼钱,没要回来多少。因为那些钱,女人早就偷偷补贴自己的娘家了。小姑子的彩礼钱,都要回来了。”
我不知道这个女人离婚后,过得好不好。
但是我想说,当这种不讲理的女人,真的好吗?你觉得你自己精明,但别人都是傻子吗?
这样的女人大多都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我想说说“坏”名声,对一个女人的影响有多大。你做的那些不讲理的事,你觉得没事,但是都会形成口碑。而口碑这种东西,一旦形成,对一个女人的影响就是致命的。
不要说,现在已经不是封建社会了,女人的名声已经不重要了。相信我,不管到了什么时候,女人的名声,都很重要。尤其是这种“坏”名声。
它真的会跟你一辈子,甚至是累及你的子女。
我原来讲过的一个我们村里的女人,给男人家要了很多彩礼。还要在男人全款的房子上加上自己的名字。
她觉得她这样做一点都不过分,她觉得她跟男人分开了就能真的找到一个冤大头。
但结果是,自从她家有了这种不讲理的名声后,但凡条件好点的人家,根本不会跟这样的人家结亲。因为,谁知道,他们又会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呢。
而那些来提亲的,大多都是那种不好的,觉得女人名声不好了,嫁不出去了,想要女人便宜嫁了的。
结果,女人耽误了好几年,一直没说到合适的亲事。年纪越大,越不好说亲,她家里人还想多要彩礼,出这口气,于是一直耽搁着。
现在这个女人依旧等着天上掉下个冤大头。
可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冤大头吗?我写情感这么多年,深以为男人在面对婚姻时,要比女人更现实。
没有人是傻子。当一个人把别人当傻子的时候,你就是最大的傻子。
剖析一下这种农村少奶奶们的心理。
我在农村走访的时候,遇到了不少这种拿离婚吓唬婆家的儿媳妇。她们不讲理,她们坚持一个原则:“你家对我不好,我还可以找别家。”
我不得不承认,很多二婚女再婚后也很幸福。但是绝对不包括这一种不讲理的女人。
因为她嫁给别人后,依旧不会知足。
有些农村女人,离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婚。真的都是婆家不好吗?有时候,真的不是婆家不好,而是她自己就不具备幸福的能力。
她结了婚不是为了好好过日子的,她就想天上掉馅饼,占别人便宜的。可但凡这种人自身条件都不好。
因为自己没能力,才想要占别人的便宜。
有人说,不善良的人,晚景都不太好。
我深以为是。她这辈子是只待了自己,未曾善待别人,别人又怎么会善待她呢?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表白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