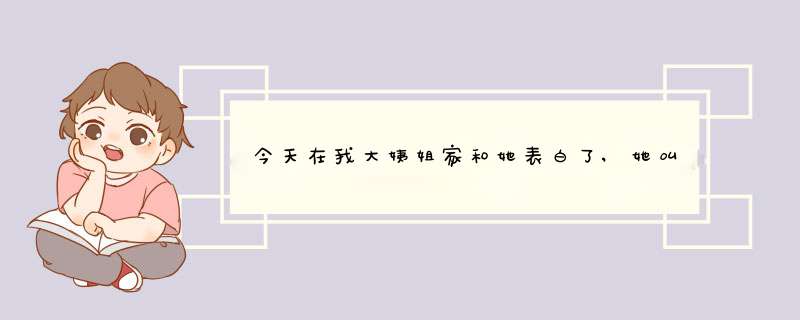
先森,一个妹纸是不会轻易叫人妹夫的,叫你“一生”妹夫,?还是“一声”妹夫?
如果是叫你一声“妹夫”我大爷呀,你表白的对象是他妹,还是喊你妹夫的那个人啊,说实话,我回答答着答着都有点乱了。
直接就告诉你我回答的答案:只要让你走的不是“他妹”,那你就有戏!因为赶你走的人叫你“妹夫”了,如果让你走的人是她“大姨姐”,这难道还要说点啥吗?小子,下次见大姨姐时该改改口了,叫“姐”或者“姨”。
不过,苏东坡倒有一个堂妹,是他的初恋情人,而且毕生对伊人念念不忘。东坡的祖父去世之后,他父亲远游归来,他的叔叔和家属也回来奔丧。这时堂兄堂妹颇有机会相见,也可以一同玩耍。据苏东坡说,伊人是“慈孝温文”。因为二人同姓,自然联姻无望,倘若是外婆家的表妹,便没有此种困难了。后来,此堂妹嫁与一个名叫柳仲远的青年。以后,苏东坡在旅游途中,曾在靖江她家中住了三个月。在堂妹家盘桓的那些日子,东坡写了两首诗给她。那两首颇不易解,除非当做给堂妹的情诗看才讲得通。当代没有别的作家,也没有研究苏东坡生平的人,曾经提到他们特殊的关系,因为没人肯提。不过,苏东坡晚年流放在外之时,听说堂妹逝世的消息,他写信给儿子说“心如刀割”。在他流放归来途经靖江之时,堂妹的坟就在靖江,他虽然此时身染重病,还是挣扎着到坟上,向堂妹及其丈夫致祭。第二天,有几个朋友去看他,发现他躺在床上,面向里面墙壁,正在抽搐着哭泣。
——《苏东坡传》第三章《童年与青年》
以上这段文字,出自林语堂的手笔。他的著作是用英文写的,中文译为《苏东坡传》。其实他的英文名称《The Gay Genius》,英美人既可读作《快乐天才》,也可视如《同性恋才子》。二十世纪前半叶,同性恋在美国还是个敏感问题,仅凭这个书名,我们就不得不佩服林语堂的商业眼光。这本传记在英美流传很广,林语堂以娓娓动人的笔触,将苏东坡的生平事迹以及为品格、思想向西方世界介绍,传播之功自不可没,但书中许多史料和观点都是错误的,上所列举的便是一例。
林语堂说苏轼一生都在暗恋自己的堂妹,主要理由就是:“苏东坡晚年流放在外之时,听说堂妹逝世的消息,他写信给儿子说‘心如刀割。’”这段话,确实出自苏轼所写的一封信:
近得柳仲远书,报妹子小二娘四月十九日有事(丧事)于定州,柳见(现)作定签(定州签判)也。远地闻此,情怀割裂,闲报之尔。
——《与程之才》第六十五简
林语堂从一开始就搞错了,堂妹之死的消息,东坡是给程之才说的,根本不是“写信给儿子”。程之才是东坡的表哥,即母亲程夫人的亲侄子,也是苏轼姐姐八娘的丈夫。八娘因为忍受不了姑婆(程之才父母)的虐待,于皇佑四年(1052)死去,为此苏洵曾作《自尤》诗,痛及程家父子,苏程两家从此断了往来。直至四十二年后,东坡被贬岭南,程之才时为广东提刑,二人才修好如初。所谓“心如刀割”,乃译者之误,原文是“情怀割裂”。东坡在后来撰写的《祭亡妹德化县君文》(德化县君为其亡妹封号,因其夫君柳仲远官位与县令相若而封)文中说:
宫傅之孙,十有六人。契阔死生,四人仅存。
“宫傅”是东坡祖父苏序封号的简称,元佑六年苏辙被任命为尚书右丞(即副宰相)时,苏序被追封为太子太傅,因此尊称“宫傅”。苏轼闻知堂妹去逝的消息,再想到自己堂兄堂妹一十六人,十二人已经过世,只剩下自己与弟弟苏辙等四个,“情怀割裂”,实属自然。
东坡给程之才的信,写于绍圣二年(1095)七八月间,也就是他堂妹去世后三四个月后。他之所以要与程之才说这件事,就是程之才对这位同乡表妹也应认识。为了弄明白苏轼堂兄妹的情况,免得行文翻来覆去仍然陈述不清,这里有必要根据苏洵《苏氏族谱》及苏轼、苏辙的相关文章,将苏家三代家庭成员列出简表:
公元纪年苏轼祖父苏序情况大伯父苏澹及其子女二伯父苏涣及其子女父亲苏洵及夫人子女苏轼堂兄妹之大体行次
973苏序生
994 22岁 苏澹生
1101 29岁 苏涣生
1109 37岁 苏洵生
1110 程夫人生
1114 42岁 苏澹21岁长子苏位生苏涣14岁苏洵5岁苏位为十六兄妹之首
1024 52岁 31岁,次子苏佾当生于此前苏涣24岁中进士乙科15岁苏位为十六兄妹之次
长子苏不欺当生于此前苏不欺为十六兄妹之三
1027 55岁 34岁 27岁,次子苏不疑生于此间19岁,娶程夫人为妻苏不疑为十六兄妹之四
1028 56岁 35岁 28岁 20岁,长女生,不久夭折此女当为十六兄妹之五
有一女,当生于此间此女当为十六兄妹之六
1030 58岁 37岁 30岁 22岁,次女生,不久夭折此女当为十六兄妹之七
1032 60岁,夫人史氏去世39岁32岁,其长女生当于此前24岁此女当为十六兄妹之八
1034 62岁 41岁 34岁 26岁,长子景先生,夭折苏景先为十六兄妹之九
三子苏不危当生于此前苏不危为十六兄妹之十
27岁,幼女八娘生于该年八娘为十六兄妹之十一
其次女当生于此前此女为十六兄妹之十二
1037 65岁 43岁,病逝37岁29岁,次子苏轼生于是年苏轼为十六兄妹之十三
其三女当生于此际此女为十六兄妹之十四
1039 67岁 39岁31岁,三子苏辙生于是年苏辙为十六兄妹之十五
其幼女德化县君当生于此际此女为十六兄妹之十六
1048 75岁,病逝 48岁 40岁
1062 62岁,病逝 54岁
1066 58岁,病逝
由上表可以看出,苏轼所悲悼的堂妹“德化县君”,乃其堂兄妹中最幼小的一个,她的去世,使颠沛流离的苏轼备感人生无常,因此“情怀割裂”,林语堂居然由此四字,便臆断这位堂妹是苏轼的所谓“初恋情人”,实属莫名其妙。
那么,苏轼在给程之才的信中,为什么要称这位堂妹为“小二娘”?若按苏家兄妹排序,她应叫“十六娘”;按女性排列,应叫“八娘”才是。可苏轼的三姐在女性中排行第五,却称“八娘”,显然苏家女孩的名字,是把苏洵堂兄妹所生的孩子都放到一起排序的。既然与苏轼紧挨着的姐姐称为八娘,这个堂妹上面还有亲姐姐,那她的排序应在“十娘”之外才是。
值得说明的是,苏轼大多数书信,都不是自己编校入集的,南宋之后,人们广为搜罗他的书信,编为《东坡手泽》,此后又被迻入文集 。从苏轼之姐名为“八娘”来看,这个堂妹应为“十二娘”,而“十”与“小”字,在行书中极易被误认。
为了行文方便,我们暂且将苏轼这位堂妹称为“十二娘”。
正因“十二娘”与“小二娘”三字之误,前人未曾辨析,林语堂便将东坡的这位堂妹,和另一“小二娘”混为一谈。东坡在晚年另一封信中,确曾提起一位“小二娘”:
小二娘知持服不易,且得无恙,伯翁一行甚安健。得翁翁二月书及三月内许州相识书,皆言一宅康安。亦得九郎书,书字极长进。今已到太平州,相次须一到润州金山寺,但无由至常州看小二娘。有所干所阙,一一早道来。万万自爱。
——《与胡郎仁修》三首之三
这封信写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四月,信中的“翁翁”指苏辙,“伯翁”乃东坡自称,宋人将祖父、外祖父称为“翁翁 ”,而对晚辈,常在称呼前加上个“小”字,比如“小二娘”。苏轼当时已六十六岁,他苏辙的孙子(女)年纪长者陆续开始婚嫁,由此可见,胡仁修乃苏辙的孙女婿或者外孙女婿。东坡信中所说的“小二娘”,无疑是苏家第三代中排行第二的孙女或者外孙女 。
于是我们可以理解,林语堂为何屡次谈及“途经靖江”、“堂妹的坟就在靖江”了。那是因为“靖江”属于后来常州所辖五县之一,林语堂见到这封信中谈及“小二娘”在“常州”,便将两个“小二娘”混作一谈,以二十世纪纲常无存之际的才子之心,度八百年前家规极严之时的才子之腹。
有人说这里的“靖江”为“镇江”之误,同样经不住推敲。因为镇江在北宋时,名为“润州”,即便州治所在地,也称“京口”,北宋初年确曾设有“镇江节度使”之职,但其节度使驻守之地却在扬州 ,直到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八月丁丑,朝廷才明令将“升润州为镇江府 ”,那时东坡已经去世两年多了。
林语堂说“十二娘”是苏轼的“初恋情人”,除了上述两个“小二娘”之间的附会外,另一个依据就是苏轼曾在润州住过三个月。林语堂说:后来,此堂妹嫁与一个名叫柳仲远的青年。以后,苏东坡在旅游途中,曾在靖江她家中住了三个月。
——《苏东坡传》第十一章《诗人、名妓、高僧》
所谓“苏东坡在旅游途中,曾在靖江她家中住了三个月”,又是一个明显的错误。熙宁七年(1074)正月至四月间,三十九岁的苏轼确实在润州呆过三个多月,不过他不是旅游,而是奉朝廷之命,到苏、常、润、秀四州赈灾放粮,润州是他的放粮地之一。作为朝廷命官,赈灾放粮自有官家驿站可供居住,将此行定为旅游并居住在“十二娘”家里,实属曲意为之。
“十二娘”确实嫁给了柳仲远,名叫柳子文,但苏轼最早认识的并不是他,而是柳子文的父亲柳仅,字子玉。熙宁三年(1070)春天,柳仅便曾到汴京拜访过苏轼和苏辙,三人一同写诗唱和,苏辙在诗中曾有“新年如是识君初”(《京师逢柳子玉郎中见寄》)之句,那一年苏轼三十五岁,苏辙三十二岁。熙宁五年(1070)苏轼去杭州赴任,道经陈州去看苏辙,正好柳子玉贬官寿春,声称船上断饮,去见苏轼兄弟,三人再次唱和一回。此后柳子玉曾约苏辙同到河北共城(今河南辉县)买田归隐,互相为邻,苏辙愉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 。熙宁六年夏秋,柳子玉被命提举舒州灵仙观,即赋予闲职,他在杭州跟随苏轼游玩了半年之久。熙宁十年(1077)柳子玉去世时,苏轼曾撰文祭奠,文中说:
猗欤子玉,南国之秀。甚敏而文,声发自幼。
元轻白俗,郊寒岛瘦。嘹然一吟,众作卑陋。
谪居穷山,遂侣猩狖。夜衾不絮,朝甑绝馏。
慨然怀归,投弃缨绶。潜山之麓,往事神后。
顷在钱塘,惠然我觏。相从半岁,日饮醇酎。
朝游南屏,暮宿灵鹫。雪窗饥坐,清阕间奏。
嗟我后来,匪友惟媾。子有令子,将大子后。
颀然二孙,则谓我舅。歌此奠诗,一樽往侑 。
由此可见,苏轼与柳子玉既是诗友,又为同道,此前多次相会,尤其是杭州“相从半岁,日饮醇酎。朝游南屏,暮宿灵鹫”,结下了极深的友谊,苏轼此番到润州出差,柳子玉专程先回家中恭候,待苏轼到来后,便领他到润州的鹤林、招隐、金山寺游览,还与另外一位老人刁约(字景纯)互相唱和。此间有《子玉家宴,用前韵见寄,复答之》和《柳氏二外甥求笔迹二首》等诗,可证苏轼曾到柳家探望“十二娘”和外甥。林语堂从此飞驰自己的想象,偏要说苏轼“曾在靖江她家中住了三个月”,显然是望文生义,信口开河。
行文至此,我们必须推算一下“十二娘”的年龄。依照林语堂的说法,“东坡的祖父去世之后,他父亲远游归来,他的叔叔和家属也回来奔丧。这时堂兄堂妹颇有机会相见,也可以一同玩耍。”祖父去逝之时,苏轼年仅十二岁、苏辙才九岁。既然互相之间可成“初恋情人”,那我们姑且将“十二娘”当时计作八岁(不能再小了,如果“十二娘”当时还不到七岁,苏轼与她所谓“相恋”更为无据),那么依据宋代女子十六岁左右出嫁之例,“十二娘”嫁给柳子文时应是八年之后,应在苏轼二十岁,正是进京考进士之时。到了熙宁七年,苏轼三十九岁,“十二娘”也应在三十五岁左右,两个孩子也都应十多岁了,均在读书之际。倘若苏轼与“十二娘”是“初恋情人”,为何林语堂在此前的十九年间,找不到一首苏轼写给“十二娘”的所谓“情诗”?
再来看林氏的第三个证据,也是他推测“初恋情人”的主要依据:
在堂妹家盘桓的那些日子,东坡写了两首诗给她。那两首颇不易解,除非当做给堂妹的情诗看才讲得通。
——《苏东坡传》第十一章《诗人、名妓、高僧》
林语堂所举的第一首“情诗”,只有这样两句:
厌从年少追新赏,闲对宫花识旧香。
林语堂抓住“宫花”大做文章说:“那时他并没坐对宫花,因为他并不是正置身皇宫之内。他说‘厌从年少’的伴侣时,他显然是描写自己;而‘花’照例是女人的象征,‘旧香’可能指一段的旧情。”好嘛,向来与皇宫没有丝毫关系的“十二娘”,竟成了“宫花”的化身。
其实苏轼这两句诗,出自《刁景纯赏瑞香花,忆先朝侍宴,次韵》之中。瑞香花又称“紫蓬莱”,是原生于庐山的一种名贵花卉,直到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0)才被发现,作为祥瑞之物,被移植进了皇宫,朝中大臣为此纷纷写诗赞誉,比如副宰相夏竦的“金盘晓日融春露,黼帐鲜云荫瑞香”(《御阁春帖子》),便是颂贺之词;与苏洵同龄的诗人李觏,也曾写下“闻说仙花玉染红,别留春色在壶中。瑶台若见飞琼面,不与人间梦寐同”(《和天庆观瑞香花》)的名作。刁景纯在仁宗朝曾做过集贤校理,曾有机会侍宴宫中并观赏宫中瑞香,所以他才向苏轼出示《赏瑞香花,忆先朝侍宴》诗。苏轼的唱和之作中,“宫花”意指为何,已经不言自明。苏轼那诗前四句是这样的:
上苑夭桃自作行,刘郎去后几回芳。
厌从年少追新赏,闲对宫花识旧香。
“上苑”即禁中园林,是“宫花”所生之地,“刘郎”一句指刁景纯离开朝廷后,变法日新,旧人逐尽,“厌从年少追新赏”一句,除了描述刁老前辈钟情瑞香、只“识旧香”外,意在称颂他不与变法新进派同调,如果说有“旧情”,则是刁约的皇宫情思。除此之外,政治上失意和托物比兴、抒发落寞情怀,才是苏轼的本意,林语堂的所谓“女人的象征”,纯粹是臆断之后,再加曲解。
再看林氏所列举的第二首诗:
羞归应为负花期,已是成阴结子时,
与物寡情怜我老,遣春无恨赖君诗,
玉台不见朝酣酒,金缕犹歌空折枝,
从此年年定相见,欲师老圃问樊迟。
此诗题为《杭州牡丹开时,仆犹在常、润,周令作诗见寄,次其韵,复次一首送赴阙》,意思是去年牡丹开时,苏轼曾与太守陈襄和钱塘县令周邠共同赴赏。今年花开,他在常州至润州道中,周邠寄诗前来,为此和了两首,一首酬答周邠,另一首寄给太守陈襄。
在前面的《朝云篇》里,我们已经详解苏轼《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中的“花开后院还空落,燕入华堂怪未归”以及“二年鱼鸟浑相识,三月莺花付与公”等诗句。苏轼上面这首诗中的“羞归应为负花期,已见成阴结子时”,仍是借杜牧“绿叶成阴子满枝”来自我揶揄。林语堂大概心存暗恋堂妹之情结,见到这类诗句,便说诗人前一句是在后悔“误了堂妹的青春时期”,第二句“分明说她已儿女成行”。至于下面的“第五和第六句分明他对求婚已迟感到歉咎”更是一派胡言乱语,林氏在前面已言“因为二人同姓,自然联姻无望”,此地却言“求婚已迟感到歉疚”,显然是自抽了一个嘴巴子。而“苏东坡这时写了一首诗,表示愿在常州安居下来,这样离堂妹家不远。他后来的确按照计划在常州买了房子田地,他后来就在常州去世的”,这样的言语就更不值一驳了。众所周知,苏轼想在常州买田,一是因他早年中进士时,在琼林宴上受到宜兴人蒋之奇的诱惑,二因他此行之中,他发现“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 ”,即地肥物美;三因常州人性情友善,苏轼在那里有许多朋友……这些暂且不提,我们只按林语堂的推论方式继续推理,既然苏轼“初恋情人”在润州,苏轼何不在润州买田置地,即便买在常州,也应买在与润州毗邻的丹阳、武进,为什么东坡将田产置于常州最南端的宜兴?那不是舍近而求远了么?
林语堂还有一个所谓证据,就是说苏轼此行“常和堂妹的公公柳谨一同写作游历,他却一次也没提到堂妹丈夫的名字,也没写过一首诗给他。”这说明他对“十二娘”的丈夫柳子文(字仲远)未作过任何考察。柳子文有《次韵呈文潜同年》诗,表明他与张耒一样,都是熙宁六年进士,也就是说,苏轼去润州公干时,柳子文刚刚考上进士,正在朝中等待分配官职,当时根本不在家中。幸亏林氏没有找到这则资料,不然的话,依照他的心理和行事方式,非要说苏轼是趁妹夫不在家之机,才在柳家住上三个月的!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共在三个章节里,大肆渲染苏轼“暗恋堂妹”之事。除了以上两段外,他在第二十八章《终了》里,在叙述东坡自海南归自润州、常州时,更有以下一段文字:
他堂妹的坟墓就在靖江(应为镇江之误),她儿子柳闳现在城内。六月十二日,甚至他身体疲弱之下,他仍然和三个儿子、一侄子,去到堂妹及其丈夫墓前祭祀。他第二次为亡者写祭文。可能是为堂妹写了一篇,另为堂妹夫写了一篇,不过从内容上看不太清楚,不敢确信。第一篇《祭柳仲远文》,先提到的是他妻子堂妹,然后才说:“矧我仲远,孝友恭温。”……
林氏再次无中生有,说东坡“甚至他身体疲弱之下,他仍然和三个儿子、一侄子,去到堂妹及其丈夫墓前祭祀”。第一,东坡自海南归来直至润州,只有幼子苏过在身边作陪,长子苏迈和次子苏迨都在为官之任上,尚未回到东坡身边;第二,两篇祭文都表明,是柳闳前来向舅舅哭诉悲情,求些悼念文字,东坡身在重病之中,根本不可能去堂妹的墓地。
东坡自海南归来,自九江东下,六月初因病先在真州(今江苏仪征)休息,会见米芾之际,便“瘴毒大作”,甚至昏迷不知人事(见苏轼《乞致仕表》),他自知随时都有可能出意外,便给弟弟写信,嘱托了后事。他乘船过江后,被润州太守王觌接住,“到京口,自太守以下,皆不能见 ”,身体赢弱,寻常客人尚不能见,如何“到堂妹及其丈夫墓前祭祀”?此时外甥柳闳远道来见,痛述其母去逝后,父亲及弟弟也相继去世,并递上一份他亲自抄写的《楞严经》,请老舅写点题跋文字。东坡在岭南时,只知堂妹“十二娘”病故,并为她写过《祭亡妹德化县君文》,病中惊闻妹夫及一个外甥也先后死去,不禁大悲,于是又写下《祭柳仲远文》二篇,分别祭奠妹夫与堂妹,文中“一恸海徼,摧胸破肝,痛我令妹,天独与贤”,乃病危之人的伤痛之语,“矧我仲远,孝友恭温。天若成之,从政有闻”,是对妹夫的由衷赞叹。面对柳闳的“衔痛远诉”,东坡极力劝慰:“逝者已矣,存者何冤?慎勿致毁,以全汝门!”当柳闳说到要做老舅那样的人时,东坡叹道:“我穷且老,似舅何益?易其墓侧,可置万室。”这里的“衔痛远诉”,分明是说柳闳远离守丧之地,到驿馆里面来见东坡,“易其墓侧”,是让外甥将他两篇祭文拿回去,重新刻石;“可置万室”,是劝柳闳在其父母墓地之旁建造佛龛,《妙法莲华经》卷四云:“五千栏楯,龛室千万,无数幢幡,以为严饰”,宋人陆文圭《挽晋千户》诗中的“护丧诸子皆称孝,万室他年置墓旁”,便是此意。
值得说明的是,在以上一段时间内,能够确考东坡行程的,惟有五月二十九日,他在真州有一篇书简,还有六月十四日在润州给章敦的儿子章援写过一封信。林氏传记中“六月十二日”如何如何,全是小说家的推断之辞。
林语堂无视苏轼这两篇祭文中的关键字句,臆造了东坡抱病祭祀堂妹的情节,在下文中还别有用心地渲染道:
第二天,客人去看他,发现他侧身面壁而卧,硬咽抽搐,竟至不能起床接待他们。来访的客人之中有已故的宰相苏颂之子,以为苏东坡是为他的亡父而哭。苏颂亡时年八十二岁。苏颂家虽然与苏东坡同姓,却不是同一省籍。苏东坡与苏颂相识,已有三四十年,但是若说他听他老友之死会伤心到如此程度,实难令人相信。并且,在前一天,苏东坡听到他死的消息时,也没亲自到墓前去祭奠,只是派长子苏迈去过。他这种悲伤的原因,我相信,必须从上面引证的祭文里去看。
为了说明东坡对所谓“初恋情人”的深情,林语堂不惜对东坡与苏颂的情谊妄加贬低。林氏只知“苏颂家虽然与苏东坡同姓,却不是同一省籍”,却不知他们同一个祖先,都是汉代名臣苏武的后裔,而且还在同一所监牢里做过难友。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乌台诗案”被关进御史大狱,苏颂也因陈世儒之妻逼杀庶母案牵连,被关在他的隔壁。苏颂听到台吏审讯苏轼时的恶声戾语,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飞语初腾触细文,
廷中交构更纷纭。
纲条既甚秋荼密,
枉直何由束矢分。
狱吏焰狂压长者,
府徒谁识故将军?
遥怜比户吴兴守,
诟辱通宵不忍闻。
源流同是子卿孙,公自多才我寡闻。
谬见推称丈人行,应缘旧熟秘书君。
文章高绝诚难敌,声气相求久益勤。
莫叹歌诗致数厄,圣朝终要颂华勋!
——苏颂《元丰己未三院东阁作十四首》之五、之十三
译介《苏东坡传》的人,称赞此书于“考据、义理、词章三要点,林语堂先生做到了,也是写传记文学的人必须做到的”(见《译者序》),此语只能糊弄那些对苏东坡一知半解的人。在《苏东坡传》第十四章《逮捕与审判》里,林语堂对苏颂与东坡既惺惺相惜、又肝胆相照的情谊置若罔闻,反过来还要质疑东坡“听他老友之死会伤心到如此程度,实难令人相信”,这说明他对苏轼的理解,只是皮毛而已。
必须申明,作为现代文坛的一个重要作家,林语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自有他的位置,后来旅居美国,他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化名人,同样功不可没,笔者在此决无将他全盘否定之意。
同时还要说明,林语堂不是苏学专家,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他的《苏东坡传》像孔凡礼的《苏轼年谱》、《三苏年谱》一样,态度严谨、资料翔实,然而传记不同于小说,小说的作者可以凭籍想像的翅膀,任意驱使苏轼去当自己的替身,实现他梦寐以求的某种夙愿,而传记必须尊重史实,不能在没有凭据的情况下,望风捕影,随意发挥。
仔细考察林语堂的生平,我们便会发现,原来他从童年起,就曾偷偷地与一个侄女辈的女孩恋爱,《赖伯英》便是他的自传体小说,小说中的男孩“新洛”便是他自己。那个化名“赖伯英”的女孩,还曾为新洛而怀孕。尽管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竭力否定这件不太光彩的事,可林语堂自己在《八十自叙》中说得十分明白:“赖伯英是我初恋的女友!”这段恋情结束后,他又与自己同窗好友陈希庆的妹妹陈锦瑞恋爱,二人的关系也是无果而终,最后,他娶了厦门富商、豫丰钱庄老板廖悦发的女儿廖翠凤为妻。后来陈锦瑞嫁给了别人,二人还经常见面,直到晚年,他还在喃喃自语说,他从外地回来:“总在我好友的家逗留,因为我热爱我好友的妹妹。”连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也不得不承认,“父亲对陈锦瑞的爱情始终没有熄灭……在父亲心灵最深之外,没有人能碰到的地方,锦瑞永远占一个位置” 。
不言而喻,所谓苏轼终生都在“暗恋堂妹”的说法,是林语堂将自己的两个心结纠集在一起,强行加给苏轼的。他煞有介事的诗歌分析和所谓东坡晚年的情景描绘,早已脱离传记文学的写实手法,进入小说的虚构状态,在借传主之身,寄托自己的落寞情怀。这不仅是十足的穿凿附会,也是《苏东坡传》中的最大败笔,
谬说搅乱视听,必须加以厘清。若是任其流传,不仅东坡先生要继续遭受世人的误解,恐怕林语堂在另一个世界里,心灵依然不能安宁,深忧东坡先生要将他捉取至前,调笑揶揄、扯耳面批矣。
放开心扉吧,既然都各自成家了,就代表重新开始了,何必为以前的事情而苦恼呢?也许人家早就不介怀了,而且说不定他现在很幸福,再说没有一个妻子是不介意丈夫的前任的,何必再去打扰他的生活呢。不过如果你是在是介意的话,可以找个时间好好谈谈,道歉取得他的原谅,最后相视一笑泯恩仇是最好的结局不是吗?加油啦~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表白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