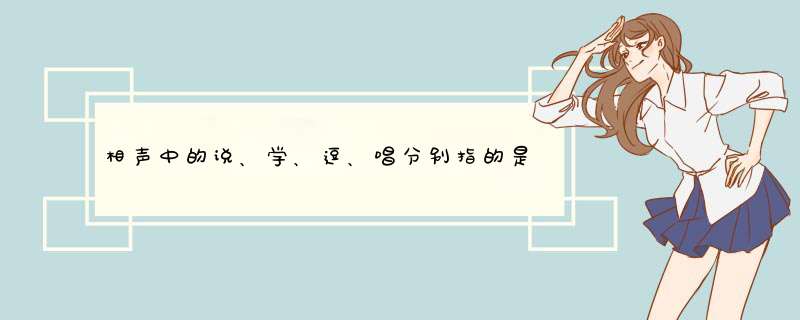
相声起源于中国北方的民间歌舞,在明代开始流行。相声是关于“说、学、逗、唱”,“说”指的是笑话、故事、灯谜、喝酒命令;“学”指学人言、鸟语,市声、叫声;“逗”指插科打诨,抓哏逗趣;“唱”指唱“太平歌词”、戏曲小调,相声演员把“说、学、逗、唱”作为培养相声演员的“四大科目”。
首先,我想知道演员是不是不会唱歌,也不会放弃唱太平歌词很纠结,说、学、逗、唱,戏弄和唱歌本身就是一种技能,是动词的分类,而不是歌曲的类型。歌唱也没有特别提到,只是一种技巧,其次,我对郭德纲说的唱京剧、唱歌是学唱完全同意,只能说学习和歌唱的技巧在这里得到了应用,而不是学习而不是歌唱。
一些北京人嘲笑那些从这些地方来到北京工作的人是“懦夫”,并错误地称他们为“一张嘴吃蚱蜢种子,两条腿上沾满黄土泥的懦夫”,带有明显的鄙视成分。后来发展到模仿山西话、胶东话、天津话、宝坻话、唐山话,20世纪30年代初,扩展到上海话、苏州话和粤语,解放后,也有模仿外国口味的汉语词汇和海外华人说的普通话,学着做小生意大喊大叫,也叫商品之声,主要是模仿卖大大小小的鱼、卖茶鸡蛋、卖熏鱼油炸面筋、卖硬面悖论、卖馄饨、卖布头、卖衣服、卖包子的喊叫声。
相声是通过“绕口令”或“贯口”,练习语言节奏。事实上,“说、学、逗、唱”不是一种科学的分类方法,既不能概括相声艺术的内容,也不能解释相声艺术的表现形式,四者之间没有逻辑关系。
意思是:终庄周梦蝶,你是上天给予的恩赐也是我的劫数,具体意思要根据语境判断,可能是对方表白,也可能是表达不满。回复的话根据具体语境回复。
这两句诗出自于德云社张九南的定场诗,全诗如下:
终是庄周梦了蝶,你是恩赐也是劫,
终是李白醉了酒,你是孤独也是愁,
终是荆轲刺了秦,一代君王一世民,
终是妲己祸了国,万里江山似蹉跎,
终是玉环停了曲,无人再懂琵琶语,
终是韩信放下枪,你是宿命也是伤,
终是悟空成了佛,你一堕落便是魔,
终是霸王别了姬,弃了江山负了你,
终是后羿断了箭,此生注定难相见,
终是评书已截止,从此告别定场诗。
请及时采纳
中国戏曲:声音在耳 情形在目
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戏曲,是由歌、舞、剧三者有机地融合为一体,而以剧情为主的一种民间舞台艺术。它是中国古老传统文化中经久不衰的一朵奇葩,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和戏曲艺术家们的伟大创造。
戏曲渊源于秦汉的乐舞、俳优和百戏。唐代有参军戏,北宋时形成宋杂剧(金称“院 本”)。南宋时温州一带产生的戏文,一般认为是中国戏曲最早的成熟形式。金末元初在北方产生了元代杂剧,戏曲创作和演出已空前繁荣,出现了像关汉卿、王实甫、白朴等一大批剧作家和深受人民喜爱的戏曲作品和艺人。到明清两代,又在戏文和杂剧的基础上形成了传奇剧。各地方剧种也蓬勃发展,以昆腔、京剧为代表,创造了丰富的戏曲文学和完整的舞台艺术体系。
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最大特点是以人为核心。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根本特点是“虚”和“空”。所谓“虚”和“空”,是指它在舞台表现上,不同于话剧和歌剧,基本没有什么舞台美术和装置。传统的戏曲表演形成“空台艺术”的物质原因,自然是那种三面观的民俗戏台建筑。但是,中国戏曲选定了这种“空舞台”的表演方法,还有其更深层的道理,那就是中国戏曲文化在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所接受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启迪。中国传统的戏曲艺术,正是遵循这“有生于无,实出于虚”的人生之“道”进行的艺术实践。所以,它所依靠的不是小小的有限的舞台上的布景与陈设,而是“人”。因之,它尽管囊括了诸多的艺术因素,但多种艺术因素却是以人的表演为其中心。
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又一特点,是以写情为主旨。
明末清初的文艺理论家也是戏曲评论家李渔认为戏曲的“大纲”,则不出“情景二字”,还说“情自中生,景由外得”,“妙在印景生情”,并强调“务使一折(指戏曲)之中,七情具备”。在中国浩如烟海的传统戏曲作品中,描述人之丰富情感者比比皆是。像《杨门女将》、《王佐断臂》中杨家将、岳家军那种反抗侵略、前仆后继,体现中华民族精神和意志的爱国之情;像《逼上梁山》、《野猪林》、《打渔杀家》中林冲、鲁智深、肖恩那种反抗封建统治的愤怒、反抗之情;像《铡美案》、《四进士》中包拯、宋世杰那种主持公道、铁面无私、扶小救弱的正义之情;像《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天仙配》中白蛇娘娘与许仙、梁山伯与祝英台、七仙女与董永等男女主人公所体现的那种热爱自由、心地善良、向往美好生活的真挚爱情等等。戏曲演出,往往是情溢舞台,情满剧场,情入人心,父子、母女,夫妇,兄妹,姐弟,亲友,师生之间,喜、怒、哀、乐、啼、笑、羞、媚、骄、娇、嗔、痴、气、急、怨、恨、惊、恐、悲、惘、迷、怜……六欲七情,表现得无不酣畅淋漓,无一不震撼观众的心灵,引起心弦的颤动,使无数观众热泪盈眶、唏嘘不止。
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第三个特点是十分重视和讲求情节安排和结构布局。
一是在展开故事情节时,采用了上场人物的自我表白,行话称作“做表”。这是中国传统戏曲别具一格的地方。“做表”包含着很丰富的意义:它概括人物的性格特征,概述人物身世,交待环境,表露情绪,烘托气氛,甚至于复述事情经过……更为重要的是,还对整出戏的布局做了“启示”,在结构上起到“交待”、“开端”的作用。二是在情节布局上讲求一种让观众明白、不让剧中人明白的处理方法。像越剧《红楼梦》中描写宝玉结婚时,观众已知新娘不是黛玉,而剧中人宝玉却不知,还兴高采烈喜不胜喜,这就非常强地加强了该戏的悲剧效果,同时也紧紧勾着观众之心。又如京剧《杨门女将》一开始即通过“孟焦报丧”,使观众明白边关吃紧、宗保阵亡,但剧中人还不明白,因而产生了“发现”、“惊变”、“陡转”等一系列情节发展。三是充分调动观众的情绪,使其心里蕴藏着长时间的等待和焦急。像折子戏《除三害》便是运用这种方法的典型。在吉询向周处叙述第一害时,观众已做了情绪上的准备;叙述第二害时,观众情绪产生了一个趋向突变的趋势,而在第三害表明之前,吉询却不再唱了,来了一个“触动”却“不立刻发生”的停顿,观众在这惊变“要现未现”的当口,显得十分焦急。正是这种布局,即使已经看过多遍的观众,虽早知道第三害是什么,但还会被那个“不立刻发生”的停顿,搞得十分焦急,而始终处于兴致勃勃的情感状态。四是在整体布局上,往往讲求有头有尾,线索单纯,结局一般是“大团圆”,善恶结果都有明确交代。这些全都具有其不可低估的艺术魅力。
中国传统戏曲之所以颇具魅力,生命长青,除上边所谈之外,更为主要的特点是其独特的舞台艺术表现形式,即它的综合性、技术性、程式性、夸张性和虚拟性。正是由于具有这种独具一格的表现形式,使其无论在叙事拟人,表意抒情方面,做到了既不是凭空地直诉,也不是苍白地呻吟,而是将具体的人物形象,即生动丰富的戏曲舞台形象诉诸观众,是看得见、听得着、摸得到的客观存在。
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综合性,其程度远远超过话剧、歌剧、舞剧等其它综合性艺术。它不仅是视觉艺术,也是听觉艺术,即使仅仅依凭唱腔、道白和“文武场”音乐(通过广播),也能构成形象,听众也能据此理解剧情,理解人物的情感,明白人物在想什么在做什么。
其次,是它的技术性。一个戏曲演员必须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他或她不仅要有歌唱演员那样的好嗓子和演唱技巧,也需要有话剧演员那样良好的音色、音质和表演才能,还要有舞蹈演员那样良好的体形和严格的舞蹈基本功,甚至还要有杂技演员那样娴熟的技巧和武术家的出色的功夫。
第三是它的程式性。所谓程式,就是将形态的某些要素定格化后加次遵守之,沿用之,也就是戏曲各艺术因素的组织化、节奏化和美化。中国戏曲从创作到表演,从舞台装置到服装、化妆、从文学到音乐,从声乐到器乐等等各个部分,整个艺术表现都有一套程式。从剧本创作来看,主要角色上场常常是先打引子,再念定场诗,然后自报家门,自述身世等等。这种手法在许多戏中都用,长此以往,便形成了一种编剧的程式。从表演方面来看,各种身段与动作表现都有相应的特定用途一切动作几乎都是规范的,而且常常要配以音乐锣鼓点。亮相、打背供之类,也都有程式。从音乐方面来看,各种板式与腔调都有一定的规格,什么情绪下用什么腔,也有其基本规范。如悲哀是用反调,哭时用哭头、大悲调、哭迷子等,抒情时用慢板,叙事时用二六、二八、原板等等。板式与板式之间的衔接也有一定的规律。
根据戏曲程式的要求,扮演不同人物的角色又叫“行当”。所谓“行当,就是指剧中人物的不同的身份、年龄、性格、扮相,以及表演上唱、念、做、打的不同要求而划分的人物类型,基本上有生、旦、净、末、丑等几类。中国传统戏曲的魅力正是其通过“程式”的灵活运用,“行当”造型的生动鲜明,充分调动艺人唱念做打“四功”及口眼手身步“五法”等艺术因素和艺术手段,在舞台上塑造出一个又一个充满丰富情感的戏曲舞台人物形象。
四是夸张性。从常识来讲,各种艺术均有夸张的特点,但像中国传统戏曲如此大胆地夸张实属罕见。我们可以把戏曲与话剧作一比较就不难看出:话剧艺术是通过逼真的外在形象,表现生活内在的或本质的真实;而戏曲则是通过近似的形象,表现生活内在的或本质的真实。首先,戏曲可以把某个动作,某段念白、某个情节加以强调、夸张,使之比真实生活更加突出,更加鲜明。在戏曲艺术中,只有用似乎违背生活真实的夸张才能达到艺术的真实。其次,是把某些情节、某些念白加以精炼、简化、使之比真实生活还要简短。它的主要目的是对那些非主要情节,但又必须交待的情节,用几句话和几个动作一下就带过去了。
五是虚拟性。在中国传统戏曲舞台上,无论表现什么样的主题,塑造什么样的人物,舞台上一般不用“景”,只设一张台子两把椅子,并没有实在的、立体的景物。如此,戏曲中人物形象的“生活背景”,则完全要靠人物的动作给以虚拟。这种虚拟随心所欲,流畅自然,而且顷刻可变,且变化无穷。大到山水城寨,小到一针一线,全然靠了艺人优美潇洒的动作,使观众会意而联想出那幅“景”来。这种虚拟的“示意”和“象征”减少了观众的视觉分散,使其可以把精力完全集中在人物形象上,看他(她)的“做”和“打”,听他(她)的“唱”和“念”,领略他或她在表现人物的喜怒哀乐、惊恐悲欢,或是在站坐走停、举手投足,以及仪态风度。
总之,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独特形式和艺术魅力,不外乎有人、有情、有故事情节、有独特的艺术形式。人为核心,情为主旨,布局是其魅力的“组织完成”,固定程式是其美化的链条。正是这些独特的东西,构成了中国传统戏曲之所以“勾魂、摄魂”“使人看过数日而犹觉声音在耳、情形在目”(李渔《闲情偶寄》中语)的魅力之所在。
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戏曲,是由歌、舞、剧三者有机地融合为一体,而以剧情为主的一种民间舞台艺术。它是中国古老传统文化中经久不衰的一朵奇葩,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和戏曲艺术家们的伟大创造。
戏曲渊源于秦汉的乐舞、俳优和百戏。唐代有参军戏,北宋时形成宋杂剧(金称“院 本”)。南宋时温州一带产生的戏文,一般认为是中国戏曲最早的成熟形式。金末元初在北方产生了元代杂剧,戏曲创作和演出已空前繁荣,出现了像关汉卿、王实甫、白朴等一大批剧作家和深受人民喜爱的戏曲作品和艺人。到明清两代,又在戏文和杂剧的基础上形成了传奇剧。各地方剧种也蓬勃发展,以昆腔、京剧为代表,创造了丰富的戏曲文学和完整的舞台艺术体系。
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最大特点是以人为核心。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根本特点是“虚”和“空”。所谓“虚”和“空”,是指它在舞台表现上,不同于话剧和歌剧,基本没有什么舞台美术和装置。传统的戏曲表演形成“空台艺术”的物质原因,自然是那种三面观的民俗戏台建筑。但是,中国戏曲选定了这种“空舞台”的表演方法,还有其更深层的道理,那就是中国戏曲文化在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所接受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启迪。中国传统的戏曲艺术,正是遵循这“有生于无,实出于虚”的人生之“道”进行的艺术实践。所以,它所依靠的不是小小的有限的舞台上的布景与陈设,而是“人”。因之,它尽管囊括了诸多的艺术因素,但多种艺术因素却是以人的表演为其中心。
其次,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以写情为主旨。明末清初的文艺理论家也是戏曲评论家李渔认为戏曲的“大纲”,则不出“情景二字”,还说“情自中生,景由外得”,“妙在印景生情”,并强调“务使一折(指戏曲)之中,七情具备”。在中国浩如烟海的传统戏曲作品中,描述人之丰富情感者比比皆是。像《杨门女将》、《王佐断臂》中杨家将、岳家军那种反抗侵略、前仆后继,体现中华民族精神和意志的爱国之情;像《逼上梁山》、《野猪林》、《打渔杀家》中林冲、鲁智深、肖恩那种反抗封建统治的愤怒、反抗之情;像《铡美案》、《四进士》中包拯、宋世杰那种主持公道、铁面无私、扶小救弱的正义之情;像《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天仙配》中白蛇娘娘与许仙、梁山伯与祝英台、七仙女与董永等男女主人公所体现的那种热爱自由、心地善良、向往美好生活的真挚爱情等等。戏曲演出,往往是情溢舞台,情满剧场,情入人心,父子、母女,夫妇,兄妹,姐弟,亲友,师生之间,喜、怒、哀、乐、啼、笑、羞、媚、骄、娇、嗔、痴、气、急、怨、恨、惊、恐、悲、惘、迷、怜……六欲七情,表现得无不酣畅淋漓,无一不震撼观众的心灵,引起心弦的颤动,使无数观众热泪盈眶、唏嘘不止。
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第三个特点是十分重视和讲求情节安排和结构布局。一是在展开故事情节时,采用了上场人物的自我表白,行话称作“做表”。这是中国传统戏曲别具一格的地方。“做表”包含着很丰富的意义:它概括人物的性格特征,概述人物身世,交待环境,表露情绪,烘托气氛,甚至于复述事情经过……更为重要的是,还对整出戏的布局做了“启示”,在结构上起到“交待”、“开端”的作用。二是在情节布局上讲求一种让观众明白、不让剧中人明白的处理方法。像越剧《红楼梦》中描写宝玉结婚时,观众已知新娘不是黛玉,而剧中人宝玉却不知,还兴高采烈喜不胜喜,这就非常强地加强了该戏的悲剧效果,同时也紧紧勾着观众之心。又如京剧《杨门女将》一开始即通过“孟焦报丧”,使观众明白边关吃紧、宗保阵亡,但剧中人还不明白,因而产生了“发现”、“惊变”、“陡转”等一系列情节发展。三是充分调动观众的情绪,使其心里蕴藏着长时间的等待和焦急。像折子戏《除三害》便是运用这种方法的典型。在吉询向周处叙述第一害时,观众已做了情绪上的准备;叙述第二害时,观众情绪产生了一个趋向突变的趋势,而在第三害表明之前,吉询却不再唱了,来了一个“触动”却“不立刻发生”的停顿,观众在这惊变“要现未现”的当口,显得十分焦急。正是这种布局,即使已经看过多遍的观众,虽早知道第三害是什么,但还会被那个“不立刻发生”的停顿,搞得十分焦急,而始终处于兴致勃勃的情感状态。四是在整体布局上,往往讲求有头有尾,线索单纯,结局一般是“大团圆”,善恶结果都有明确交代。这些全都具有其不可低估的艺术魅力。
中国传统戏曲之所以颇具魅力,生命长青,除上边所谈之外,更为主要的特点是其独特的舞台艺术表现形式,即它的综合性、技术性、程式性、夸张性和虚拟性。正是由于具有这种独具一格的表现形式,使其无论在叙事拟人,表意抒情方面,做到了既不是凭空地直诉,也不是苍白地呻吟,而是将具体的人物形象,即生动丰富的戏曲舞台形象诉诸观众,是看得见、听得着、摸得到的客观存在。
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综合性,其程度远远超过话剧、歌剧、舞剧等其它综合性艺术。它不仅是视觉艺术,也是听觉艺术,即使仅仅依凭唱腔、道白和“文武场”音乐(通过广播),也能构成形象,听众也能据此理解剧情,理解人物的情感,明白人物在想什么在做什么。
其次,是它的技术性。一个戏曲演员必须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他或她不仅要有歌唱演员那样的好嗓子和演唱技巧,也需要有话剧演员那样良好的音色、音质和表演才能,还要有舞蹈演员那样良好的体形和严格的舞蹈基本功,甚至还要有杂技演员那样娴熟的技巧和武术家的出色的功夫。
第三是它的程式性。所谓程式,就是将形态的某些要素定格化后加次遵守之,沿用之,也就是戏曲各艺术因素的组织化、节奏化和美化。中国戏曲从创作到表演,从舞台装置到服装、化妆、从文学到音乐,从声乐到器乐等等各个部分,整个艺术表现都有一套程式。从剧本创作来看,主要角色上场常常是先打引子,再念定场诗,然后自报家门,自述身世等等。这种手法在许多戏中都用,长此以往,便形成了一种编剧的程式。从表演方面来看,各种身段与动作表现都有相应的特定用途一切动作几乎都是规范的,而且常常要配以音乐锣鼓点。亮相、打背供之类,也都有程式。从音乐方面来看,各种板式与腔调都有一定的规格,什么情绪下用什么腔,也有其基本规范。如悲哀是用反调,哭时用哭头、大悲调、哭迷子等,抒情时用慢板,叙事时用二六、二八、原板等等。板式与板式之间的衔接也有一定的规律。
根据戏曲程式的要求,扮演不同人物的角色又叫“行当”。所谓“行当,就是指剧中人物的不同的身份、年龄、性格、扮相,以及表演上唱、念、做、打的不同要求而划分的人物类型,基本上有生、旦、净、末、丑等几类。中国传统戏曲的魅力正是其通过“程式”的灵活运用,“行当”造型的生动鲜明,充分调动艺人唱念做打“四功”及口眼手身步“五法”等艺术因素和艺术手段,在舞台上塑造出一个又一个充满丰富情感的戏曲舞台人物形象。
四是夸张性。从常识来讲,各种艺术均有夸张的特点,但像中国传统戏曲如此大胆地夸张实属罕见。我们可以把戏曲与话剧作一比较就不难看出:话剧艺术是通过逼真的外在形象,表现生活内在的或本质的真实;而戏曲则是通过近似的形象,表现生活内在的或本质的真实。首先,戏曲可以把某个动作,某段念白、某个情节加以强调、夸张,使之比真实生活更加突出,更加鲜明。在戏曲艺术中,只有用似乎违背生活真实的夸张才能达到艺术的真实。其次,是把某些情节、某些念白加以精炼、简化、使之比真实生活还要简短。它的主要目的是对那些非主要情节,但又必须交待的情节,用几句话和几个动作一下就带过去了。
五是虚拟性。在中国传统戏曲舞台上,无论表现什么样的主题,塑造什么样的人物,舞台上一般不用“景”,只设一张台子两把椅子,并没有实在的、立体的景物。如此,戏曲中人物形象的“生活背景”,则完全要靠人物的动作给以虚拟。这种虚拟随心所欲,流畅自然,而且顷刻可变,且变化无穷。大到山水城寨,小到一针一线,全然靠了艺人优美潇洒的动作,使观众会意而联想出那幅“景”来。这种虚拟的“示意”和“象征”减少了观众的视觉分散,使其可以把精力完全集中在人物形象上,看他(她)的“做”和“打”,听他(她)的“唱”和“念”,领略他或她在表现人物的喜怒哀乐、惊恐悲欢,或是在站坐走停、举手投足,以及仪态风度。
总之,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独特形式和艺术魅力,不外乎有人、有情、有故事情节、有独特的艺术形式。人为核心,情为主旨,布局是其魅力的“组织完成”,固定程式是其美化的链条。正是这些独特的东西,构成了中国传统戏曲之所以“勾魂、摄魂”“使人看过数日而犹觉声音在耳、情形在目”的魅力之所在。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表白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