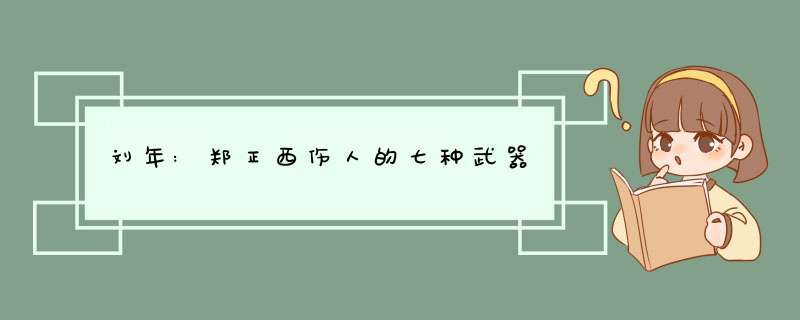
郑正西伤人的七种武器
作者:刘年
1
把诗坛比作江湖的话,郑正西像极了星宿老仙丁春秋。
老当益壮,而且,擅长用毒。
2
我脸皮厚,胆子小,郑正西攻击了我四年,只字未回。
他得势不饶人,到如今,伤害了越来越多的诗人,甚至伤害到了诗歌本身。再不站出来,有点对不住自己的良心了。这里介绍一下他的为人和手段,仅供各路豪杰参考。如有雷同和巧合,以新华社的通稿为准。
他招式繁杂,总结起来有七种武器。
这七种武器,都在我身上用过,每一种都大获成功。
3
第一种武器,诗歌。
我经常说,诗歌是人间的药,但被他一用,就变成了毒药。
初级拉关系的时候,就这样:你不听我话,我就不转载不编选你的诗歌,哪怕你写得再好;你听我话,你写的再烂我都会推荐你。
当升级到他想斗人的时候,就把你最烂的作品拿出来,说你水平低。大家都知道,艺术和木桶不同,木桶是以最短的那块决定你的盛水量,而艺术是以最高的那一部分作品代表你的成就。李杜写了几百首烂诗,并不影响他们的伟大。没有烂诗的实验尝试,也很难创作出好诗来。郑正西无数次说雷平阳写得不好,却从未提他《春风咒》《大江东去帖》《集体主义虫叫》等代表作。骂了余秀华三年,也不敢正视她的《我爱你》《我养的小狗,叫小巫》《下午,在田埂上摔了一跤》。
当升级到他想置你于死地的时候,也就是最毒的时候,把你的诗歌进行曲解,给你扣政治帽子,给你封建社会才有的文字狱。因为他知道,所有的诗歌都会有歧义,都可以曲解。
幸好,他没有一统诗坛,要不然,会有多少好诗人会打进冷宫。
幸好,他没有一统天下,否则,这片土地上又要多多少白骨和冤魂。
4
第二种武器,仇恨。
有良知的诗人都会这样认为,诗歌是人类用来传递温暖、爱和希望的,是用来化解仇恨和隔膜和围墙的。在荒凉的人世,我们用诗歌取暖和安慰。
在郑正西手里,诗歌是用来制造仇恨的。几乎他所有的文章都充满戾气,满口大字报风格,非白即黑,表决心,戴帽子,攻击人身,攻击私生活,上线,上纲,顺者昌,逆者亡,反对他的人都是敌人,“敌人”做的一切都是错的,“敌人”支持的他就反对,“敌人”反对的他就支持,诗人应有的宽恕、包容、慈悲和温暖,在他的文章中半点都看不到。
通过作品的对比,制造诗人和诗人的仇恨,制造官刊与民刊的仇恨,制造编辑与作者的仇恨,制造暂时没发表的作者和发表过的作者的仇恨。他很清楚,大家有了仇恨,他的斗争手腕才会变得重要,当世界充满爱和温暖的时候,他这种人,便没有了用武之地。
其实,真正了解当下诗歌的人都知道。官刊(有刊号的正规刊物)民刊互为补充,互相尊重,官刊经常选民刊的诗,民刊也经常用官刊的作者。中国的诗歌无论创作上还是影响上,最近都有了不小的起色,其实是官刊民刊诸多优秀的编辑,和优秀的诗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但他就看不惯,说现在的诗人曝光率太高,诗歌奖太多,诗歌活动太多,甚至《诗刊》涨稿费,他都看不惯。
让辛苦、清贫的诗人过好一点,不好吗
出版商愿意出诗集了,不仅不收诗人的钱而且还给诗人稿费,不好吗
电视节目新闻媒体愿意接纳诗人和诗歌了,这不好吗
老百姓在喜欢新诗了,愿意买诗集了,不好吗
年轻人可以仅凭才华、诚实和勤奋就可以出人头地,不好吗
让这个物欲的人间,多一些爱诗读诗的人,多一些诗意的栖居,不好吗
5
第三种武器,反腐。
这是郑正西最常用的武器,这种武器,也最毒,百试不爽。
因为他知道,所有的人都对腐败深恶痛绝。包括我自己也是。
反腐的时候,一定要讲证据,讲法律,因为每个名字后面都是一个温暖的生命,每个生命后面,可能都有一个家庭、半生努力。但在郑正西的眼里,我恨你,你就是腐败,你反对我,你就是阻止我反腐败。当说一个有权者腐败,他将永远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当能说一个有权者腐败,而不需要证据的时候,他将无往而不胜。当我们能说一个有权者腐败,而不需要证据的时候,我们将退回到那个丛林社会。
他说朱零腐败,有权色交易,他认为在十多年事业发展部的岗位上,必然有大量的权钱和权色交易,经反复调查,没有。他说商震腐败,有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认为一个国刊的常务副主编,有各种机会贪污,经反复调查,没有。他说李少君腐败,有权色交易,经反复调查,也没有。他说我有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经查也没有。我曾经不止一次痛斥给我送钱的作者,至今还被人记恨。
这年头,有人清白,有人坚守,只是某些人看不见或者不愿看见。
6
第四种武器,谎言。
他的谎言太多,只要他自己写的,几乎每一篇都有。在你不知道不经意的角落,他会动手脚。“移花接目”“断章取义”“混水摸鱼”“混淆是非”“指鹿为马”是最常用的'几招。他知道,真正清楚内情的人不多,也不会立马站出来。就是事后指出来了,他想要达到的效果早就达到了。
前段时间,还在帖子上说我是“见习编辑”,最近,又说我是《诗刊》的“接班人”,这两个身份隔着几条长安街,怎么可能他硬说《诗刊》推出余秀华《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诗刊发表的是《打谷场上赶鸡》组诗里面,根本没有这首诗。前几天,他说巡视组开会,时间都精确到分钟了,内容列了八条,第一条劈头盖脸的一句“作协存在权色交易”,今天我看到的原文是“有人反映有的领导干部在评奖中搞权钱、权色交易”,掐头去尾,意思就全变了。他不去写间谍小说,宫廷剧本,真是浪费了。
谎言,是有毒的,而且有剧毒(详细说明,参见拙文《你真诚地叙述,我会真诚地听》)。
7
第五种武器,识时务。
有人说郑正西是疯狗,我真不赞成,他的智商很高。
他知道他七十五岁了,别人会同情老者,所以纵情诽谤(其实他是1946年生人,只有71岁,连自己的年龄都撒谎)。
他知道自己写不好诗,也编不好诗,要拥有话语权,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制造事端,制造新闻,攻击最出名的诗人和编辑。他知道什么东西最吸引眼球,无限制地编造情色故事,让一些女诗人惶惶不可终日,一个在上海的打工女诗人,因此不敢写诗歌了。
他从不咬真正有权势的人。他矛头,只对准诗人,而且是那些认真写诗认真编诗的人。他知道,对诗歌越认真的人,越容易欺负,因为这些诗人都有良心、有坚持,都自命为君子、高士,不计小人过。随便算一下,他攻击的谢冕、吉狄马加、商震、李少君、于坚、雷平阳、谢有顺、林莽、金铃子、荣荣、朱零、李琦、李犁、陈先发、西娃、霍俊明、潘维、玉珍、颜梅玖、杨克、汤养宗、夏午、张二棍、侯马、李元胜、林莉、陈仲义、高洪波、庞培、何三坡……等等,哪一个不是谦谦君子。相反,不明真相的诗坛吃瓜群众,反而是他团结的对象。
他还知道攻击《诗刊》和《人民文学》最有效,其一,他们名声大,反响大;其二,国刊的人不会放下公务和他计较;其三,在国刊上能发表的毕竟是少数,没有发表的诗人,都可以是他潜在的支持者。
显然这一系列选择,他都是对的。
只是,他忘记了四个字,“邪不胜正”。
8
第六种武器,执著。
他深知,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不停地说,反复地说,他有的是精力和时间。他的帖子又不要证据,不要逻辑,只需把几个黑白分明的词语堆上去即可,和大字报一样,一天能写好几个帖子。
他曾连续三年,用几百个帖子骂余秀华。他认为,伤到了余秀华,就伤到了《诗刊》。余秀华作为一个优秀的农民女诗人,生活艰辛。《诗刊》发表推荐余秀华那组《打谷场上赶鸡》没有任何色情和政治问题。最后余秀华的命运得到了改变,由喂兔子年收入四百块的农村残疾妇女,变成了一个影响到全国的诗人,无论对余秀华本人,还是整个诗歌文化,都是一大善举。但在郑的眼里,成了罪过。无底线地攻击她,还涉及她的私生活、他的老公和上大学的儿子,其手段之阴狠、用词之恶毒,不了解内情的人,还以为余秀华是吕后、妲已、汪精卫,卖了国,殃了民。
有一段时间,还真担心余秀华自杀。
9
第七种武器,底线。
郑正西没有底线,就好比丁春秋的化功大法。
你有底线,他没有。你有原则,他没有。你有诗歌要写,他没有。你有工作要做,他没有。你有家人和孩子要养,他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没有底线,他的手段更多,战术更加灵活。你跟他说诗歌,他跟你讲道理,你跟他讲道理,他跟你讲政治,你跟他讲政治,他跟你讲私生活,你跟他讲私生活,他跟你说谎,你拆穿他的谎言,他的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谎言早就酝酿好了。你把他所有的谎言都揭穿,他又跟你耍流氓。你总不能跟着耍流氓吧。
这次又大获全胜,连续刷屏,成了诗坛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
他苦苦追求的出名,终于达到了。
“星宿老仙,法驾中原。神通广大,法力无边”!
“星宿老仙,法力无边。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文字像精灵,只要你用好它,它就会产生让你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无论我们说话还是作文,都要运用好文字。只要你能准确灵活的用好它,它就会让你的语言焕发出活力和光彩。下面,我为大家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脑瘫诗人余秀华的励志故事 篇1余秀华,女,生于1976年,湖北钟祥市石牌镇横店村村民。因出生时倒产、缺氧而造成脑瘫,使其行动不便,高中毕业后赋闲在家。2009年开始写诗,代表作《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经过墓园》、《摇摇晃晃的人间》等,作品被《诗刊》微信号发布后,她的诗被热烈转发,人们赞叹她诗歌里的文字质朴滚烫、直击人心、有力量。
她在现实世界里直接、莽撞、痛感十足。余秀华没想到,让自己走红的会是一首关于爱情和肉体的诗。她是一个女人,农民,脑瘫患者。当然,她更是一个健康的诗人。她有些抵触外界突如其来的对诗的热捧,还有伴随在这热捧之后的猎奇。
她会自我解嘲,“炒作之后,幸亏你们发现脑瘫不是假的”。在余秀华看来,一切的喧嚣都会过去。她依然会像自己在诗里所说的那样,“有时我是生活的一条狗,更多时,生活是我的一条狗”。而她“只有在写诗歌的时候,我才是完整的,安静的,快乐的”。
格格不入的农民
横店是湖北中部一个普通的村庄。
它在余秀华的笔下充满诗意。她描写这里的白云、午后和麻雀。但当被问到家乡对她的意义时,她丢出一句“鬼地方!”
为什么这个名字总出现在你的诗里
余秀华几乎没有停顿,“因为这个词简单、好用,就跟‘爱情’、‘春天’一样”。
因为疾病,余秀华说话有些口齿不清,面部肌肉的抽搐让她的神情显得有点夸张。但她思维非常快,话说得直而且冲。不仅是对别人,也包括对她自己。有人小心翼翼地问“你怎么看待别人总提你的身体疾病”,她立刻打断了,“脑瘫。你直接说呗,修饰什么。”
“她与这里显得格格不入。”余秀华的小姨说。在她看来,余秀华脾气古怪,思维跟别人不一样。她在村里跟谁都不怎么熟,也说不上什么话。母亲说余秀华脾气坏,爱和别人吵架,在村里没什么朋友。余秀华说过,她不甘心于命运,但她所有的抗争都落空。“我会泼妇骂街,当然我本身就是一个农妇”。她和朋友说起自己爱骂人,因为自己爱说真话。
余秀华在村里不怎么走动。这个农妇对村里人聊的家长里短毫无兴致。村里人也没有人读过她写的诗。问起来,他们笑着摇摇头,“看不懂”。余秀华办了低保,每个月60块钱。去年正月,母亲买回了20多只兔子,给余秀华照看,这些兔子成了她的宝贝,也能卖点钱。每天早起吃饭前,她先去割草,喂饱兔子。
最近,兔子一只只死去,让她感到伤心。每天上午是她的看书时间。她最喜欢的书是《悲惨世界》,喜欢那本书中的一切——语言、结构、思想,“那种对人性的刻画,真是好!”她爱读诗,房间的诗集里,几乎每页都有她随手写下的感受和批注。午后,她会花很多时间去写作,她的手不灵活,只能用一根手指敲着键盘,把诗的一字一句录进电脑里。
高中毕业,父亲在村里给她盘下一个杂货铺。母亲周金香觉得,女儿的心思根本不在杂货铺上。“她每天都在打电话,不知道跟谁打,一聊好几个小时,有人来买东西她也不搭理”。有一个月电话费花了174块钱。
除了看书,下象棋最让余秀华快乐。她象棋下得好,提起和村里人下棋,她总是笑,“他们老悔棋,就是不让我悔”。徐建国是荆州著名的棋手,在他看来余秀华的象棋水平在县级可以排到前十。他说她下棋“犀利、灵活有力量”,喜欢进攻,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势,“棋风和她文风一样”。
脑瘫者的远方
“这个身体,把我在人间驮了38年了,相依为命,相互憎恨。”她不得不接受身体的缺陷。
在诗里,她说“说出身体的残缺如牙齿说牙痛一样多余”。远方对她来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她曾经尝试过离开这个小村庄。2012年,余秀华第一次离开家乡,去温州一家为残疾人办的厂子打工。那一个月里,她仍然在写诗,晚上把诗读给工友听,“但他们都是木头”,余秀华说。只一个月,她就回了家,她说因为周围的人太世俗,父母说因为女儿手脚不利索,干活慢。
周金香说,秀华在流水线上,手在撕皮包边的时候总是使不上劲儿,怪搭档没修好边,害她撕不下来,然后跟人家吵架。领导出来调解,说给她换个搭档,她又死活不愿意,说,“这个位置好,别想把我换走!”打工没挣到钱,回家还借了100块的路费。那次的逃离对余秀华来说唯一的意义,是让横店村在她心里第一次成了遥远的“故乡”。
2014年12月19日,她在母亲的陪同下去了北京。后来她在博客里写下北京之行略记。
她提到了照顾她的诗友,感慨在人民大学的教室里朗诵自己的诗歌:这是我额外的收获,我更愿意说它是人们敞开怀抱拥抱我的一次美意。这开敞让她感激。但她依然强调自己的独立。“我希望我写出的诗歌只是余秀华的,而不是脑瘫者余秀华,或者农民余秀华的。”无法远行的日子里,余秀华的“远方”寄托于信纸和网络。
1995年,她第一次投稿给《钟祥日报》,一投即中。
母亲说她从初中就有了远方的笔友,后来又有了很多网友。很多人从外地来看她。她也会去钟祥或是荆门会网友。钟祥论坛上留下了她许多印迹,从2009年开始,她陆续发了很多诗歌帖。从最早发帖开始,她的诗就赢得了很多赞美。2009年,钟祥贴吧的网友们凑钱给她买了台电脑。在网络上结识的朋友,互相理解、支持、鼓励。说到这儿,余秀华流露出一点感伤,“时间会改变一切,不会一直是这样的。”有一阵子,余秀华把所有的诗歌群都退了,因为和别人吵架。“因为看得过重,反而更容易吵架、容易伤心。”
余秀华被网友伤害过,一次一个网友约她见面,对方远远见到她真人,就掉头走了。诗友老井回忆和余秀华的第一次见面,虽然之前知道她是个脑瘫患者,但没有细想过,见了面,老井被余秀华行动和语言的吃力“震撼”了。老井说余秀华是个苦命的天才。她率真,有些逆反心理,时常在网上得罪人。有些网友攻击她的作品,她喜欢反击,老井劝她假装看不见,她做不到。这是她自己。
余秀华说,这世上有抵达得了的远方和抵达不了的远方。如今,她仍然在那个叫横店的村庄,割草、喂兔子、下象棋、读书、写作。
女人的爱情
她没想到是一首爱情诗让她走红。
《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里面有肉体,有爱情和远方。她对这首诗并不是很满意,“那首诗里有些辞藻用得太大了,不够克制。写诗的时候不能自亲也不能自疏,要和自我保持一定距离。”
对丈夫,她似乎更不克制。丈夫被她形容为“青春给予她的一段罪恶”。她在诗里说,婚姻无药可救。结婚时,余秀华19岁,丈夫尹世平大他12岁。当时,这个四川籍男子在湖北荆门打工。余家人觉得秀华身体有残疾,能找到个对象就不错。尹世平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又是小学文化,也没什么挑的了。余秀华年轻时曾担心丈夫会跑掉。在余秀华的口中,丈夫性格火爆,斤斤计较,两人经常吵架。吵完架丈夫也离家出走过,余秀华又把他追了回来。
“现在真是后悔,干吗追他回来”余秀华说,20年,这段婚姻太累了。“爱情有个屁爱情!”有人提到这个字眼,她干脆利落地回答。余秀华的母亲周金香说,结婚后,女婿一直在荆门市做建筑工人,偶尔回家,孩子两岁后,两人就开始争吵不断。
三年前,因为在荆门讨不到工钱,他又去北京打工,每年只是过年回来。“不喝酒的时候人是很好的,喝了酒脾气稍微暴了点,话多,秀华就嫌烦。”两人闹过几次离婚,都被余秀华的父母劝阻住了。“死都不能让他们离婚。”在周金香眼中,女婿是老实巴交的人,肯吃苦,没嫌弃过女儿的身体状况。虽然喝了酒会说些难听话,但不会揭余秀华的伤疤。“日子挺好的,两人又有孩子,都是秀华自己在闹。”
尹世平从没读过余秀华的诗,也没兴趣读。他关心的并不是余秀华的精神世界。“你们这样捧她都是一时的,过去就没了。你们能不能帮她在北京找份工作啊,一个月能挣一千多块钱就行。”余秀华把对爱情的态度和渴望都放在了诗里。
“她想给他打电话,说说湖北的高粱酒,说说一个农妇醉酒之后,在大门口拉下裤子解手,说她心里的血都被尿了出来,说她拦住过路的人喊他的名字”。对于这首诗是否有所指,她说忘了。关于现实生活中她的爱情,余秀华有点躲闪。她承认,自己写的爱情诗,她在内心都是经历过了这些过程。但具体的“我不能告诉你”。
她只是说,爱情像信仰,信则有,不信则无。下辈子,希望有个人在她19或20岁时走进她心里,因为那个年纪像花一样。
女儿与母亲
提起父亲的时候,余秀华褪去了她的防备。
余秀华和父亲的感情特别深厚,她说父亲在家人中最理解她。因为出生带来的缺陷,她从6岁才学会走路,那以前,她总是在院门口爬来爬去。行走对于幼年时代的她非常困难,家人先是给她做了学步车,后来又换成拐棍,再后来终于可以摇摇晃晃地走了。
父亲对她付出的爱也比对弟弟更多。余秀华八岁才上小学,和小她两岁的弟弟一同入学。那时候上学放学,她都是在父亲的背上。课间休息,他叮嘱老师安排小伙伴轮流陪女儿上厕所。余秀华上初中时,弟弟总骑一辆28车载着姐姐上学,她身体不协调,在后座上总是坐不稳,弟弟骑起来就会特别艰难,有时候很恼火,对她不耐烦。说到这,父亲余文海形容是哭笑不得,但“感觉心酸”。
余文海回忆起余秀华在高中住校的日子,孤零零地没人照顾她。因为手脚不利索、动作慢,打饭时总抢不过别人,有时候剩饭剩菜也抢不着,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
这段话,余文海花了很久的工夫才说完整,中间几次因为哽咽停下。讲完后,他捂住脸,哭出了声。余秀华在诗中感叹父亲这么老了也是不敢生出白发的,因为他还有一个残疾的女儿,和一个刚刚成年的外孙。余秀华的儿子跟了余家的姓。村里人总说,余秀华的儿子“真有出息”。小伙子今年考上了华中科技大学,读环境工程。在家人口中,孩子内向、懂事,跟母亲的关系特别好。
余秀华的世界里,儿子是重要的感情支柱。她不止一次说,“这是我培养出来的儿子。”用余秀华的话说,他们母子之间是没大没小、无话不谈的。
余秀华的朋友圈里除了诗歌外,偶尔也记录着和儿子的互动。今年元旦,她送了儿子一条蚯蚓,儿子一头雾水。她解释,“蚯蚓是用来钓鱼的呀,送你蚯蚓,是要你去钓到一条美人鱼!”“我不知道儿子有没有读过我的诗,如果读了应该会不好意思吧。”余秀华笑了。
在诗里她这样写:我只是死皮赖脸地活着,活到父母需要我搀扶,活到儿子娶一个女孩回家。
喧嚣与沉默
余秀华不期然的就火了。
几乎是一夜之间,余秀华的一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在微信朋友圈被争相转发,她也被贴上了“脑瘫诗人”、“农民诗人”、“草根诗人”等标签。
余秀华不喜欢被强行赋予的标签。她在博客里写下这样一段话:我身份的顺序是这样的:女人、农民、诗人。这个顺序永远不会变,但如果你们在读我诗歌的时候,忘记我所有的身份,我必将尊重你。
她说自己不是天才。为什么能够写出这样的诗她也不愿意去回答。面对褒贬不一的评价,余秀华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无所谓”。她并不期待所有人的欣赏。“如果所有人都理解,那就不叫理解。我不需要在任何地方找到理解,不能为任何人而写,只能为自己写。”
但她对诗歌的感受也并不止于直觉上,也有着系统化的反思,她经常修改自己的诗。“沈浩波也许说得对,我的艺术性还不够。”她觉得行文造句需要不断地修炼和提升境界,要不断突破自己。她读诗的时候不只是凭着感觉读,她会把每首诗读透,仔细读、思考,把自己的思想放进诗的意象中。在她口中,她的诗是发自于“小我”,基于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个人体验,以及这其中生发出的想象。
海子也曾让她不能自拔,现在能够批判地看了。她曾在贴吧里贴过一组献给海子的诗,叫做《为海子而哭》,里面写道,“我遇见了披头散发的你/我遇见了口吐火焰的你”。而现在,她可以更批判地看海子的诗了,“也没有那么好,有时太抒情了”。
在余秀华爆红后的几天里,她家的院子挤满了采访的记者、摄像,出版社编辑,还有慰问的领导。面对喧嚣,她在朋友圈里说,“对诗歌而言,这样的关注度实在不应该,超过事情本身都是危险的。不管东南西北风,不管别人怎么说,姑奶奶只是写自己的诗歌,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尽量写好。呵呵,幸好这样的风刮不了多久。”
她几次对记者提到,“诗是很安静、很私人的,不该经受这样的炒作。”她对诗充满了敬意。《摇摇晃晃在人间》几乎是她对诗的告白。她说,它以赤子的姿势到来,不过是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在摇摇晃晃的人间走动的时候,它充当了一根拐杖。
“诗歌一直在清洁我,悲悯我”。
脑瘫诗人余秀华的励志故事 篇2余秀华,她的诗跟梵高一样,可以折射出生命向日葵的绚烂,也像莫奈笔下的荒原草垛,在四季不同晨昏发出耀眼的光芒。窥探其诗歌的特征,痛苦的凝视仿佛是诗歌产生的来源。也许对她来说,生命不需要回归,因为她的诗就代表生命本真。
一、痛楚特质幻化美的力变。
余秀华是左手压着右手写字,诗行里每一个字渗着疼痛。她站不稳自己的身子,总是摇摇晃晃,偏偏倚倚,她的声音挤出的不是绚烂,但是比绚烂还美的痛楚,甚至像哭泣似的悲悯。正是这样的痛楚带给她诗歌美的力变。她的目光既有对内心世界的挖掘,也有对外部世界的观望。希望通过诗的远游来结束心灵的磨难和无休无止的孤独无援。她的诗是在内心苦闷矛盾的状态下写出的。带有象征美学的特征。诗人运用各种物象来暗示内心微妙的世界。物质感的形象在她用暗示、烘托、对比、渲染和联想的渠道表现出来。在诗句的描述中,她时刻处在冬天,虽然诗歌却常把她往春天的路上带。她如云朵一样的年华随时可以倾塌,像露水一样的心只能在清风下发呆。她是一棵在若有若无的风里怔了很久的草,偶然扭动一下身躯,也是一艘漏底的船在荒芜的岸,同时拥有木性和水性。她的痛被遮盖、掩埋却又赤裸裸地暴露,像大地一样的辽阔忧伤,她在以疼痛取悦这个人世。爱在她心里就像一场雪,因为过于洁白而接近春天,所以她一次次按住心里的雪,又渴望下一场大雪。爱对她来说,不是诗歌,更像一颗提心吊胆的心,又抑或爱只是经过,像秋风在院子转了一圈,过去了。
二、荒野村落填构筑诗意背景。
余秀华诗歌有其特有的布景,江边、庭院、打谷场、果园、麦田等成了她追逐痛苦和喜悦的风景。在诗歌里爱着,她隐匿自己,又暴露自己。她生活轨迹单调贫乏,环境简陋闭塞,但是却用自然的背景创作出宏大而丰富的诗歌背景,她把思想安放在这个背景之中,潜心铸就诗歌的艺术。在有限的空间,获得心灵的自由,构筑起属于自己的天堂。
三、饱满而匮乏的诗心对立。
余秀华的创作热情和灵感丰沛,她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余秀华最可贵的一点,是她对诗歌感悟和表达是直白的,她的诗观:一切关于诗歌的表白都是多余的,它是我最深切的需要。诗人刘年曾这样评价:别人都穿戴整齐、涂着脂粉、喷着香水,白纸黑字,闻不出一点汗味,唯独她烟熏火燎、泥沙俱下,字与字之间,还有明显的血迹。她的诗不粉饰、不雕琢,不是充满华丽装饰的客厅,质朴得像子夜的村庄那照着想象的微弱的灯火,她的诗代表了新诗的发展,也是一个时代稀缺的物品。
刘年
刘年,本名刘代福,1974年12月出生于湘西永顺,诗人。
永顺一中毕业后,考入湖南省建材工业学校读机械制造专业。曾在佛山高明明城水泥厂做过3年的机械维修工。1997年返乡后曾做过各种小贩,卖木柴、卖棉花、卖谷种、卖烟叶、卖药材等。2010开始从事文学工作,先后在《边疆文学》《诗刊》担任编辑。现在从事诗歌散文的创作与教学工作。
中文名:刘年
别名:刘代福(本名)
国籍:中国
出生地:湘西永顺
出生日期:1974年
职业:文学作家,教师
毕业院校:湖南省建材工业学校
主要成就:2013年获人民文学诗歌奖
曾推出诗人余秀华
代表作品:诗集《为何生命苍凉如水》《行吟者》,散文集《独坐菩萨岩》
主要作品
诗集《为何生命苍凉如水》
诗集《行吟者》
散文集《独坐菩萨岩》
《走过稻城是苍凉》
获奖记录
2013年10月,荣获2013年度诗探索·华文青年诗人奖
2013年12月,组诗《虚构》荣获人民文学杂志社2013年度茅台杯人民文学奖
2015年5月,组诗《沉默》被评为第四届(2013-2014年)汉语诗歌双年十佳
2016年1月,荣获2015年度“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优秀编辑(记者)奖”
2016年10月,诗集《为何生命苍凉如水》荣获第二届“中国·兴隆刘章诗歌奖”
2016年11月,组诗《旷野》荣获2016年度储吉旺文学奖·优秀作品奖
2017年4月,组诗《虚构》荣获第二届大观文学奖
2017年11月,十首诗歌荣获第三届中国“刘伯温诗歌奖”
2018年4月,作品《南沙》(组诗)在“致敬海南!——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诗歌征集活动”中获一等奖
2018年8月,诗歌作品《天边的北斗七星,是永远拉不直的问号》荣获第三届《朔方》(2016-2017)文学奖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表白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