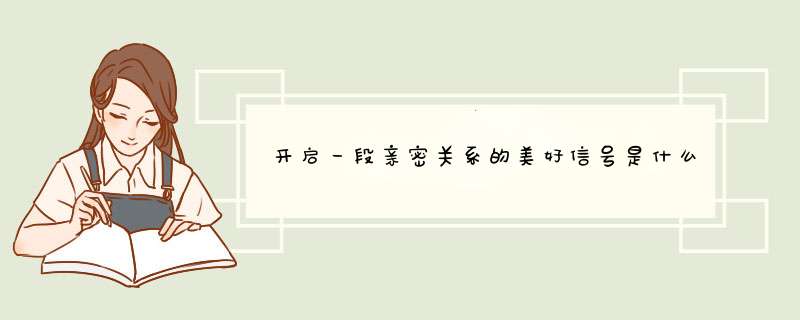
开启一段亲密关系的美好信号是表白成功。
表白,或称告白,意为向他人表示自己的想法或心意,特指表达爱意,又称示爱,在这种情况下通常被认为是建立恋爱关系的方式。
表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如当面表达,写情书,打电话,网络即时通讯,送礼物如送花等。这些都算是比较传统的表白,更有甚者为了追求创意,而创造出很多另类的表白方法。
引证解释:
1表现,显示。
唐 裴铏《孙恪》:“阴阳之盛衰,魂魄之交战,在体而微有失位,莫不表白於气色。”
明 郎瑛《七修类稿·诗文一·各文之始》:“表者,白也。以情旨表白于外, 汉 则散文, 唐 以后用四六矣。”
2表述,说明。
元 范子安《竹叶舟》第三折:“ 陈季卿云:‘诗写就了也,待我表白一徧,与你听咱。’”
明 冯梦龙 《东周列国志》第五十七回:“此事且搁过一边,表白在后。”
《儒林外史》第一回:“可笑近来文人学士,说着 王冕,都称他做王参军 ,究竟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所以表白一番。”
叶圣陶《倪焕之》四:“他于是动手写文章,表白自己对于教育的意见。”
3犹说白。
郭沫若《<孔雀胆>后记》:“因为 阿盖 的念诗,如要配上音乐, 车力特穆尔的表白会被搅乱,不配上音乐吧,白念是难得讨好的。”
关于《儒林外史》1-4章中提出问题并作答?
作者在楔子中塑造了元末诗人王冕的形象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并作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标准。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经史等大学问无不精通;而又安于贫贱,以卖画为生,不趋炎附势。作者通过他的嘴,抨击了科举制度。在作者看来,文士们只有像王冕那样讲求“文行出处”,才能免于“功名富贵”的牢笼,堪称“品地最上一层”。
全书一开始就通过周进、范进中举前后的悲喜剧,揭示了科举制度是怎样腐蚀着文士的心灵,以及士子们热衷科举不过是为了爬上统治阶级地位,升官发财,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一群考取科名的读书人,他们出仕则为贪官污吏,居乡则为土豪劣绅,从而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政治的腐败。
主要特点:
1)该书一个显著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
2)成功的运用了写实主义的讽刺艺术;
3) 喜剧性与悲剧性的高度和谐统一:
4) 将生活之丑转化为艺术之美;
5)小说描摹出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景观,从根本上揭示了封建制度对人才的摧毁。
人物形象

书中重点描绘了一群热衷于功名富贵的儒林丑类,从而揭露和讽刺了科举制度的腐朽和整个封建道德的虚伪。腐儒的典型——周进、范进;贪官污吏的典型——汤奉、王惠;八股迷的典型——马静、鲁编修。正面典型王冕、杜少卿。周进的哭,范进的笑。王玉辉的笑而后哭,可以看出作者笔锋所指不是某个人,而是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因此,作者在对人物进行褒贬时,他的讽刺总是紧密地围绕着事物的本质问题而显示其分寸的。不同的人物典型体现出了不同的思想认识价值。
周进
周进,《儒林外史》的重要人物。作品将其设定为一个皓首穷经、迷信经典、沉溺于科举难以自拔的人。周进生活穷愁潦倒,不得不忍受着士林人物的羞辱和市井小民的轻蔑。但始终坚信科举是自己唯一的救命稻草。
刚出场时,周进已经六十多岁,依然是个老童生。在汶上县做了三年西席,学生顾小舍人都进学成了秀才,他再无资格继续教下去,沦落到薛家集观音庵私塾中来坐馆糊口,饱受秀才梅玖和举人王进的嘲弄和冷遇。
不久,周进丢了饭碗,只好替一伙商人当帐房。可以说,已到了科场梦醒之时。然而,当他进省城路过贡院的时候,他多年的心结却又被触动了。但他是童生,他是不能进入贡院的,看门人的鞭子将他打了出来。想象周进无助地站在贡院冷冷的门外,世界对他而言真的是一无所有了。
当他恳求别人带他参观贡院时,大半生追求功名富贵却求之不得的辛酸悲苦,以及所忍受的侮辱欺凌一下子倾泻出来,周进的人生也一举进入高潮:周进一进了号,见两块号板摆的齐齐整整,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不知道是悲从中来的发泄,还是灵光乍现的奋力一搏,周进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他苏醒后满地打滚,放声大哭。几个商人得知原委,答应每人拿出几十两银子,让他纳监进场。周进道:“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爬到地下就磕了几个头。众人还下礼去。金有余也称谢了众人。又吃了几碗茶,周进再不哭了,同众人说说笑笑回到行里。几个商人帮助周进捐了个监生。
不久,周进凭着监生的资格竟考中了举人。顷刻之间,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是朋友的也来认做朋友,连他教过书的学堂居然也供奉起了“周太爷”的“长生牌”。过了几年,他又中了进士,升为御史,被指派为广东学道。在广州,周进发现了范进。为了照顾这个54岁的老童生,他把范进的卷子反复看了三遍,终于发现那是一字一珠的天地间最好的文章,于是将范进取为秀才。
周进角色评价:
这一节是《儒林外史》中名篇,足以和范进中举媲美。作者以其神来之笔,描绘了士人被科举制拨弄地神魂颠倒的可悲可怜可笑之处。由于前面用周进所受的种种屈辱做铺垫,揭示了其久不得志的心境,醉心功名而功名无望,撞板一段就显得水到渠成,毫不突兀。实际上,周进和紧接着出场的范进两人一个悲伤地要寻死,一个高兴地发了疯的细节,都寄寓了无限深意。
作者揭示出科举制弱化了知识分子的生存能力,使他们深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神童诗》)的观念毒害。中举是他们唯一的生活目标,八股是他们唯一的生活技能。科场若不如意,就再无其它谋生本领。周进宁可撞板,因为他深知:除了科举,自己无法自食其力。
作者在讥讽其丑态的同时,也对人物寄寓了无限的同情。因为其用意不止于暴露科场和官场人物的污秽,而是着意批判形成他们种种性格的社会根源,极其尖锐地指明科举对于人性的异化作用。
自此,周进的人生陡然发生了喜剧性变化。如果说从前沉沦落魄受尽冷眼,此后可谓春风得意一帆风顺。中举人,中进士,做御史,做学道,一路升到国子监司业。
吴敬梓当然不是要写一个知识改变命运的传奇故事,实际上,周进的喜剧性结局大大加强了讽刺力量。这种悲喜交融的美学风格,显示了滑稽的现实背后隐藏着的悲剧性内蕴,瞬间的可笑蕴含着永恒的悲哀。
作者通过周进发迹前后士人群体对他的态度变化,批判了整个士人阶层和市民社会。在写主角的同时,也描绘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态。士人之间的相处之道,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惺惺相惜,或者同命相怜。相反,他们之间完全是一种赤裸裸的食物链关系。一旦科场失意,得到的不是同情,而是整个阶层的鄙视和唾弃。一旦跃过龙门,跻身上流社会,便发现整个阶层全都笑脸相迎。吴敬梓本人对此即有刻骨铭心的感受。
发迹后,从前瞧不起周进的人态度判若两人。梅玖冒称是他的学生;他在村塾中写下的对联,被恭恭敬敬地揭下来裱好;辞退了他的薛家集也供奉起他的“长生禄位”。周进熟识人物态度的转变,除了写尽世态人情之外,更表现了科举制度对各阶层人物的间接影响,是造成污浊世风的根源。
周进前半生生活在社会底层,地位卑下,事事仰人鼻息,形成逆来顺受的性格。暮年飞黄腾达后,同情提携同样出身下层、同样屡试不第的范进,表明周进秉性忠厚,迂而不恶。写出了他性格的复杂面。在这个醉心于科举,而心术并未大坏的读书人身上,更可见出科举制对士子灵魂的侵蚀之深。
匡超人原来是一个比较勤恳淳朴的农家子弟,先在柴行记账,后来又以测字为生,在杭州城隍山遇到了马纯上,马二劝他读书制艺,应试科举才是“荣宗耀祖”,“显亲扬名”的唯一途径,并且资助他回乡攻读。接着他在家乡又遇到了乐清县知县李本瑛,受到他的奖掖提携,先后考取了案取、秀才。从此以后,匡超人的气质就开始发生了变化,势利嘴脸才逐步暴露,甚至只承认李本瑛是他的老师,却不承认学里的老师!并公然对门斗发脾气:“我只认得我的老师!他这教官我见他去做甚么?”其变化之大真是快速之至。但他又是何尝真心感激和爱戴李本瑛?只不过因为李本瑛是他的父母官,是他向上爬的靠山。后来李本瑛被错参了坏事,他竟然掉头不顾,并不过问,全不介意远走杭州。及至杭州途中,结识了景兰江,听到这个杭州“名士”的谈吐,一方面固然“不胜骇然”一方面也学会了欺世盗名的诀窍,对他的恩人马二也看不起了。在杭州又与潘三混在一起,冒名替考,巧取豪夺,干了不少坏事,完全成了这个恶棍的帮凶。
马二先生人物的性格的情与礼的矛盾性主要通过“马二先生游西湖”这一段来展现的。吴敬梓一会儿写他看女人,一会儿又写他怕看女人,用笔散漫,似乎游离于主题之外。其实,正是这些“闲笔”,触到了马二先生最隐秘的神经,揭示了他潜意识与显意识之间的冲突与裂痕。乍看西湖边,马二先生就看到了那“一船一船乡下妇女”,观察之细,连她们的发型、衣着甚至脸上的疤痕都没放过。行仅里许,他有“看见西湖沿上柳荫下系着两只船,那船上女客在那里换衣裳。”但这些“并不在意”,并未诱使他想入非非。这说明上述两番看女人,不过是其感官对外界刺激的本能反应,尚停留在非理性、不自觉的潜意识领域。写当女人们走到他跟前时,“非理勿视”的理性意识迅速发挥作用,“他赶紧低下头走了过去,不曾仰视”。通过上述的分析可知,马二先生来到西湖所面对的是一个物质世界,这个世界以“食和色”为代表的两种事物冲击着他的意识使他在“持念日久的文章德业”和“西湖风情物态所唤起的本能”两种意识的碰撞中显得窘迫不已。
王玉辉他是个六十多岁的“迂拙的人”又做了“三十多年的秀才”但依然功名不就。家中既无恒产,子女又多,生活极端“清贫”,可是却立定志向,要撰写礼书、字书、乡约,以“嘉惠来学”。他解释自己所著礼书是讲“事亲之礼,敬长之礼”乡约书是“添些仪制,劝醒愚民”。由此可见,他的头脑仍被封建理想所束缚,而在他自己看来这却是“劝民”的善举。更可悲的是当他的“三姑娘”要绝食殉夫时,他不仅不劝阻,反而诚心诚意的鼓励女儿绝食殉夫,认为这是“青史留名的好事”。但王玉辉在做出这个决定时,人格是处于极度分裂的状态下,他一方面为良知所左右,结果女儿真的殉夫后,他的精神又落入了痛苦的深渊。使他在“烈女入祠”的当儿“转觉心伤”。
严监生因为临终时仍在可惜灯盏中点着两茎灯草一直伸着两根指头不肯断气而成为中国小说史上悭吝人物的典型
太守王惠敲诈勒索,敛集财富,汤镇台则注重立德修身;周进的痛不欲生、范进的喜极而狂和马二先生的冬烘迂腐;牛浦郎的招摇撞骗不同于匡超人的虚骄做作;同是风流不羁的大家公子,杜少卿的豪放纯真,不谙世故有别于杜慎卿的“雅中有俗”的外延下的精明,同是兄弟,严贡生挖空心思谋夺哥哥家产,其他方面的品行也很恶劣,而余大先生余二先生则兄弟情谊敦厚,余二先生为哥哥消除了一桩官司,而余大选了徽州府学训导,也要弟弟随同上任。说:“我们老兄弟相聚得一日是一日。
参考资料:
王冕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作者据此进行了改编。王冕在小说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整个小说的人物塑造上,他奠定了作者理想人物的基本特点,正如回目所说“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王冕作为一个士人作为一个“名流”,在他身上体现着中国士人的精神。
王冕(1287年~1359年),字元章,号煮石山农,亦号食中翁、梅花屋主等,浙江省绍兴市诸暨枫桥人,元朝著名画家、诗人、篆刻家。他出身贫寒,幼年替人放牛,靠自学成才。
王冕性格孤傲,鄙视权贵,诗作多同情人民苦难、谴责豪门权贵、轻视功名利禄、描写田园隐逸生活之作。有《竹斋集》3卷,续集2卷。一生爱好梅花,种梅、咏梅,又攻画梅。所画梅花花密枝繁,生意盎然,劲健有力,对后世影响较大。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时代背景上,清朝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三代,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社会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封建社会的腐朽,统治者镇压武装起义的同时,采用大兴文字狱,考八股、开科举,提倡理学以统治思想等方法以牢笼士人。
吴敬梓反对八股文、科举制,憎恶士子们醉心制艺,热衷功名利禄的习尚。他把这些观点反映在《儒林外史》里,以讽刺的手法,对丑恶的事物进行深刻的揭露。
《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出身望族。曾祖父和祖父两代人“科第仕宦多显者”(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共有六名进士,其中榜眼、探花各一名。而其父吴霖起是康熙年间的拔贡。吴敬梓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考取秀才,同年父亲病逝。
由于不善于治理生计,他过着挥霍浪子生活。雍正七年(1729年),他应科举时,被斥责为“文章大好人大怪”,遭到侮辱。后愤懑离开故土,靠卖文和朋友接济为生。乾隆元年(1736年),吴敬梓参加博学鸿词科预试。
安徽巡抚赵国麟正式荐举他入京廷试,但他“坚以疾笃辞”(顾云《吴敬梓传》),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至晚年,常处于饥寒交迫。这样的个人经历,令他本人对考八股、开科举等利弊感受尤深。
书名上,“儒林”一词源出《史记》“儒林列传”。是“儒者之林”,指学术界等。 [6] 国史列传,自然是“正史”,作者专门以“外史”为书名,正是为了作区别,正如作者的挚友程晋芳在《怀人诗》中所揭示的:“外史记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史传。”
则是作一正统记史之外的的儒林传记,并且作者有意把书中故事假托发生在明代,以类“正史”,而实际上描绘的却是清代广泛的社会生活,反映了作者同时代的文人在科举制度毒害下的厄运。
-王冕
-儒林外史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表白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