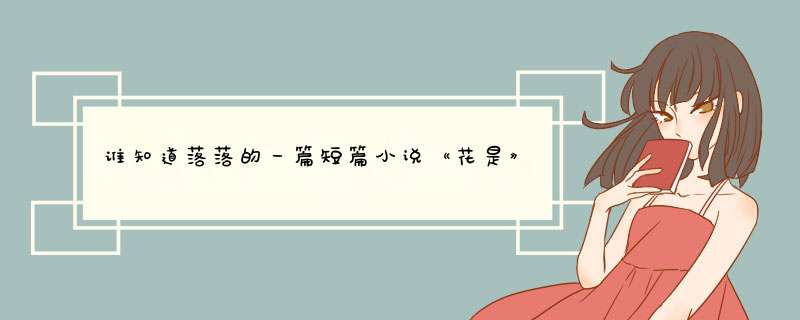
花是
——By 落落
改编自绿川幸《花之迹》
——我把认识你的过程画成天台上的老鼠和它养的一盆芝兰。星光灭绝的晚上它和它彼此以豆豆眼对视,这样的夜里瞬时浪漫无边,凉意不动拂过你的脚趾,眷顾着你饱满的梦和我谨慎的脸。
菊池醒来的时候又看见了桌角的花朵,端详一阵,片刻里阳光变得猛烈,世界起了连绵羞涩的绿意。菊池把鼻子凑上前,伪装它是一颗春天里的蘑菇。嗅到森林静静,浮尘结伴落下溅起。凌子前天还分析说那朵花一定是个腼腆的男生为了表白而画的,今天又改口讲或许是上夜校的学生随手涂的。菊池就笑她的前言不搭后语。把当初凌子用来嘲笑自己所谓的“桃花运”一个个反击回去……“桃花运”,那样浓烈的香,本就眷养在深宫美院,和自己的庭院隔得很远很远。
尽管如此,当菊池那天早上在自己的桌面上发现了留言般的简笔画——一朵孤寂而凌乱的花,晾在一季空旷里。它不动声色地望向菊池,背景是这个好端端暖洋洋的日子——她的思绪就刹那被拉得很细很长,绷着微微的情绪。菊池念着凌子的话,应该是读夜校恰恰坐在自己座位上的人画的没错了。她伸手去抚摩这小小的记号,大片大片的空白班驳在心底:“是什么样的人?”班级里一张张充沛的面孔填塞着空间,没有相似的痕迹。
一天天过去,花变得越来越多。常常只是一个夜晚而已,它们就肆无忌惮地延续。这是多么不可名状的夜晚,菊池愣愣地想,就在自己睡着的时候,从无到有,小心拾掇自己未来的繁华盛世。
那个真正云淡风轻的日子,她忍不住,在空余的地方临摹了一朵相同的花朵。明了的线条和诉诸不清的内核,汩汩。时光在枝头骄傲地来回,菊池看着桌面上愈加盘踞了大半个寥落的世纪的涂鸦,不悲伤的白天,有流云写下匆匆的长短句。但当潮湿的夜晚结束,太阳直直地指向自己的课桌,那里连绵的花群和半真半假的春天,都已经被人擦得一干二干净。菊池的背影僵硬,像吃了难堪的败仗,有了羞辱——只有自己添加的丑陋的花,还在勉强维持着荒凉的笑脸。“是我的画蛇添足,叫他讨厌了罢?”菊池心里爬出怕黑的叹息。
放学后和凌子在车站分手,却突然想起有东西落在教室里。菊池啪嗒啪嗒返身跑回去,啪嗒啪嗒的声音甩在幽暗的走廊,填出让人感叹的背景。背景里有他削瘦敏感的侧脸,就站在自己的座位前,同那朵生硬的花打着照面。他发现了菊池,转过头来看向自己。那清秀的眼和温和的头发,一层层向自己涌来,于是海龟和月亮都不再说话,它们安静地依偎在海岸线,听一场不绝的喧嚣。
——它们长久地爱慕着,悄然不语,我的阳台上有了袖珍的彩虹,短短的桥只为了缩小一点称不上差距的差距。那些美丽的事,那些配不上的美丽的语言。
他在菊池弯下身来拿出书本的时候问她:“是你的桌子?”得到了女孩肯定而疑惑的回答后歉意地笑了:“抱歉之前把你的桌子弄脏了,晚上读书时我不自觉地就涂了几笔。昨天看见你的画才发现这不是我的课桌……昨天才擦干净,真是抱歉。”“没关系,你画的花,我很喜欢……嗯,我叫菊池。”正视着他似笑非笑的眼睛和敏感的鼻子,很好看的。都是很好看的。“谢谢。叫我仓田好了。”
菊池知道自己正在一条巨大的船上,无声无息地迎来落日绽放的伤口和人鱼华丽的晚装。菊池想得紧张,弓身对他说“再见”匆匆跑了出去——那些美丽的花朵就随着贵族**的呜咽从窗口落入海里,它们分离或是团聚,须臾的疯狂和漫长的寂寞,在浪起浪伏间来不及想。
“哎呀,原来是仓田君啊。”凌子滔滔不绝地说着这位和自己国中同班的旧友,菊池看见她昂扬的眉毛,想起昨天睡前期待的一场好梦,梦里开一生一世的花朵,直到再堆不上弯起腰身,世界那样充裕,眼睛都被涨疼。
她倾听着仓田完全不同自己棉布一样平和的初中时光。那一度在颠峰疲倦的微笑。仓田是那种人好,长得好,还能画在国际上得奖的习作的美术天才少年。虽然菊池才刚刚尴尬地听闻,这些分别很久的记忆,在同城中却千里万里地追随而来,终于挨到了脚边,只吐得出精疲力尽的气:“很有才能的,师从一名女画家时却传出不不好的绯闻,搞得他再也画不出画了。”
胸口嘎嘎作响。那些故事出乎意料的轰华绚烂。完全不似那天傍晚他的脸,沉在井中,夜色阑珊,没有和悲伤的瓜葛。菊池皱着疼痛的眉头想起他浅色的眼神,他抚摩着自己的那朵花的手,他发现了自己抬头望过来,望过来的时候天空默默裂开。
还是放学的时候,菊池找凌子找到学校后的保管仓库里,她一下下地喊着,声音回荡在灰扑扑的仓库,死水微谰。却猛地听见头顶有动静,吓得大叫,却听见一把恍惚的声音:“是菊池?……我是仓田。”
菊池抬头看向仓库顶棚下被关闭的阁楼,她却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一片封闭的空间。她向声音的位置问:“你怎么会,在这里?”仓田温和的声音因为距离的关系却突然变得明显,他说自己经常溜课到这里来,“这里很暗,叫我觉得安全”。仓田说自己正在工作呢,菊池弄不明白了,她期待地问我能爬上来看看么?仓田远远地笑了,菊池察觉——“抱歉不行,这里都是垃圾,很乱”——他笑得和那天一样礼貌而好看吧。
终于还是告别说了声再见,女孩返身离开,看一眼被幽闭的阁楼,真的什么也看不清楚。
菊池想,仓田。菊池想,仓田仓田……
——走过繁冗的下午,就是疲倦的黄昏。一世纪一世纪的星辰正在跃跃欲试,却永远参不透这两者之间的默契。在远离海水的干涸的阳台,汹涌的是断续的情愫。
他的样子从各种说法中逐渐清晰,是一头一无所有了被逼迫到走头无路的动物,没有了锐利的犄角只有一场不紧不慢的笑。菊池凝视住桌角上那仅存的花,这个一相情愿的约定,承不了几世几载的欢喜。她想起仓田,她不再想。
再次的相逢有一片疾云奕奕的天,所有的风都努力地搜刮着草间微妙的秘密。
菊池急匆匆地穿过小城后的荒原,天很凉,凉了就不愿意停下脚步来看这世上仅剩的美好,青春做酿。
仓田坐在一处废弃的台阶上,一边吃面包一边喂着大胆的小鸟。他冲她打招呼:“哎。”菊池的脚步停下,坐到他身边。看他把面包吃完,仓田有时侧过脸来问她话,她就如实地回答。然后都沉默着,注视着日子尖利地骈阗而过,黑暗在其中大声呼吸。菊池拢住自己被吹起的裙子,眼神示意他手里大包的颜料:“要去画画?”
“不是。”他低头扫了一眼那些绚烂的商标,“我只是要把这些颜料全部挤出来,扔掉。”
“哎?”菊池看着他抓住包袋的敏锐苍白的手指,好象那里会突然开出莫测的云霞。
“就好比我喜欢涂花一般的形状。”他拍拍身上的面包屑站起身,菊池也赶忙跟着爬起来。两人往前走,前面墨色的地平线。他的声音漂浮于空气之上云霭边缘,被风重新勾勒的脆弱的好看的脸庞。仓田说他自己总会察觉有些东西溅落在眼前,它们渺小飞快地坠地,随后沿着中心向四处逃散。
“我总按捺不住想要把它们用笔捕捉下来,最后却发现,我画的其实是朵花。”
仓田把一整袋的颜料从左手换到右手,菊池也跟着从他右边站到左边。左脸看上去的仓田,是悲伤的。不是另一边那样填满着隔膜的平静的瞬间,轻易地停止自己的故事。菊池把心里的石头一个个摆开,长长的难看的一列——
“他们说仓田从前是那样叫人惊讶的绘画神童,但有了后来。”
“他们每次说仓田总是会说到‘一蹶不振’和‘流于平庸’。”
“他们说仓田曾经有满心的画,但现在却再也不能表达了,即使他尝试画再多再多也不能表达。”
这处曾经坍塌的山谷,被默许了告别生命的境遇。菊池不发一语,看见头顶像海水一样流动的云,悄悄地不可抗拒地就将仓田带往灰暗的寂地。
女孩一把抓住他的衣袖:“我要怎样……才能把仓田,领回来呢?”
他的眼睛终于刹那变得透明,回望着那柔弱的头发和纤细的脖颈,这一切的小心翼翼。你可以看见你的心不堪一击,到头来它为之奋斗的不过是透明的泪水而已。
——被越过的青春,被打碎的瓶子,被挥散的混沌,被释放的梦魇,我想那些都与我们无关。就像它每天为她衔来洼处的水,她慢慢为它开一朵花。很久以前的认识,延误到现在。
“你其实知道我的事……”仓田凝视着被菊池拽紧而皱起的衣角。他的心本来就在高处,那里云瀑无声,日日掠过孤傲的虹。只是这样无声的寂寞,终于遭受了几年前的打击。可以听见一切轰然倒塌的声音,却因为心在高处而叫魂魄不能自由,“你无法想象让深信自己才能的人失望居然是那么可怕的事情。可我不画画的话,就好象死去了一样。”
别人是无法知道的,无法知道那些必须取之不尽的才华一夜之间就宛如梦幻。那些日夜尾行的责难和逼问,那些不折不挠的期盼和等待,那些暗中滋长的谣言和传说,那些那些,那些这些,这些这些……全部。
“但是,仓田的画,才是真正的花朵。”菊池扬起的脸,横横地拦截,“那些溅落逃离的‘它们’,就是你的心。”
她目送着男孩的离开,他摆摆手笑着说,“再见”,他因为手里大包的颜料而微弯着身,看起来力不从心而惶恐。菊池这样目送着仓田。她转过身往家里跑去,路上开始下煽情的雨,不滂沱也不瓢泼,似有似无的迷离般的雨,很容易地把人打湿。
断然的时光蜿蜒向前,经过我们成群结队的寂寞和悲伤,那些虽然造作却真实的花朵,从涨痛的心源源不断地开放。结果春天居然变得寒冷,那些无从消化的情感,猎猎地在寒风下破土,永远永远不见了蝴蝶。
菊池更深地在课上睡觉,她把头埋向那个刻骨铭心的季节,那里有一朵自己的心。仓田再无法画画的那天起,那唯一与世界沟通的桥就蒸发成了彩虹。菊池揣摩着他心里的欢喜和伤感,他理应享受的明媚和清澈,他那被干净的脸所埋葬的痛苦——
“它们溅落到我眼前,飞快地坠地,然后迅速地逃开。我尝试用笔去捕捉那慌乱的轨迹,最后却发现,我画下的是一朵花。”
“只有把这些颜料从我心里挤出来,扔在这个世界上,那些充溢在我身体里的错觉,才有被消化的舒畅……我知道你听不懂呢。”
菊池把头紧紧地埋在臂弯里,好象拥抱一面已经破碎的月亮。那个无从得知的世界,是仓田为自己留下的最后的黑暗和空白。它遥远的遥远的悬挂着,决然的决然的坠毁。那些好看的眼和好看的脸,那些好看的笑里面难以捉摸的创伤。
“所以他只能涂鸦,那些花一样的画。不然心里的情绪无从排遣,就会粉碎……我什么也帮不了……什么也不能做……但起码惟一的——”
宁静的温暖的夜晚,灯光无暇。仓田站在桌前,那幅已经淡却的涂鸦,和那行纤细的字摇摇欲坠:“我喜欢你。”
穿越时空而来的叫人惶恐的花朵,横亘青春而至的汹涌湍急的河流,泻出匣子而临的漫无边际的云海,向着那一无所有的透明的心脏。
无数简笔的花,从空中溅落,折断在他的胛骨和眉间,却依然,依然顽强地把他美好地覆盖。
“我喜欢你。”
——念忘,今心亡心。
遭遇,曹行禺行。
菊池在走廊上撞见了仓田。她冲他害羞而美丽地笑。他依然是这样纤细明净的人,眼弯弯的时候像某个明星。跟着太阳斜下,她和他的影子有了些微的重叠,彼此交汇的阴影,剩余的大片暗黄。
“……把花和告白擦掉的人是你吗?”菊池的手不自觉地交握着。
“嗯,我把他们藏起来了。”他低下头看着眼前善良的女孩,那张青春平和的脸,“因为我要带他们去别的地方。”仓田顿了顿,那样叫阴影都无从着落的脸,菊池半映着日光,有她柔和的曲线:“我们全家要搬到另一个城市去了,新的生活。”
菊池难以释怀地对视着他,看他继续说:“今天晚上就会离开。我总有一天会回来见你的。”这种距离,菊池突地想到同样的那天傍晚,他漠漠地礼貌地对自己第一次说话……而现在,那里有了更深的温度,那些温度饱满地填着他的每根细小的血管。
“我可以,摸摸你的脸么……”这话却由他率先说出口,菊池惊讶地抬起下巴。
你的味道和我的呼吸,那个被我们涉足的沙漠,是最强烈的最强烈最强烈的温度。它们根植在我们的心脏,总有一天会放出同样强烈的光,放逐了所有不解的潮湿和灰暗。由我们的拥抱里,繁衍出无可比拟的喜欢来。
我喜欢。一如我现在真实地拥抱着你不松开不会松开。
仓田的消失,带走了自己的花一样的轨迹和告别,课桌也暂停了多余的故事。菊池依然在教室里参仰着自己的森林,那里浮尘静静。或许有一天,她想了,那些几笔潦潦的花会蔓延到自己的手臂,经过她的手指,在指尖上迎风,或许有一天,那些剔透的花和清澈的理由。而现在,就依然过得每一天都像依附在湿衣服上的肥皂泡沫,在阳光的催化下变成细微的固体漂浮或坠地。
当菊池想起了仓田临走前说的话,她在傍晚穿过已经空旷沉默的教学楼,把窥视的斜阳关在了仓库的大门以外。
“我,算是在工作吧。这里都是垃圾,很乱……你上来的话会叫我觉得失礼。”
菊池想到他再也无从触摸的背,搬来工作梯,移开阁楼的门探上身去。一片漆黑的,真的一片漆黑。还有那除不去的尘埃的呛味,幸好自己带了节能灯。她支撑起胳膊爬上去,看见地上仅有的大堆空空颜料管。
“我只要把这些颜料全都挤出来,然后扔掉。”他好看地笑。
“哪里去了……”菊池寻思着抬起头。
——“有东西落下来,从中心向外扩散,飞快地逃开,当把它们涂下来,却发现那是一朵花。我把那送给你看,那花非花,画非画的东西。”
——阁楼的天顶,全是巨大繁盛的花朵,拥挤在她的视界里,是静寂而高亢的尖鸣——盛大的颜色,明媚的形,轻言絮语的布局,无可替代的惊喜。这旁人的世界无法享用的华丽,它们曾经那么凄婉地盘踞在一个人的心里,现在被人用身体的全部细胞和毛发,全部骨骼和脉络,轻轻地炸成仓促的穹庐,底下漫过诗一样的寂寞。
——“可我不画画的话,就好象死了一样。”
菊池看着整个天顶上都是仓田心里的花,言语无处声张。少年的脸清风扬起,他消失在了最后。于是神灵补偿了这个用花朵来织就的天,这个刻骨悲伤刻骨绚丽的花之天。
一笔,一就,一色,一就,一春,一就,一心,一就,一物,一就,一时,一就,一目,一就。灵魂促就。
菊池慢慢地躺倒身子,柔韧地像没有出处的羽毛。最后她看到地面上一朵用笔潦潦涂下的花朵,它长着稚嫩的脸,和溯流而上的时光——那天他在自己的课桌上画下了心里的轨迹,那天后的那些花。
书里讲颧骨是为最美丽的河流准备的丘陵。现在它们爬过两行悱恻的泪水粘稠而悲伤。你看我的世界,那么悲伤。好看的悲伤。挥别了你内心的烂漫春色和堂前谢燕,连绵流淌,不绝地流淌。
你喊我的名字“菊池”、“菊池菊池”,喊得那里花色缤纷。
而菊花,谢在那个蓦然的冬天。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表白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