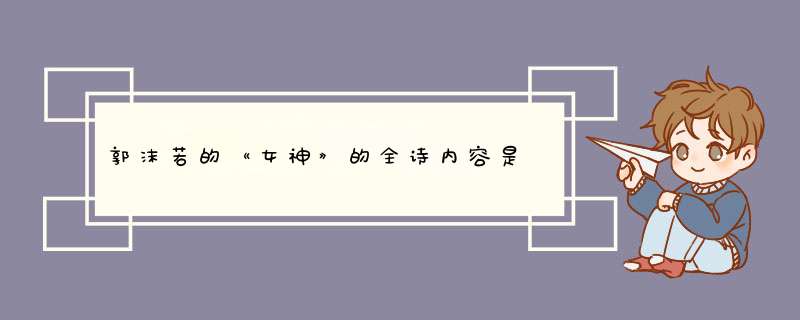
郭沫若的《女神》是一本诗集 《女神》出版于1921年8月,是中国的第一部具有真正现代意义的新诗集。收集了《女神之再生》、《凤凰涅盘》、《天狗》、《晨安》、《炉中煤》、《匪徒颂》等代表性诗篇。
在诗歌形式上,突破了旧格套的束缚,创造了雄浑奔放的自由诗体,为“五四”以后自由诗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天地,成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也是郭沫若代表作。今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本,后又重印多次。
扩展资料
《女神之再生》是诗集《女神》的开篇诗剧,以其浪漫主义雄风独步文坛,这部诗集代表了那个狂飙突进的文艺振兴时代的激情和浪漫的最强音。这里节选的是“女神”的歌吟,象征着建设一个美丽新中国的理想和欲望。
诗人假借女娲补天的神话传说开篇,表达了美丽的向往和对于盛世的怀念。在女娲开拓的优美世界中,音乐响彻、花开月圆,生命自由自在,循环往复。
作品通过英雄人物聂政、聂嫈姐弟的抗暴锄恶,表现了他们对黑暗社会的痛恨和见义勇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不愿久偷生,但愿轰烈死。愿将一己命,救彼苍生起!”同时也抒写了他们对新生活的热望与追求:“迸发成自由之花,开遍中华”!
-女神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坛上风格较为独特,同时具有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的优秀作家。他出生于湘西成名于都市,在其2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始终探索着人性的奥秘。他一生的小说创作,大致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对人性美的赞颂和讴歌,这主要是他的“湘西小说”创作;二是对摧残、破坏人性美的种种阴暗面或罪恶势力的揭露和鞭挞,这主要体现在其都市小说上。因此,沈从文便有两套笔墨:一套用来描绘湘西乡土世界,展示乡村生命形式;一套用来描绘都市世界,展示都市生命形式。而对于这两个具有对立与对照性质的生命世界,沈从文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情感取向。对湘西乡土世界及其所代表的生命形式,他满怀热忱,表现出一个在精神归宿上始终向着“乡下人”的知识分子对湘西乡土的天然亲近感与认同感;而对文明化的都市世界,沈从文则始终怀有一种无形摆脱的敌对情绪与潜在的恐慌感,代表一个有湘西“乡下人”向城市“边缘人”转化的知识分子寻找精神归属的陌生感与荒诞感。无论是叙写人性美还是人性扭曲,沈从文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一致的,那就是痛惜人性的失落,呼唤人性的复归,而在他构筑的两个鲜明对立的世界表现了自己对人性问题的独特思考。这两个世界的塑造都是独特而成功的,其原因就在于沈从文没有把眼光仅仅局限在湘西,单纯地在世外桃源中描绘人性的善与美,而是从湘西走向现代都市,以都市世界的参照,以一个现代文人的眼光返顾湘西的文化体系和趋向,从而使他获取了超越于自身乡土文化锻造的人格模式,同时又将批判的锋芒指向都市文化的形态。
因此,沈从文这种将原始的乡野文明与新近生成的都市文明互渗互参的描写姿态,为其都市小说提供了比较独特的都市文学视角和文化意蕴。在“都市批判”中,茅盾用社会科学家的理性精神剖析了中国都市生活中各个经济阶层的命运沉浮,以政治的视角对都市进行全景式的反映,试图以“革命”为改造的方式,重建理想的都市人生和积极的都市生活;老舍从文化的的视角审视古都的风俗人情,对于向现代化都市转变的北京表示出深深地忧虑,挖掘传统文化因子在市民阶层的沉淀。沈从文在都市文明的批判中没有重复上述作家的思路,而是在生命的体认中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哲学视角,用“自然人性理想”的尺度去丈量都市人性的缺失与扭曲。沈从文在他所构筑的都市世界的审美观照中,包含着一种犀利的文化批判眼光,从中传达出独特的生命理想,并通过这种生命理想表现出独特的创作追求。因此,探讨沈从文创作中的都市生命形式,对于理解沈从文的都市小说及其全部创作是很有必要的,由此可以发现其创作的独特性的一些重要方面。
二
始终自认“乡下人”的沈从文,当他把小说创作视点由自己曾经生活过的“湘西世界”转移到现在生活其间的都市社会时,沈从文毫不掩饰地表达他对都市的情感厌恶和道德批判。那么,沈从文拿什么掀开都市的面纱?他以人性和道德完善理想发现了都市文明的生活和生命,或是暴露上流社会和绅士家庭的欲望游戏,或是描绘知识阶层的虚伪做作,或再现了一部分生活在上流社会中不甘沉落,力图超拔泥沼的人们,或展现了都市下层贫苦人民的道德光辉。从而展现其都市小说中的各种都市生命形式。
一、人性腐蚀的都市绅士阶层
沈从文对都市世界的情感取向较之湘西世界时逆向而行的,当“乡下人”的眼光转向都市生活时,就从看湘西世界时的平和与宽厚顿时变得锐利与尖刻起来,不时露出讽刺的锋芒。都市世界在他笔下显露出来的生活样态,往往成为讽刺与嘲弄的载体,对绅士阶层生活的针砭与解剖已成为他的一个重要视点。这类作品有《绅士的太太》、《有学问的人》、《某夫妇》、《或人的家庭》、《若墨先生》、《王谢子弟》、《大小阮》等,最具代表性的是《绅士的太太》。正如他在《绅士的太太》中开宗明义地说:“我不是写几个可以用你们石头打他的妇人,我是为你们高等人造一面镜子。”[1]这样突出了绅士阶级人生形式的腐蚀传染性,它像一个巨大的无形的黑色染缸,侵蚀着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小说主要描绘两个绅士家庭的日常生活状态,在讽刺调侃的调子里,展示了一幅绅士阶层醉生梦死的生活图景。这些绅士淑女,表面上礼数讲究、稳重贤淑,背地里干的都尽是肮脏勾当。生活在豪华的大公馆里,整日忙于串门、打牌、上馆子、进赌场,放浪堕落,醉生梦死,用“虚假”保持其文明外表和体面秩序,暗藏心机,对握有旁人隐私怀有浓厚的兴趣。如其中描写绅士太太要试探月光下在大少爷书房窗边听到的女人笑声是谁,于是当三姨太回到客厅时她便说:“三娘,你真是使人要笑你们,怎么晚上也擦得一身这样香?”再说:“外面月亮真好,我们打完这一牌,满圈后,出去看月亮。”有这样特有的语言方式暗示了三姨太偷情事情的败露。这种绅士社会的绅士式的语言规则充分展示了一场虚情假意的人生游戏,而对两性关系的摹写,则展示了绅士们的“爱”在含情脉脉的纱网中受到阉割、扭曲,甚至“爱”成**。绅士家人表面上个个讲究风度修养,暗地里却是另一番不能见人的勾当。早已失去性机能的瘫子绅士拥有三房姨太,年轻的三姨太不甘寂寞,与大少爷私通;另一个绅士的太太为报丈夫的不忠,也掺杂近来,构成一种畸形的三角关系。绅士的趣味在于寻花宿柳,太太的乐趣来自窥视捉奸,这里面充斥这夫妻间的相互欺骗,两性关系间的**与糜烂,毫无意义的交际与处心积虑的陷阱,所有的人物都成为受物欲与情欲驱遣的可怜奴隶,沦为人性异化的“衣冠禽兽”。因此,都市绅士阶层家庭看似守礼有节的面具下充斥着**、通奸和欺瞒,道德观念的伪善和行为方式的堕落形成巨大反差。再如《大小阮》中的叔叔大阮是一个人格庸鄙手段下劣的都市绅士形象,他认为侄子小阮参加革命活动是“中毒”太深,而且“不可救药”,等于“跳火坑”,而标榜自己处事“稳健”,把媚悦女人出入社交场所作为生活的最高目标。他把小阮托他保管的活动经费据为己有,并以此为资本爬入上流社会,并且“凭地主,作家,小要人的乘龙快婿三种资格,受欢迎回到母校去作训育主任”,成为所谓“社会中坚”。因此,通过对这些绅士阶层的讽刺和嘲弄,沈从文向我们有力的呈现出具有普遍性的腐朽堕落的上层社会病相。
二、道德虚伪的都市知识阶层
如果说沈从文对都市绅士阶层持异常犀利的讽刺与嘲弄态度,那么,他对自己处身其间的知识阶层所持有的态度则混合着悲悯与戏嘲的异样成分,着力于对知识分子进行灵魂与心理层面的解剖,这也代表了沈从文看取与理解都市生命形态的另一维度。这类作品有《八骏图》、《有学问的人》、《知识》、《记一大学生》、《自杀》、《平凡故事》、《来客》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八骏图》。在《八骏图》中,作者从八个学者的心理揭穿“八骏”浮在思想表层的种种虚伪。他们八个都是“人人皆赫赫有名”且知识渊博的著名教授,或尊奉独身主义,或自诩清心寡欲,或满腹社会道德,而下意识中爱欲的本能却都被压抑着、堵塞着,只有借助变态的行为流露出来,我们且看这些病态的表现。教授甲尽管表面庄严老成,一幅道学家的模样和气派,但其卧室里却是:“枕旁却有两本香艳诗集”,“大白麻布蚊帐里挂一幅半裸体的香烟广告美女画”,“同时窗台上海放着一个红色保肾丸瓶子,一个鱼肝油瓶子,一幅头痛膏”;教授乙在海边看到一队穿新式游泳衣的青年女子,大感稀奇,就流连不去,禁不住意乱情迷,并“从女人一个脚印上拾起一枚闪发珍珠光泽的小蚌螺壳,用手指轻轻的很情欲的拂拭着壳上粘附的沙子”,赞笑着它的美丽;教授丙自认是“老人”,对恋爱不再感兴趣,却又死死盯住达士房中那希腊爱神雕像上的大理胴体的凸凹处,仔细端详,并想起一个顶美的内侄女;教授丁说“自己倾心女人,就不让对方知道,尽她嫁一个不如自己的男子,等她衰老,再告诉她”,“我的爱一定还新鲜活泼”;教授戊是个结了婚又离婚的男人,主张对女人不宜停留在莎士比亚式的辞令追求上,要抓住机会,“就默默的吻,就抱,她到后就成了妻子”;教授辛“简直是个疯子”,自以为身心健康的周达士发现这六位教授都有“病”,他向远方的未婚妻表示,要医治他们的“病”,然而当黄衣女子把目标对准自己时,这位自命为医治人类灵魂的医生,最终也承认自己“的确已害了一点很蹊跷的病”,推迟了与热恋中的女友相会的日期。沈从文通过细致而精彩的描绘,表现了这群教授的欲望被压抑着、禁锢着,却又极力装饰着虚伪的外壳,他们的人性都已被他们的那种“文明”所扭曲,变成了精神上的“畸形人”。同时,也揭示了由现代文明造就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和心态,讽刺都市人程式化的爱情,被文明禁律扭曲的情欲,从而批判了知识分子这种扭曲的、不健康的、毫无生命优美和激越的非自然人生。
三、力图挣脱庸俗人生的都市新女性
沈从文建构的都市世界也并非全无亮色,而是在都市的整体性污浊与灰浊中,也有一脉生机存在,尽管这种亮色也许在都市世界并不惹眼,但却是民族生命精神在都市顽强生存的一种象征。作为一位深谙艺术辩证法的作家,沈从文在都市世界与湘西世界的两相对照中,既清醒地意识到“文明病”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性,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在都市主流性的病态生命形式后面,也潜伏着一脉跃动的生命之流,与湘西世界的生命精神相互映衬。这在他的后期作品中得到体现,如《如蕤》、《薄寒》、《都市一妇人》、《一个女剧员的生活》等,这些小说都具有系列性特征,都表现都市女性爱情与婚姻,都是描绘都市女性追求真挚爱情的复杂心路历程,表现她们因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所引起的内心痛苦与彷徨,以及对于现实的挣扎与反叛。这些女性不再是被毒害而不知甚至还乐在其中的绅士太太,而是身受都市生活的桎梏,却不甘沦落的都市知识女性,她们力图从都市的窒息中解脱,而在乡村精神中寻找灵魂的归宿。
《如蕤》中那个城市女子如蕤,对城市中虚伪的道德厌倦表现出对城市文明的极大反感:“都市中的人是完全为一种都市教育与都市趣味所同化,一切女子的灵魂,皆从一个模子里印就,一切男子的灵魂,又皆从另一个模子印就”。个性与特征全不复存在了,恋爱变成了商品形式,恋爱如同在商人手中转着,千篇一律,毫不出奇。主人公如蕤厌倦了那些“成为公式的男子与成为公式的爱情”,甚至希望“在强暴中得到快感”。《薄寒》中那个年轻女教师渴求异性的欲望更强烈,为了逃出这个虚伪的衣冠社会,她甚至“愿意被人欺骗,愿意被弃,愿意被蹂躏,只要这人是有胆气的人。别人叩头请求还不许可,若这人用力量来强迫她时,她甘心投降”。她向往“一种惊心动魄的波澜,一种流泪流血的社会”,[2]但却找不到,周围的男子都“微温、多礼貌、整洁,这些东西全是与热情远离的东西”,[3]她嫌恶这一切,最后屈服于一个鲁莽无畏的军官。《都市一妇人》中的那个将军遗孀,因心地单纯而误入上层社会的圈套,向往爱情屡遭遗弃,在对男人实施的变态报复中却又没有完全泯灭人性,对年轻军官满腔热情,却又狠下毒招,这是一个在都市生活碾压下人性未泯灭但人格变态的悲剧性人物。再如《一个女剧员的生活》中的萝,尽管出身于都市上层社会,但却与弥漫于上层社会的虚伪庸俗气氛格格不入,在性格上表现出反叛性,结果萝摆脱众多追求者的纠缠,而与初次相识的宗泽闪电般订婚,她厌恶向其献殷勤的温文尔雅、谦卑柔弱的知识男性,向往湘西世界的原始野力。[4]在这些作品中沈从文在对都市文化的审视中,向我们展示了都市新女性形象,这些都市社会的女性们想摆脱上流社会的羁绊,厌恶并反抗这庸俗的人生,渴求一种新的人生,她们向往“固执的热情疯狂的爱”,向往“光明如日头的另一种生命”。同时,这些充满理想色彩的女性将那些带有乡村气质和精神的男子作为拯救自己肉身和灵魂的力量,这是作者对乡村和都市两种文化的评判,也是“以乡村改造都市”命题的间接表现。
四、闪现道德光辉的都市下层贫民
在沈从文的都市世界中,主要通过上流社会绅士阶级的庸俗人生,提出了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批判。但在为数不多的几篇小说里,他同时将目光转向都市的“抹布阶级”,涉及了都市贫民的生命形式,侧重于展示这些都市贫民泥涂里的道德光辉,既与都市上层的生活样态形成鲜明的对照,又构成对湘西生命形式在都市背景下的某种回应,从中似乎可以看到湘西乡下人晃动在都市里的背影。更确却地说,从中可以看到湘西生命精神在都市贫民身上的显现。[5]这类作品如《腐烂》、《生》、《泥涂》等,集中展示了30年代都市下层社会一角的现实图案。
小说《生》撷取一个都市街头极常见的场景,抒写出玩木傀儡戏老人的人生辛酸。这老人在烈日的炙烤中,一次又一次不停顿地玩着王九打倒赵四的老一套,在他心里,埋藏着一段不让人知道的往事:王九是他死去的儿子,王九是死于同赵四的相拼。“王九死了十年,老头子在北京城圈子里外表演了王九打倒赵四也有了十年”。这当然只是一种原始的复仇情绪,然而,作品通过老人的执着,避去单纯地表现人物生活上谋求温饱的可怜努力,从灵魂深处听到了下层人民对生的权利和人生尊严的急切呼喊。《泥涂》着重写了几个下层人物,如刘娘、祖贵、张师爷、刘娘的秃头七叔等。尽管他们都身份卑微,生活上的需求简直比动物还低,但却都不忘做人的尊严,都有共同的人类同情心。在一场突发性的火灾中,祖贵为救火则“失去了原来的人行”却全不把受伤当做一回事,认为这不过是做人的义务;秃头七叔在瘟疫中五个孩子死了两个,在救火中“自己一切东西都烧掉了,还发痫似的极力帮助别人抢救物件,照料到那些逃难的女人小孩”;刘娘等下层妇女也都加入到救火行动中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张师爷在这里是一个有着复杂性格内涵的人物,一方面,他“仗义热心”,“尽想帮助别人”,为下层社会利益奔走,最后在救火中位救人、救小孩、救猫、救鸡中被砖头砸死;另一方面,他又常常“陪巡长烧烟”,与当官的套近乎;一方面请愿失败,他说着“气氛大话,要报仇,要烧房子”,另一方面,他又总是不忘上书请愿并坚持要在禀帖上写上“恳予俯赐大舜之仁”一类糊涂话;一方面,他穷的一无所有,“自己常常挨饿,另一方面,又念念不忘自己过去的“上士”身份,抱怨革命党把他的地位革掉了“,并死抱着”这是民国,五族平等“的信念不放。小说写出了这个人物性格的两重性,及其内在的统一。它统一在人物过去的特定的经历中,统一在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现实关系中。他是一个被资本主义经济畸形发展所殃及的民国初年的“遗民”。[6]同时,在作品中也体现了张师爷所代表的下层社会传统道德观念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矛盾。
沈从文从这些下层人物为维护社会公众利益舍生忘死的生命行为中,挖掘出他们泥涂里的道德光辉。在他看来,与都市上层社会仅仅有“生活”而无“生命”截然相反,这些下层人物栖居在“生命”的高处,显示出精神上的优越性,他们不仅具有健康理想的人性,而且并不因身份卑微而弃却做人的尊严与责任,也不因身存极度困苦而放弃对人生远景的凝眸,其生命形式焕发出神性的光辉,从中寄予着沈从文“向人生远景凝眸”与“生命庄严”的生命理想。
三
沈从文曾无数次表白自己“实在是个乡下人”[7],他执着地以“乡下人”自称,以“乡下人”的视角关照都市世界,正如他说:“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柏子》和《八骏图》对照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阶级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明显具体地反映在作品里”。[8]毫不夸张地说,对都市人性的指斥,对都市“文明”的怀疑与批判,沈从文这种写作姿态在现代中国作家中,最为激切最为鲜明。那么,沈从文为什么成为都市最为刻薄激愤的文学者呢?我认为凌宇先生的解释最为精确,那就是“城乡对立互参模式”。[9]因此,沈从文所建构的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在这两相对照中展示出截然不同的生命形式,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全部创作的基本思想内涵及其艺术表现。
在生存体验维度上看,沈从文所建构的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代表“两个对立的经验世界”[10]深深地打上沈从文个人的生命体验色彩。在湘西世界,那里,“神之存在,依然如故”,[11]地方上,“人生情感的朴素,观念的单纯,以及环境的牧歌性”[12]都一如既往,象征一个“神的时代”,在这里,沈从文体验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3]一种自然和谐的生命境界。而相反,在都市却是一个“神已解体的时代”,置身其间,沈从文体验到的是一种强烈的异己感和异化感,由于这种对都市社会情感上的拒斥感,沈从文眼中的都市就是一个“衣冠社会”,虚伪、自私、怯弱、灵魂的扭曲与生命失去活力等等病态现象,都触目惊心地显露出来。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人往往只剩下一具“空壳”,生命的丑陋处全都显露出来。正是在这样的两极性生命体验中,沈从文强烈地感受到湘西社会与都市社会代表的两种不同的生命形式,因此在他的创作中,就构成了两个对照与互见的艺术世界,体现出其独特的艺术追求和创作个性。
从人性维度上看,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代表了两种对立的人性形态。在湘西世界中,自然人性与原始人性尽管常常表现为生命的“自在状态”,但却与美和爱合一,显出自然率真的生命品格与雄强健康的生命气魄。在都市社会里,人性受到压抑,生命本质沦丧,结果形成“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14]形成都市人普遍的“阴性人格”。在这样的两种人性的对立的形态中,我们便可以看到沈从文关于“生命”与“生活”的思想,“生命”指陈健康理想的人性形态,表现为一种自然和谐的生命形式;“生活”指向病态扭曲的人性,表现一种庸常无聊的生活样态,因此,在这两种世界的对照与互见中,可以明显看到其对立的人性形态,从而看出其思想指向。
从价值维度上看,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代表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我们知道,“生命神性”与“生命庄严”是沈从文做追求的生命形式。在湘西世界中,一切都与真善美连结,显示出生命的神性,是一种健康理想的生命形式。在都市世界中,一切则与假恶丑连为一体,是一种堕落与下降的生命形式。这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在沈从文的创作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中一可以看到其关于“生命”与“生活”的思想,这一思想主要是通过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的对照与互见中鲜明地体现出来,并贯穿其全部的创作当中。
沈从文从其“乡下人”的独特视角出发,因其独特文化品格的影响,以及对人性问题的独特思考,为我们构筑了一个独特的都市世界,在伦理道德和乡土文化的层面上审视都市的生存状态,体现出对人性异化的忧虑和对人性复归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西方近现代从异化角度对文明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哲学思潮”,[15]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为“一种现代观念,一种现代人所具有的批判意识、怀疑精神和超前眼光”[16]。他所提供的审视都市的别一种立场和方法以及这种面对现代文明审视人性异化的文学行为本身,都使他区别于其他都市小说家,从而体现出其独特的创作思想和艺术追求。
(《遗山先生文集》卷38)如范仲淹入相出将的政绩一样,他的才艺也是多方面的。他精通琴律,书法很好,诗词文章也都有脍炙人口之作留传后世。范仲淹的散文和词的成就早有公论,毋庸多说。他的诗名似乎不为后人所重视,在诗歌史上也无有一席之地,但是范仲淹的诗却自有一种独特的风格,而且有裨干我们从侧面研究范仲淹的人品思想。笔者不揣浅陋,对范诗试作一初步探讨。
关干范仲淹诗歌的艺术特色,前人论之甚少。只有明人蔡增誉为新刻的《范文正公全集》作序,含混地称他“词篇或类元、白。”这样的平语很难说是褒还是贬。因为北宋之初,由于王出撰的倡导,文人士大夫竞以白居易诗为宗,以明白畅达的语言,一屏五代诗的轻桃浮华。然而不久,“西昆体”起来了。杨亿、刘绮等专师李商隐,片面强调形式的典雅,词藻的华靡,内容却十分地空洞晦涩,给诗坛带来不好的风气。范仲淹生活的时代,梅尧臣、苏舜钦等已经起来革除西昆体的弊习,上宗李白、韩愈,标榜“气饮”,下F张“平淡”。而这时的范仲淹仍然是在走王禹倩的一路。不过范仲淹向前人借鉴,并不墨守一家一式,他的取法是多方面的,而且往往追摹得形神俱肖,使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师承所自比如他的《和使舍人观潮》第二首的起句:
把酒问东溟,潮从何代生
宁非天吐呐,长逐月亏盈
豪逸清奇,儿可夺胎李及白。而《听真上人琴歌》的凄艳幽冷,又使人立刻联想到李贺的诗:
银潢耿耿霜棱棱,西轩月色寒如冰。
上人一叩朱弦绳,万籁不起秋光凝
伏牺归天忽千古,我闻遗音泪如雨。
哇哇不及郑卫儿,北里南邻竞歌舞。
竞歌舞,何时休,师襄堂上心悠悠。
击浮金,戛鸣玉,老龙秋啼沦海底,
幼猿慕啸寒山曲。陇头瑟瑟咽流水,
洞庭萧萧落寒木……
读到这些诗句,会使人自然产生一个疑问,诗人为何要苦苦追摹前辈大家 的不同风格是否诗人自己的艺术才能有限,还无法自出机杆,自成境界但是作者文集中又明确有如下的优秀诗作: 珠彩耀前川,归来一扣舷。
微风不起浪,明月自随船。
(《舟中分》)
江上往来人,但爱妒鱼美。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江上渔者》)
姑苏从古号繁华,却恋岩边与水涯
重入白云寻钓濑漱,更随明月宿诗家
山人惊戴乌纱出,溪女笑偎红杏遮
来早又抛泉石去,茫茫荣利一吁磋。
(《依韵酬张推官见寄》)
非烟亦非雾,漠漠映楼台。
白乌忽点破,残阳还照开。
肯随芳菲歇,疑逐远帆来。
谁会山公意,登高醉始回。
(《野色》)
后一首诗将登高远眺所见苍茫迷蒙的野色描绘得生动逼真,宛如图画,尤以“白鸟忽点破,残阳还照开”最为精彩,即使置于唐人诗集中也毫不逊色。
范仲淹还是描摹物态的高手,他的诗作中不乏有这样的佳句:
云中凋玉叶,星际落榆花。
(《次韵和刘夔判官对雪》)
清风起丛桂,白露生阶栏
(《明月谣》)
山分江色破,潮带海声未。
(《送识上人游金山寺》)
这些秀丽的诗句足以解消我们心中的疑问,我们不能不承认作者有诗人的天赋、才华。但是,一个新的疑问又产生了。范仲淹的诗歌,或明快,或疏淡,时而纤丽,时而豪放,却难以一种固定的风格来规定他,就象难以把他划入宗法何派诗人的行列中一样。而且,既然范仲淹干诗歌颇有天份,他为什么没能成就一位伟大诗人呢
因为诗人、文学家的头衔都是后人给他加上去的。他自己的志向并不是要做一个诗人。
范仲淹的理想是“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在诗中曾这样描写自己:“有客淳且狂,少小爱功名。非谓钟鼎重,非谓箪瓢轻。索闻前哲道,欲向圣朝行。”(《赠张先生》)他一心一意地想继承濡家传统的道德事业,辅佐明君,拯济黎庶,做一个正大光明的堂堂君子,他何尝措意于诗的风格!他写诗作词,全凭自己起初的感受和情思,并不重视自己文学上是否有天赋,是否诗中有的地方借用古人。正是因为这种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使范仲淹的诗和那些矫揉造作,刻意雕镂的诗人的作品相比,显得清新自然,尤为可贵。
在这一点上,一向景仰范仲淹为人的大诗人苏轼与他很相似。苏轼的词作很出色,后人认为他并不是刻意为之,“盖其天资不凡,辞气迈往,故落笔皆绝尘耳。”(王若虚《浮南诗话》)苏轼自己也主张作文要“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干所不可不止”(《答谢民师书》)。范仲淹为后辈唐异的诗作序,批评诗自“三代以还,因人之尚,忘己之实”赞扬唐异“孑然弗伦,洗然无尘,意必以淳,语必以真”(《序唐异诗》)。可见他们的主张也很近似。其实,范仲淹自己的诗就是以淳、真见长,只是他自己未必留意而已。在这一点上,他要高出苏轼一筹。 更进一步看,范仲淹做诗以“真”、以“淳”,他思想、人品的高尚自然会反映在他的诗中,所谓“诚于中而形于外”也。范仲淹经常在诗中表白自己的志向:
吾生宣不幸,所秉在刚肠。
身甘一枝巢,心苦千仞翔。
志意尚天命,富贵非我望。
主谭万乘前,肝竭喉无桨。
意君成大舜,千古闻瘫擅香……
(《鄱阳酬泉州曹使君见寄》)
即使是在完全模仿《琵琶行》的《和葛闳寺拯接花歌》中,他表达的仍是自己的感情,而且要比白居易高扬得多,虽然当时他也正遭贬滴,处境极似当年的江州司马。在听完接花者的泣诉后,他也同样联想到了自己:
我闻此语聊悒悒,近曾侍中班中立。
朝违日下墓无涯,不学尔曹向隅泣。
人生荣辱如浮云,悠悠天地胡能执。
贾谊文才动汉家,当时不免来长沙。
幽求功业开元盛,亦作流人过梅岭。
我无一事逮古人,滴官却得神仙境。
自可优优乐名教,曾不恓恓吊形影。
“进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访陕郊魏疏处士》)。范仲淹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也许正是因为他一贯是这样做的,他才在诗中表达出来。当他的诗篇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思想情操,并为他的所做所为印证了以后,他的诗作往往会显出特殊的魅力:
圣相贤君正弥纶,谏诤臣微敢徇身。
但得葵心长向日,何妨弩足未离尘。
岂辞云水三千里,优济疮痍十万民。
宴坐黄堂愧无恨,陇头无是带径人。
(《依韵酬吴安道学士见寄》)
交亲莫笑出麾频,不任纤机只任真。
远护玉关优竭力,入陪金铉敢周身。
素心直拟圭无玷,晚节当如竹有筠。
道本逍遥惟所迢,吾生何用蠖求伸。
(《酬李尤化见寄》其二)
仿佛有一种浩然正气充溢干范仲范的诗中,使读者油然而生敬意,这就是范诗独特的风格。
范仲淹的诗很好,但他并不要做一个诗人。黄庭坚为他的诗集作跋,也不从诗谈起文云:“范文正公在当时诸公间第一品也,故余每于人家见尺犊寸纸,未尝不爱赏弥日,想见其人。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文正公饮食起居之间先行之而后载与言者也。”(《黄山谷先生全集》卷27)可谓真知范公者。
举报/Report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表白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