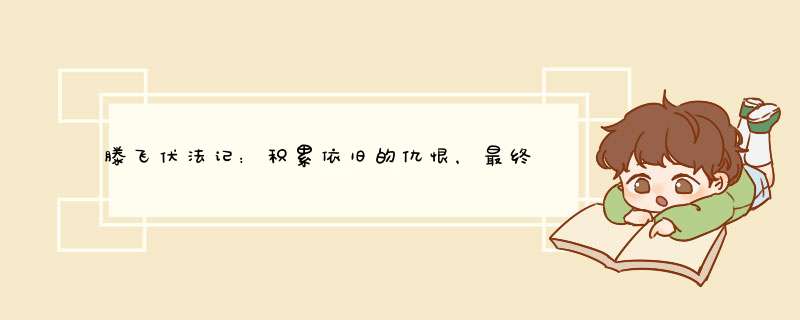
李老师美锦曾经说过,很多青少年犯罪和成年犯罪有关他的成长经历,许多犯罪行为不是一天形成的,他生长在一个缺少爱的家庭问题密切相关,容易导致孩子做违法犯罪行为。显然,邓小时失去了父亲,母亲再婚,依靠别人的经历,创造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碎尸案。
大学是每个人青春的印记,是每个人高考后魔战考试合格的象牙塔。每个人都来自全国各地,来自不同的省份。事实证明,大学生活是一种与社会人士互动的体验,而大学似乎是一个封闭的社会。你不仅可以徜徉在书的世界里,增长知识,还可以学习到人生的经验。
陆海清顺利考入四川师范大学。天生随遇而安,性格开朗,喜欢被人喜欢,喜欢笑,当然喜欢开玩笑,从小就喜欢唱歌。换句话说,这种愚蠢的性格就是让陆海清在班级和宿舍“玩”。当然,她最近说得很好。
滕彪也被四川师范大学录取。由于他童年的成长经历,他性格敏感,心理素质差,冷漠而孤独。在课堂上很少有人来联系他,他很孤独,特别独立。每次他都只看表格。
同样来自甘肃省。我被同一所大学录取了。和欺负。幸运的是,他们俩被安排在127号宿舍。宿舍里有六个人,一个来自湖南,其他都是甘肃人,原来家里看到两个人就流泪,但这次的相遇,让两个人的交流硬化了。
进学校的第一个国庆节,宿舍里几个人一起出去吃饭。哥哥们一起高兴地拼了多少酒,大家一瓶一瓶地喝,都很高兴,每喝到七瓶都很高兴,他们决定不喝了。但此时的滕某还是继续喝酒,交谈之间的心情更激动了,带着一副杀气腾腾的眼神,心里却很不高兴。从那时起,大家都认为邓鸿吉有人格“问题”。
陆海清和腾二人的床很近,性格完全不同。一是玩很多游戏,读心理犯罪小说。因此,两个人经常产生矛盾和摩擦。
有一次,陆海青打翻了杯子,泼了水。就在这时,滕先生滑倒了。由于性格原因,陆海清不但没有道歉,反而在床上微笑着。这让秋先生很不高兴,“我迟早要杀了你。”
2016年春节前夕,陆海清和她一起去玩。我感到很高兴。不要说那个快乐的字眼。我说的是特里和十。“请不要过多地参与学校的社会活动。那我就有女朋友了。像你这样的人,谁喜欢你”一直沉默的滕先生什么也没说。他把陆海青的话当作是对自己的侮辱,并把这件事记在心里。仇恨的种子在心里慢慢地蔓延。
日常交往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关系的恶化。每个周末,陆海清7点起床,到外面工作。每次我起床,都有睡觉的声音。影响滕先生的休息。两人因为这件事吵了好几次架,和别人在宿舍换了床,换了宿舍,但没有结果。
一首歌激怒了躁动的灵魂。宿舍一片宁静,一些同学正在演奏王峰的《生命盛开》。这时的陆海清忍不住一起唱了起来,这一开口激怒了腾正读着一本书。他喊道:“有什么好唱的”你唱得好吗”陆海清舍不得说:“我唱两首怎么了”两人你一声,我一声动手打了起来,腾的脸上被口袋弄伤了,卢的t恤被撕了。
之后,滕彪警告了陆海清。他说他患有抑郁症。你最好别惹他生气。陆不在乎。我觉得和男人约会太好了。开玩笑:“谢谢你。不杀人的弟兄的恩宠”。这是两个人的最后一句话。
第二天,藤杞在自己的垃圾桶里发现了陆海清的衣服,认为他是在挑衅,最后决定杀了陆海清。
3月27日,邓鸿吉给班上一名认识的女学生打了电话。人们不太关心。下午,我买了啤酒和一把菜刀,回到了我的卧室。我把菜刀藏在抽屉里,边喝边等陆海青回来。
陆海清回来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滕先生无法坐下。我在自习室里。我知道,今天陆海清没有回宿舍。这样一个生命就会消失!
陆海清回来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滕先生无法坐下。我在自习室里。我知道,今天陆海清没有回宿舍。这样一个生命就会消失!
事发后,从早上开始,陆海就充满了目光。他身上有50多处刺伤。这个事件震惊了整个学校。滕先生因故意杀人被判处死刑。
律师问他:“你为什么杀了他”“我想杀了他,”他断然地说。
当我了解到他的成长过程时,我觉得一切都是多余的。邓年轻时失去了父亲,母亲再婚,依靠他人生活。他在高中时患有抑郁症,多次试图自杀。这样的人,想必他也经历过黑暗的童年,造就了敏感、孤僻、古怪、自卑的性格。
1及时改口
历史上和现实小许多能说会道的名人,因在失言时仍死不改口而惨败的情形不乏其例。比如1976年10月6日,在美国福特总统和卡特共同参加的、为总统选举而举办的第二次辩论会上,福特对《纽约日报》记者马克斯•佛朗肯关于波兰问题的质问作了“波兰并未受苏联控制”的回答,并说“苏联强权控制东欧的事实并不存在“这一发言在辩论会上届明显的失误,当时遭到记者立即反驳。福特如果当时明智,就应该承认自己失言并偃旗息鼓,然而他觉得身为一国总统,面对着全国的电视观众认输,决非上策,于是继续坚持,一错再错,结果为那次即将到手的选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相比之下,里很就表现得高明许多。一次,美国总统里根访问巴西,由于旅途疲乏,年岁又大,在欢迎宴会上,他脱口说道:“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为能访问玻利维亚而感到非常高兴。”有人低声提醒他说漏了嘴。里根忙改口道:“很抱歉,我们不久前访问过玻利维亚。”尽管他并未访问过玻利维亚。当那些不明就里的人还来不及反应时,他的口误已经淹没在后来的滔滔大论之中了。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当面丢丑,不失为补救的有效手段。
2移植法
就是把错话移植到他人头上。如说“这是某些人的观点,我认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这就把自己已出口的某句错误纠正过来了。对方虽有某种感觉,但是无法认定是你说错了。
3引申法
迅速将错误言词引开,避免在错仍h缠。就是接着那句错误的话之后说:“然而正确说法应是——”或者说:“我刚才那句话还应作如下补充—…”这样就可将错话抹掉。
4借题发挥
借题发挥就是指错话—经出口,在简单的致歉之后立即转移话题,有意借着错处加以生发,以幽默风趣、机智灵活的话语改变场1:的气氛,使听者随之进入新的情境中去。曾有一个新毕业的大学生去某合资公司求职,一位负责接待的先生递过来名片。大学生神情紧张,匆匆一瞥,脱口说道:“腰野先生,您身为日本人,抛家别舍,来华创业,令人佩服。”那人微微一笑:“我姓滕,名野七,是地道的中国人。”大学生面红耳赤,无地自容,片到后,他诚恳地说道:“对不起,您的名字使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日本老师——藤野先生。他教给鲁迅许多为人治学的道理,让鲁迅受益终生。希望滕先生日后也能时常指教我。”滕先生面带惊奇,点头微笑,最终录用了他。
5将错就错
将错就错就是在错话出口之后,能巧妙地将错话续接下去,最后达到纠错的目的。其高妙之处在于能够不动声色地改变说话的情境,使听者不由自主地转移原先的思路,不自觉地顺着我之思维而思维。
字义约定俗成
“意内言外”这个题目是借用《说文解字》里的一句话:“词,意内而言外也。”这句话究竟该怎么讲,其说不一,不必详细讨论。我们只是借用这四个字做题目,谈谈语言和意义的关系。
前一章说过,一个句子的意思不等于这个句子里一个个字的意思的总和。可是句子的意义离不开字的意义,这是用不着说的,现在就从字义谈起。一个字为什么是这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换一种提法,为什么这个意思用这个字而不用那个字,例如为什么管某种动物叫“马”,不管它叫“牛”?回答只能是“不知道”,或者“大家都管它叫马么,你还能管它叫牛?”象声性质的字,例如“澎湃、淅沥、朦胧、欷歔”,它的意义跟它的声音有联系,不容怀疑。有些字,例如“大”和“小”、“高”和“低”,是不是当初也有点儿用声音象征意义的味道(a对i,也就是“洪”对“细”,那就很难说了。就算是吧,这种字也不多。有些字不止一个意义,可以辗转解释。例如“书”有三个意义:(l)书写,(2)书籍,(3)书信,后两个意义显然是从第一个意义引申出来的,可是当初为什么管写字叫“书”呢,回答仍然只能是“不知道”,或者“人家都这么说么”。这就是所谓“约定俗成”。二千多年以前的荀子就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他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当然,“约之以命”不能死看,决不是召集大家开个会,决定管一种动物叫“马”,管另一种动物叫“牛”,而是在群众的语言实践中自然形成的一致。
根据约定俗成的道理,字义形成之后就带有强制性,可是字音和字义的最初结合却是任意的、武断的。单字意义的形成是任意的,字组意义的形成就不是完全任意的了。比如“白纸”、“新书”、“看报”、“写字”,它们的意义是可以由“白”、“纸”等等单字的意义推导出来的。可是这里也不是完全没有约定俗成的成分。随便说几个例子:(1)“保”和“护”的意思差不多,可是只说“保墒、保健”和“护林、护航”,不能倒换过来说“护墒、护健、保林、保航”。(2)“预报”和“预告”的意思是一样的,从广播节目中只有“天气预报”,不说“天气预告”,出版社的通告里只有“新书预告”,不说“新书预报”。(3)“远距离”和“长距离”的意思是一样的,可是操纵是“远距离操纵”,赛跑是“长距离赛跑”。(4)“赤”和“白”是两种颜色,但是“赤手空拳”的“赤手”和“白手起家”的“白手”是同样的意思,都等于“空手”。可是尽管意思一样,不能倒换着说。(5)“火车”一度叫做“火轮车”,“轮船”一度叫做“火轮船”,后来都由三个字缩成两个字,可是一个去“轮”留“火”,一个去“火“留“轮”。(6)两相对待的字眼合起来说,“大小、长短、远近、厚薄”都是积极的字眼在前、消极的字眼在后,可是“轻重”是例外。“高低”属于“大小”一类,但是“低昂”又属于“轻重”一类。(7)意思相近的字联用,常常有固定的次序,例如“精、细、致、密”四个字组成“精细、精致、精密、细致、细密、致密”六个词,每个词的内部次序是固定的,不能改动(更奇怪的是都按照“精、细、致、密”的顺序,没一个例外)。地名联用也常常是固定的,例如“冀鲁、鲁豫、苏皖、江浙、闽广、湘鄂、滇黔、川黔、川陕、陕甘”。(8)意思相近的字联用,常常因为排列的次序不同,意思也有分别,例如“生产”(工农业生产,生孩子)和“产生”(一般事物),“和平”(没有战争或斗争)和“平和”(不剧烈),“查考”(弄清楚事实)和“考查”(按一定要求来检查),“展开”和“开展”(使展开),“担负”(动词)和“负担”(名词),“罗网”(自投罗网)和“网罗”(网罗人才)。这些例子都说明字的组合也常常带有约定俗成的性质,就是所谓“熟语性”。
选自:吕叔湘《语文常谈》
“约定俗成”不是遮羞布
时间:2006年05月19日 08时15分 作者: 王乾荣 新闻来源:检察日报
大众念错字是极平常之事。汉字有五六万个,老百姓没有必要都认识;连三四千个常用字,也不能要求人人念准确。比如一个水利工程师,只要能造起坚固漂亮的大坝,他将堤坝之“堤”说成“提”,无伤大雅。又比如哪怕一个作家,他不知道“淙淙”的读音,只要他能把这个词妥帖安置于行文之中,他又不当众朗读这文句,算不上太丢份儿。“祥子”在大排档与工友神聊海侃,他说不说错字,关别人啥事?
但是面对大众的播音员、主持人和演员等等,更有一贯以“文化学者”自居、经常训导别人之人,就不同了。人们不能要求他们去背《康熙字典》,甚至也不巴望他们把常用字全部读准确,但是他们手头备一本一般的文字工具书,遇到读不准的音翻一翻,还是有必要的吧。
这些经常抛头露面,以他们的声音和“文化”塑造形象,教给众人以知识的人读错了字,不光有损他们自己和他们所代表的单位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可能谬种流传。而万一他们读错了字,表示一下歉意,并立即更正,这不但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须的。
比如,著名配音演员曹雷,一次不慎将“一叶扁舟”之“扁”读作“匾”。当她发现自己的错误读音已制成音带时,诚恳地说:“实在是误人子弟,也对不起那位(原作者)泰戈尔老先生(其实是翻译家用了那么个文绉绉的词儿,而不是泰戈尔)。”她还要“借媒介向众人赔个不是”,其情可鉴。她并自嘲这是“阴沟里翻船”。这才是君子风度。
这回,大文化学者余秋雨在青歌赛上将“仁者乐山”之“乐”读成“勒”,有识者指此字在这里读“要”。余秋雨狡辩道:“我在评点时还愣了一下,想要不要读‘要’。但我想对大部分读者来说并不知道这个读音,所以我才读了大家熟悉的读音。”
他甚至讽刺正确读音者为“字典派”。字典派有什么不好?你离得了字典吗?有人为余秋雨辩护,说不能“苛责”他,读音应遵循“约定俗成”原则,云云。
苛责,意即“过严地责备”。可是没有人“责备”谁,人家不过纠正了一个读音而已,就是说,请把“一”读成“一”,而不要读成“二”,何“责备”之有?当然更没有什么“过严”——不符合事实的责备,才叫“过严”呢!
至于读音的“约定俗成”,也有过去读某音,如今准读另音的,但那要经过权威和大众认可;否则,有人读原来的音,有人读“俗成”之音,一通乱念,学话的孩子会莫衷一是。比如上述“一叶扁舟”之“扁”,如果其音或正读为“偏”,或“俗成”为“贬”,到底该怎么念呢?还有,作为姓氏的“仇”字,你是念“绸”,还是念“囚”?有一个姓“解”的人,你总不能叫他“老姐”吧?
以余秋雨的张扬个性,他如果真知道那个读音,早卖弄上了,还会“一愣”?把“仁者乐山”之“乐”说成“勒”,即说明他理解错了,因为“仁者乐山”之“乐”当“爱好”讲,并不是“快乐”的意思——正如“音乐”之“乐”必须读“月”一样。“暴乐”之“乐”当“稀疏”讲,还念“luo落”呢。
现在的很多风云人物,文字功夫大都欠佳。看似很有学问,或者自我感觉学问挺大的人,一刨根问底,就露馅了。露馅没有关系,像可敬的曹雷女士那样,谦虚谨慎一些,总可以吧?
那次倪萍把“关卡”的“卡”读成“卡片”的“卡”,人家指出来,她说她老家就那么念——其实这根本不是方言和普通话读音差别的问题。
朱军在采访大卫·科波菲尔时,居然把“腼腆”说成“腼典”;饰演毛泽东的古月,湖南口音模仿得挺像,却大大咧咧把人家“韩复榘”喊成了“韩复渠”;上届青歌赛点评人之一滕先生,也将“和”的第四声念成了第二声……
另,咱们经常在广播电视里听到类似于“机戒(械)”、“包屁(庇)”、“漆(膝)盖”、“狡(角)色”……这样的读法,真是错声一片,难道都属于“约定俗成”?
吃“开口饭”的人,用心认字吧,别再拿“约定俗成”当遮羞布了。
将错就错就是在错话出口之后,能巧妙地将错话续接下去,最后达到纠错的目的。其高妙之处在于能够不动声色地改变说话的情境,使听者不由自主地转移原先的思路,不自觉地顺着我之思维而思维。引申法,迅速将错误言词引开,避免在错仍H缠。就是接着那句错误的话之后说:“然而正确说法应是”或者说:“我刚才那句话还应作如下补充”这样就可将错话抹掉。就是把错话移植到他人头上。如说“这是某些人的观点,我认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这就把自己已出口的某句错误纠正过来了。对方虽有某种感觉,但是无法认定是你说错了。
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犯错,如果在某一场合说了不合时宜的话或者做了不当的事,就应该设法加以补救,而且应该紧跟着就用后话去弥补。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表白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