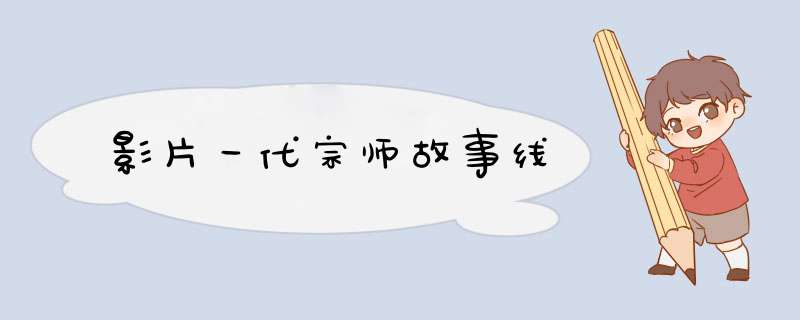
**里三条线,三个人物主要人物,三个武术流派分别代表三种格局:
一、一线天(张震扮演)
他,是一个八极拳的顶级高手。出手,必要人命。
他,本来是一个国民党的军统特,专门负责上级赋予的暗杀行动。
他暗杀过很多日本军官,绝对算得上是一位地下的民族英雄。
可是,他没想到,自己也有马失前蹄的一天。在他行刺汪精卫的时候,因任务失败而受伤逃跑。
列车上,成堆的日本兵为了抓住刺客,正在凶恶地对旅客逐个排查。
他马上就要被发现,准备拼死一搏的时候,对面突然来了一位貌美的女子,假扮成她的伴侣,助其蒙混过关。
一线天(张震饰演),八极拳,见天地。作为武术家及时参与时事,以军统特务身份刺杀日寇而后退隐香港开理发店守望宫二。可谓侠客之大者,于国有难时,以己身践行国家兴匹夫有责,事成之后重新回归个人生活,深藏功与名,混迹泯泯于红尘市井之中,所做作为与天地无愧。
二、宫二**(章子怡)
宫家六十四手和八卦掌传人,见自己。父亲宫宝森是中华武术会会长,被叛出师门投靠日寇的马三所杀,为了雪耻复仇,她决然退亲奉道,在火车站击败马三,断其筋骨,拿回了宫家的武艺,并且一生守誓,终生不嫁,以武载道,活出了极致的自我。
三、叶问
叶问与宫二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王家卫天才地配上一段意大利歌剧,这场戏恰到好处地表现出,两个人看上去若无其事的内心已经翻山倒海。之后的“夜里藏花一度,梦里踏雪几回”也非常暧昧,要知道,宫二又叫“宫若梅”,踏雪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梅。包括宫二的回复“一约既订,万山无阻”看上去都是男女之间的表白。
扩展资料:
一、剧情简介:
广东佛山人叶问(梁朝伟饰),咏春拳掌门人。年少时家境优渥,从师咏春拳第三代传人陈华顺学习拳法,师傅“一条腰带一口气”的告诫,支持他走过兵荒马乱、朝代更迭的混乱年代。妻子张永成(宋慧乔饰)泼辣干练,二人夫唱妇随,琴瑟合璧。
1936年,佛山武术界乱云激荡。八卦掌宗师宫羽田(王庆祥饰)年事已高,承诺隐退。然而其所担任的中华武士会会长职位,自然引起武林高手的关注与觊觎。包括白猿马三(张晋饰)、关东之鬼丁连山(赵本山饰)、咏春叶问等高手无不将目光聚焦在正气凛然的宫羽田身上。
拳有南北,国有南北乎?最有德行之人才堪会长重任,然这浮世虚名却引得无数迷乱之人狂醉奔忙,浪掷残生。生逢乱世,儿女情长埋藏心底,被冷若寒冰的车轮碾作碎泥。
二、故事情节
1、“一线天”开理发店
原本故事主线之一的“一线天”张震,在《一代宗师》中仅剩三场戏,不少观众觉得该部分无头无尾。戏中张震在火车被章子怡所救,此后即再无交集,看过**的观众,都觉得在张震跟章子怡的那段戏,留白的部分太多,要在足本上才可以窥全豹。
王家卫在接受采访时补充说:“章子怡在火车上救了张震之后,他们在香港还有一次碰面。张震视子怡为知己惺惺相惜,虽然念念不忘,但完全没有介入她的生活,只是在身边守候。”
然而片中张震的最后一场戏,已经跳跃至他在香港开了理发店,并教训了小沈阳饰演的小流氓,对于张震开理发店的原因,王家卫说:“因为理发店就在子怡的医馆附近,作为对子怡的守望,到她死为止。”
王家卫解释“一线天”的原形来自少时家里附近的一间理发店,他说:“那个时候尖沙咀家里附近有间理发店,楼下理发楼上教武,当时真的好多卧虎藏龙的高手,都散落在低下阶层里面隐世。”
2、赵本山匿世
喜剧大师赵本山出现在以“闷骚”著称的王家卫**中,也让一些观众感到不习惯,不过抛开先入为主的眼光,赵本山在片中饰演的丁连山也有很多故事可以挖掘,只不过在片中他的戏份也语焉不详,仅留下一个“匿世高手”的形象。
王家卫解释说,丁连山和一线天同为当时北方暗杀团的杀手,致力以暗杀手段推翻满清政府,“赵本山的戏里提到1905年,当年就发生北方暗杀团刺杀清廷出洋五大臣的大事,赵本山参与其中,所以避难去佛山”。
导演表示,生于大时代的武术家,都有忧国忧民的使命,所以身为八卦掌大师兄的赵本山舍易取难,将中华武术会会长传给师弟章子怡的父亲,成就他的“面子”,自己则隐姓埋名,成为了“里子”,这就是片中的一句经典台词“人活一世,有人成了面子,有人成了里子,都是时势使然”所表达的内容。
-一代宗师
人民网-“一线天”一生守候宫二王家卫解惑《一代宗师》
林黛玉最怜惜花,觉得花落以后埋在土里最干净,林黛玉第一次葬花是因为花儿落了,贾宝玉要把他们丢进水里,,林黛玉怕他们流到臭水沟,所以葬花。
第二次葬花是黛玉头夜敲怡红院的门找度贾宝玉,晴雯误以为是丫头,便拒绝开门。黛玉错疑在宝玉身上,那一夜她枉自嗟叹着身世生宝玉的气。
次日恰逢饯花之期,看见落花满地,便躲过了众人来到昔日葬桃花的地方,更不由感花伤己,感叹自己的凄伤身世,写出了那篇有名的《葬花词》,不觉已悲痛地专倒在了葬花坡之上。宝玉听到后痛苦不堪,宝玉赶上去作了“既有今日,何属必当初”的沉痛倾诉,才化解了这一场误会。
扩展资料
林黛玉的性格特点:
林黛玉生得容貌清丽,兼有诗才,是古代文学作品中极富灵气的经典女性形象。从小聪明清秀,父母对她爱如珍宝。5岁上学,6、7岁母亲早亡,10岁师从贾雨村启蒙。
林黛玉敏感、细心、淡泊、真实、易伤感、绝顶聪明、悟性极强、自尊自爱、多愁善感、博览群书、学识渊博。林黛玉才学横溢和浓郁的诗人气质,容易感到寂寞,害怕孤独。不轻言放弃,但有时过于顽固,感情丰富。
在一代宗师中扮演宫二、我觉得她的演技非常好
2013年的时候,看《一代宗师》,最为心折的角色非叶问而是章子怡的宫二,凭一口气,点一盏灯,章子怡将一个女人一生尽数藏在衣襟与指掌之中,单手为单刀双手为双刀,有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匆忙,也有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牵挂,有如大地安忍也有如六十四手般。
缘悭一面的遗憾,却凭着这叶底藏花的身姿,一约既定万山无阻的气势,把“一代宗师”演成了“宫二传”——最好的运气是什么?是我在最好的时候碰到你;最好的爱情是什么?就是一句:你来,我等着。功夫,爱情,章子怡的这两样,都让人动容。
这一版影片中,情节有诸多增有删,围绕章子怡的那些横生的枝节,没来由的点缀,都从故事中去掉,便有了更为清晰的,纵贯始终的线索——希望有一日,我可以再见宫家的六十四手。梁朝伟的一句寄望,章子怡一生的挣扎,故事都在章子怡的功夫与感情上。六十四手与“我心里有过你”为敌,章子怡最释怀时的表白,平淡中有波澜,不和时势论输赢,心和梦以及人生,都是易碎品。
因为贯穿始终的线索,也因为这镜花水月般的感情,章子怡的宫二,形象更为立体深刻,相较于上一版结局无缘再见六十四手的遗憾错失,这一次,王家卫在字幕后,让章子怡给了梁朝伟“一扇门的时间”看宫家的六十四手,一如乱世儿女的一厢情愿,惊鸿一瞥。却也了了观众两年前的一个心愿。一扇门的时间,一个时代的距离,一个经典镜像中的章子怡。
“叶里藏花一度,梦里踏雪几回”的意思是才只是刚刚碰面,浅显的交涉,心绪却不由自主跟对方随而去,在梦里相寻。
“一约即订,万山无阻。”的意思是当许下诺言时,不管万水千山,路途由多么遥远,也无法阻挡前进的脚步。
“叶里藏花一度,梦里踏雪几回;一约即订,万山无阻。”这句话出自香港导演王家卫的功夫**《一代宗师》,是描写叶问和宫二的句子。
扩展资料
宫二性情刚烈,要报仇,“我不要一世,我只要一时”。报了仇,也断了后。她最后一个镜头是在白茫茫雪地里一个人习武。她心里很明白,“我选择留在自己的时代”。“我见天地,见众生,唯独见不到自己”,她知道自己过不了我执这关。
而叶问,从一开始感兴趣的并不是宫二,而是她的64手。他痴迷的是宫二代表的武林,一个他未能超越的境界。后来叶问去东北找宫二,以及宫二临死前向叶问表白,叶问却说“我们之间没有恩怨,有的只是一段缘分”他感兴趣的不是儿女情长,叶问对宫二更多是棋逢对手、见贤思齐的惺惺相惜。
参考资料:
婴宁人性美的回归
内容提要:婴宁作为《聊斋志异》中一位勇于反抗封建礼教的鲜明女性形象,其“爱笑”的特点与《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哭”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无独有偶的绝调。
本文试从婴宁爱笑的特点入手,对其性格及其形成原因进行理性的探索。
最终站在美学角度认为婴宁的笑是一种人性美的体现。
并且肯定这种人性美,是作者对于先秦时代理想人性的回归。
从而对《聊斋志异》的审美理想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解与把握。
关键字:婴宁 人性美 回归
《聊斋志异》驰想天外,幻迹幽冥,花妖狐媚,梦魂依稀,成为集神话志怪寓言之大成的宝典。
其神仙狐鬼精魅故事,不仅在叙事模式上超越了六朝志怪小说,,更为重要的是,其“志怪”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将其“游心娱目,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巫的六朝志怪”[1]小说发展成为作者“集腋成裘,浮白载笔”仅成的“孤愤之书“。
充分表达了作者寄寓其中的对于当时黑暗社会现实的忧思孤愤之情。
而《婴宁》一文,更是以蒲松龄”我婴宁“的爱称表达了作者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人格倾向,在婴宁“率直,纯真,浪漫”的美好人性背后,是蒲松龄对于一种完美人性的执著的追求。
一 婴宁的笑
婴宁最大的特点就是爱笑。
文中用“笑”来刻画其天真烂漫共26处。
出游时“笑容可掬”,见有人挑逗她时是“笑语自去”在园内是“含笑捻花”,见客人时是“笑不可揭”,下树时是“且下且笑”,行婚礼时是“笑极”。
再看与王子服见面一节[2]:
媪曰:“唤宁姑来。”婢应去。
良久,闻户外隐有笑声。
媪又唤曰:“婴宁,汝姨兄在此。”户外嗤嗤笑不已。
婢推之以入,犹掩其口,笑不可遏。
媪逋目曰:“有客在,咤咤叱叱,是何景象?”女忍笑而立,生揖之。
媪曰:“此王郎,汝姨子。
一家尚不相识,可笑人也。”生问:“妹子年几何矣?”媪未能解;生又言之。
女复笑,不可仰视。
媪谓生曰:“我言少教诲,此可见矣。
年已十六,呆痴如婴儿。”生曰:“小于甥一岁。”曰:“阿甥已十七矣,得非庚午属马者耶?”生首应之。
又问:“甥妇阿谁?”答曰:“无之。”曰:“如甥才貌,何十七岁犹未聘?婴宁亦无姑家,极相匹敌。
惜有内亲之嫌。”生无语,目注婴宁,不遑他瞬。
婢向女小语云:“目灼灼贼腔未改!”女又大笑,顾婢曰:“视碧桃开未?”遽起,以袖掩口,细碎连步而出。
至门外,笑声始纵。
这样的举止言行,是超越我们常人正常的行为表达方式的。
也许,在许多人的眼中,婴宁的笑已被归入了傻大姐的行为表现当中。
那么,婴宁到底傻不傻呢?实际上婴宁不傻。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婴宁一露面,捻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
她看到王子服对自己一个劲地盯着看,笑吟吟地说了句“个儿郎,目灼灼似贼。”大大方方地把花丢到地上,跟丫鬟有说有笑的走了。
婴宁说的“贼”不是“小偷”,是淄川方言,淄川人叫心爱的小男孩是“小狼贼”。
婴宁似乎无意的丢花,其实是丢的是爱情信物。
婴宁再露面,执杏花一朵,她爬到树上摘花,看到王子服,哈哈大笑,差点儿从树下掉下来。
王子服拿出珍藏的花给婴宁看,婴宁说:“枯矣,何留之?”王子服说,他保存花是为“相爱不忘”,婴宁说:这好办啊,等你走的时候,让老奴把园中花折一巨捆负送之。
王子服说:我非爱花,爱捻花之人,并进一步表白,这种爱不是亲戚间的爱,而是夫妻间的爱。
婴宁问:“有以异乎?”夫妻之爱和亲戚之爱有什么区别呀?王子服回答:“夜共枕席耳。”婴宁低头寻思许久,回答:“我不惯与生人睡。”婴宁竟然说出这样的话,表面看,她憨极了,简直是个傻大姐,实际上她假装不懂王子服的爱情表白,是为了让他把爱情表达得更热烈,更赤诚。
她说折一巨捆负送之,就是让王子服进一步把爱捻花之人的话说出来,婴宁还把“大哥欲我共寝”这句话,当着王子服的面说给母亲听,吓得王子服魂飞天外。
其实,她说“大哥欲我共寝”的话时,丫鬟出去了,而她母亲是个聋子!听到这个话而且着急得不得了的,只不过是王子服。
婴宁是在跟王子服进行妙趣横生的爱情逗乐,让王子服把爱情表白得更炽热一点。
所以我们说,在婴宁极其憨直的外表下,实际掩藏的是一颗及其聪慧的心。
那么,婴宁为什么如此爱笑呢?这就要从婴宁生活的内外环境说起了。
这里所说的外环境,指的是婴宁生活所处的自然环境。
婴宁从小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山谷之中。
那里山峦起伏却寂无人行。
繁花似锦,绿草如茵,如婴宁般美丽;洁净的空气,朴素的摆设如婴宁般无邪。
由于这是一个世外桃源,所以没有礼教的熏染,也没有世俗风气的浸浊。
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少女,不懂人情事故,只有自然与清纯。
这时的婴宁是自由的,她那爱美爱笑的个性得到最大限度的伸长。
当然,在我过的文学作品宝库中,在如此绿色环保的环境下生长起来的女性形象并非是绝无仅有的。
沈从文笔下湘西《边城》中的翠翠,汪曾祺《受戒》中的小英子,不都是纯朴的自然环境影响下而形成的典型女性形象?
再看她的内环境。
也就是作为自身主体的内在条件。
在那个受封建礼教的枷锁牢牢束缚的时代,现实世界中的少女永远也无法像狐女那样去寻找自己的爱恋者。
假如婴宁,作为一个闺中少女,逢人就笑,在户外“哧哧笑不已”,在树上“狂笑欲坠”,笑得“不能自止”,笑得“不可仰视”,甚至笑掉了自己的婚礼,这种行为岂能为世人所容?然而婴宁是狐,那么一切都可以原谅,一切都可以通过,封建礼教对于她而言,简直可以说是形同虚设。
台湾王溢嘉先生在《欲望叫响曲——〈聊斋〉狐妖故事的心理探索》[3]中用分析心理学的理论指出“《聊斋志异》狐妖故事可以说是汉族文化的潜意识里浮现出来的助人实现欲望的非法力量。
如果说《聊斋志异》里狐妖的故事是中国人个人原我及社会原我的显影,那么作为个人超我的道德意识及作为社会超我的人间法律和礼教,在这里都派不上用场,对它少有制裁力量,它们成为只有原我,而没有超我的欲望交响曲”。
也就是说,狐妖实际上是作者一种原我潜意识的体现,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象征隐喻手法。
二 笑——人性美的体现
什么是人性?
马克思在其成熟的著作中,把“一般的人性”或“人类的天性”肯定的归结为人类对于真善美的追求。
他在为新亚马克思撰写的美学条目中写到:
最可靠的心理学家们都承认,人类的天性可分作认识,行为,情感,或是理智,意志和感受三种功能,与这三种功能相对应的是真,善美的观念。
美学这门科学和感受的关系正如逻辑学和理智,伦理学和意志的关系一样。
逻辑学确定思想的法则;伦理学确定意志的法则;美学则确定感受的法则。
真是思想的最终目的,善是行为的最终目的,美则是感受的最终目的。
确实,对于真善美的自觉追求及与此相联系的追求真善美的对象化活动,正是人之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显示出人性的美好,崇高和庄严。
[4]而笑,做为一种人类精神状况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一种真心诚意的表达,是一种对于虚情假意的反抗,正是一种对于“真善美”的回归。
正如果戈里所说:“笑的美学意义就在于使人们对于那些极其卑鄙的事物唤起明朗的高贵的反感。”婴宁的笑,率直,纯真,浪漫。
他的笑,涤除了人性中“假丑恶”这一作为 的部分。
没有了假——迷信,谎言,欺骗,恶——残忍,贪婪,诈伪,丑——嫉妒,寡情,势利眼。
她以纯乎又纯自然的美来净化人的心灵,化解人类的纷争,以蕴涵着崇高理想的美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激发人追求美好生活的勇气和信心,给人类带来和平和温馨,创造和求进。
婴宁的笑,简直可以和《红楼梦》中的黛玉的哭共同成为我国小说史上无独有偶的绝调,她无拘无束的笑,无法无天的笑,笑的那样天籁,那样美,把封建时代少女不能笑,不敢笑,不愿笑,甚至于不会笑的条条框框都打破。
那时代的女人只能“向市儿井下,听人笑语”只能笑不露齿,笑不出声,否则就是有悖纲常,有失检点,不正经[5]。
婴宁如此率直,天真,浪漫的个性不是人性最美的真实写照么?
婴宁的笑,打破了一切封建礼教的苑囿,她的美赢得了王子服的爱情,赢得了身边众多女子的的友情,她的笑赢得了王母的疼爱,这种笑,难道不值得赞美吗?
她宛如山涧的清泉,丛林的清风,纯净得让人忘记生在尘世。
这种美,又岂是我们这个到处充满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社会所得企及?
所以,我们可以说,婴宁的笑实际上就是作者内心所深切渴望的,人性中至真至纯至善的美。
关于回归为什么说这种人性之美是一种回归呢?事实上,这种人性之美,早在先秦时代就有所反映。
比如说《诗经》。
尤其是“风”的部分,是古代社会的真实反映。
其中有不少写爱情,生活的作品,就是人性美的体现。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
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
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
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诗经•邶风•静女》
溱与洧,方涣涣兮。
士与女,方秉蕳兮。
女曰观乎?士曰既且。
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
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溱与洧,浏其清矣。
士与女,殷其盈矣。
女曰观乎?士曰既且。
且往观乎?
洧之外,洵訏且乐。
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
〈 郑风 溱洧〉
前一首写一个女子相悦的男子在城隅约会。
女子赠男子彤管示爱,男子则用彤管比况和夸赞女子的美。
后一首写的是一个女子同一个男子到洧水边上参加驱除不详的盛会,问答笑谑,互赠鲜花,而在《婴宁》的开头,作者也给我们展现了一个“上元佳节,游女如云” 的场面于是才有了两人的偶然邂逅,一人扔花,一人拾花,两情相悦,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不能不说是作者对于男女自由恋爱的向往。
而实际上在那个充满程朱理学,三纲五常,男女之大不防的时代,男女之间自由,单独见面,岂是社会所允许?
再者,我们从《婴宁》之名看,它取自《庄子∶大宗师》,“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婴宁,撄宁者也,撄而后宁者也。”所谓“婴宁”,就是指的得失成败都不动于心的一种精神追求。
赞美婴宁这一女性形象,也正寄寓着对老庄人生哲学中所崇尚的复归自然的天性的向往,对于人世的叹息与无奈。
这种回归,犹如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追求。
是一种人性意识的觉醒,婴宁作为生命力的象征,勇敢地冲破了封建社会女子三从四德的牢笼,以超然宁静的心境,傲然独立在这个风刀霜剑的恶浊的时世中。
她犹如一泓清泉,在这个非人间所能建构的精神世界中涤荡着世俗的灵魂。
蒲松龄的一生穷困潦倒,封建统治的黑暗腐朽,科举考试的屡试不中,程朱理学的束缚,让他对这个黑暗的现实世界失却了理想与希望,因此,作者对于这种美好人性的回归,是一种心灵的解脱,是一种芳草美人式的隐喻。
然而,这种回归也是有局限性的。
蒲松龄生活在清初,就文化心理而言,正处于明中叶兴起的启蒙思潮和复古思潮的交汇处,人生观,世界观,充满复杂性,在文学作品中呈现为矛盾性。
在《婴宁》中,就可以看出作者既有明代后期文学主情重欲的思潮色彩,又有清代文学内敛和重实的倾向。
在《婴宁》浪漫故事的背后,有一个现实主义的背景。
作者丛来也没有忘记现实,婴宁最终被王子服带入了现实社会,并且始不复笑,笑是人的本性,天赋性情,竟为世俗所禁锢,这无异于失去了精神与灵魂。
这种不笑看似一种成熟,其实是人性之花的凋谢。
张爱玲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最可恶的是莫过于一个才女成为少奶奶。”婴宁出嫁是一个悲剧,她的婚姻代表她从世外走入尘世,一个可爱的美丽的女孩儿成为人妇,成为只知相夫教子男性的附庸。
于是她的性情,梦想也就随之而泯灭了。
出嫁后的婴宁身上,我们再也看不到人的价值,尊严,权利,正当的欲望。
看到的只是极端自卑,极端软弱,任人宰割。
这时的人性,已被完全扭曲变形,甚至成为一种“人性的异化”。
[6]
蒲松龄希望人性完美,期盼人性复归,以便实现人性的重建。
这种愿望不仅可以理解,而且令人钦敬。
他试图以鬼、狐、仙去改造世人的灵魂,劝说人们远离污浊的现实, 即使身不能远离,心也要远离,以此摆脱现实给人们所带来的压抑、辱和烦恼。
这种思想情节,正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不肯同流合污的传统品格,表现了同统治阶级明显的离心倾向,具有积极意义。
然而,作为一种封建时代历史的局限性,这种理想仅仅只能成为一种回避矛盾,逃避现实的幻想,这仅仅只是这位乡村秀才乌托邦式的幻想罢了。
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嘲笑作者理想的空幻,太脱离现实。
当一般人面对阶级社会的人生重压而委曲求全时,当一般人麻木得把剥削阶级给自己套上的精神枷锁视为本体的自然组成部分时,蒲松龄却发现这是一种人性的异化和失落,这难道不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人性自觉吗?他对人性回归的梦想和追求,难道不是一般庸俗作家难以企及的精神品格吗?
人性是要回归的,但不是回到老庄时代的“小国寡民”,不是回到原始人的深山丛林,更不是回到动物世界。
只有当人类彻底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压迫之后,才能在更高的社会形态里去实现这种复归。
存在决定意识。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蒲松龄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
但他又是可敬的。
他尊重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让他笔下的“婴宁”按照客观环境的制约因素及其自身的性格逻辑去发展,没有把自己的主观愿望强加到她身上。
这种“真”,真正达到了美学意义上的李泽厚先生所认为的“真与善的和规律性和和目的性的统一”,成为了文学作品“美的本质和根源”。
[7]
注释:[1] 《搜神记》干宝等编著,顾希佳选译,浙江古籍出版社。
[2] 《聊斋志异》蒲松龄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版,143页 [3] 《古典今看:从诸葛亮到潘金莲》王溢嘉 国际文化出版社 2006年4月第1版 2156 [4] 《人性精神论 》许苏民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年5月第1版 62页\[5] 《马瑞芳揭密聊斋志异》马瑞芳 东方出版社 2006年5月第1版 381[6] 《聊斋美学》吴九成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年5月第1版 358页[7] 《美学四讲》李泽厚 三联书店 1989年6月第1版 75页
《婴宁》篇,但明伦评说:“以笑字立胎,而以花为眼,处处写笑,即处处以花映带之。”篇中爱笑与爱花两个细节极富象征意蕴和表现力。
狐女婴宁含笑捻花出场:“……有女郎携婢,捻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
后,又遗花地上,笑语自去”。
王子服一见倾心:“拾花怅然,神魂若失”,相思成疾。
“至家,藏花枕底,垂头而睡,不语亦不食”。
后,“探视枕底,花虽枯,未便凋落,凝思把玩,如见其人”,及至“怀梅袖中”寻访婴宁,得见时:……(生)乃出袖中花示之。
女接之曰:“枯矣。
何留之?”曰:“此上元妹子所遗,故存之。”问:“存之何意?”曰:“以示相爱不忘也。
自上元相遇,凝思成疾,自分化为异物,不图得见颜色,幸垂怜悯!”女曰:“此大细事!至戚何所勒惜。
待兄行时,园中花,当唤老奴来,折一巨捆负送之。”生曰:“妹子痴耶!”“何便是痴?”曰:“我非爱花,爱捻花之人耳。” 以上处处写花,也是处处写人,一枝梅花不仅是婴宁爱花成癖个性的象征,而且充当了她与王子服建立真挚、纯洁爱情的无声媒妁,终至合卺。
爱笑的细节描写,让读者“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王子服到婴宁家,其养母老媪让婢去唤宁姑后,“良久,闻户外隐有笑声。
媪又唤曰:‘婴宁!汝姨兄在此。
’户外嗤嗤笑不已。
婢推之以入,犹掩其口,笑不可遏。” 这里处处写笑,也是处处写人。
据计,篇中有二十多处不同境遇,用细节凸现婴宁迥然各异的笑貌之妙。
比如“含笑”、“隐笑”、“嗤嗤笑”、“笑不可遏”、“忍笑”、“笑不可仰视”、“大笑”、“笑声始纵”、“狂笑不止”、“笑而依树不能行”、“微笑而止”、“笑辄不辍”、“吃吃笑”、“浓笑不顾”、“放声大笑”、“笑嫣然”,等等。
种种笑貌细节,将一位憨态可掬、纯洁天真、乐观开朗而又非幼稚的少女形象,描摹、刻画得栩栩如生。
行文至此,人们自然会联想到《红楼梦》中,娴熟自如地运用笑貌细节刻画人物形象的极致。
它的造诣是不言而谕的。
但须说明的是,《红楼梦》是长篇巨制《聊斋志异》是短篇,在一个短篇里,一个主人翁身上,运用这种传神细节,细腻、精妙刻画塑造典型形象,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表白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