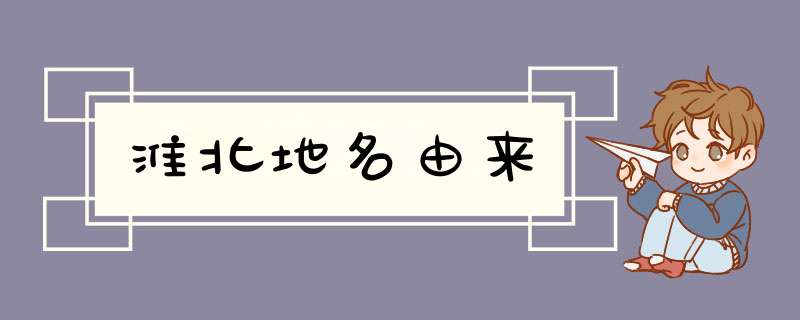
相传公元前21世纪,商王朝的创立者商汤的十一世祖相土向东部开拓疆土,建城于相山南麓,相山、相城由此得名。
淮北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四千多年前,商汤十一世祖相土建城于相山南麓,发文明之滥觞,此后历代王朝在此设郡置县。有蹇叔、桓谭、嵇康、刘伶等先贤圣哲。
风景名胜有相山公园、龙脊山、南湖湿地公园、华家湖、石板街、临涣古镇、隋唐运河古镇、大坊寺等,纪念地有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双堆集战场旧址等,被誉为皖北江南。
扩展资料:
历史沿革
夏禹分天下为九州,现淮北市域属徐州。
公元前21世纪,助禹治水有功而成为商部落首领契的孙子,商汤十一世祖相土为进一步向东扩张,由商丘迁徙至此,作为别都,此后山即为相山、城即为相城。商汤伐桀,灭夏建商,商沿夏制,相城仍属徐州所辖。周武王伐纣更商分封诸侯,以纣王兄微子启代殷,立国号宋,相属宋。
公元前588年至前576年期间,宋共公瑕为避水患,曾将国都由睢阳(今商丘)迁至相城。战国时期,齐、楚、魏灭宋,相归楚国。
-淮北
唐朝开元末年至天宝年间,李白家居东鲁。东鲁其地,确指兖州。在唐朝,兖州曾改称为鲁郡(天宝元年改兖州为鲁都,乾元元年复为兖州)。因为李白移家于此,杜甫的父亲杜闲也正在这里做官,故李白与杜甫的多次相聚,地点主要在兖州。对于研究这两位伟大诗人的初聚,需首先弄清他们各在何时初游兖州?这是个至今尚存疑议的话题。
李白举家迁徙于兖州之前两年,约在开元二十二年(或前一年)夏天,曾经有一次兖州之行,是在一入长安辞京之后,泛黄河东至汴州,游燕赵,复南行,初到东鲁,在兖州滞留数月。对此,在明清以迄当代诸家之《李白年谱》中,均失记,幸有此间李白在兖州写的作品,可资研究:即《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嘲鲁儒》、《寄远其十》、《初月》、《赠瑕丘王少府》等。
《五月东鲁行》一诗可见此行乃为李白独自一人初到鲁地,时白尚年轻,未曾及仕,为“举鞭访前途”,而“学剑来山东”,这里只言为“学剑”而来,无移家迹象。诗人好学求进之年,来此逗留,复将要返还安陆并准备再次入京,即“西归去直道”云云。清王琦《李太白年谱》谓此诗“是初游鲁地之作”。道出其时尚未移家。
《嘲鲁儒》中的鲁儒,与前诗中汶上翁为同一人,因为前诗对于此翁之嘲讽意尤未尽,复以《嘲鲁儒》再作斥责,是前诗的延伸。诗中展现青年诗人之言行豪爽,毫无顾忌地嘲讥这一鲁地儒生。
《寄远》十二首为李白在三十岁前后作于长安、洛阳等地的寄内诗,是许氏夫人在世时的作品。《其十》一首,乃为游至兖州时作。诗人离别安陆已久,思念家人,便在鲁缟上写诗寄内。安旗先生指出《寄远其十》“作于鲁地”(见《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寄远其十》题解)。郁贤皓主编《李白大辞典》也指出这是一首写在鲁地的作品。
《初月》一诗为诗人在兖州泗水畔望月抒怀之作,因闻尧祠亭上管弦乐舞,忆起前不久在燕赵边地所见戍边征战,而发“乐哉弦管客,愁杀征战儿”之感慨。作于开元二十一年秋初游河北之后。
《赠瑕丘王少府》,也是一首初游兖州之作。少府亦即县尉。李白与王少府初交即以诗相赠,盖因即将离鲁而无缘相再会。诗言“我隐屠钓下”,可知李白其时如姜尚未遇,名声不显。“尔当玉石分”句,似有如汶上翁者说过有损于他的话,要求予以辨污。诗中对并不重视李白的王少府美言恭维,知诗人还较年轻。詹钅英 指出此诗作于“尚未得势”时;安旗指出写在尚“微贱之时”——亦即初游东鲁时。李白既有移家于兖州的打算,不得不委曲于这一地方长官之下,或为听人劝告,而作此诗相赠。据以上数诗,可略见李白移家东鲁之前两年的初游行踪(余另撰有《李白初游东鲁作品考略》)。
李白从五月到秋天,居于兖州,与任城六父及诸从弟相聚,并结识了杜闲、王少府、刘长史等地方长官和竹溪六逸中的孔巢父、张叔明等,也许与杜甫同住在杜闲的官邸,方逗留时间略长。这是对李杜初遇时间最早的估计。此行,确定了两年后的移家东鲁并作了相应准备。这是一入长安后的长途跋涉,其路线是:安陆启程—洛阳—长安—洛阳—梁宋—燕赵—兖州。复经梁宋,旋返安陆。从开元十八年三十岁时辞家到返归,历时四年。
杜甫青年时代,初到兖州省亲的具体时间有三说。清人钱谦益、仇兆鳌等认为在开元二十五年,闻一多、郭沫若、萧涤非等认为在开元二十四年。今人王伯奇撰《杜甫初游兖州时间考辨》、《李白初识杜甫时地新考》(二文并编入《李白杜甫在兖州》),认为“开元二十年春正有贡举下第,始至兖州省父,是时杜甫的父亲杜闲正在兖州司马任上”。“开元二十二年,李杜初识在兖州,是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论证“杜甫因父寓家兖州,……开元二十年春,比李白早两年有半即至兖州”。这一论点发中以有详加论证,是有意义的。李白诗《东鲁门泛舟二首》,作于移家兖州之翌年桃花夹岸的早春。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中有“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与李白在初春时节月下泗水泛舟时地相合,透露出李杜同游的迹象。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谓“白家本在鲁郡。公《送白二十韵》曰‘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知白游梁园之次年春,已至兖州”(《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两人在兖州相聚,当早于此时。数年中同往来于此地,因得相识相聚。只是尚难得查到可靠的证据。
天宝三载,李白沼许还山,出长安行至梁宋(旧说洛阳),与杜甫相遇,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诗中有“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未负幽期志,兼全宠辱身。”《赠李白》中有“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味诗意,其时已深为相知。通常以为此时李杜初聚,恐未确。杜甫作于这次相聚之前的《饮中八仙歌》中,生动逼真的塑造李白形象。早于此时就结下的深厚友情,还见于杜甫的多首诗中。
杜甫诗《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中写道“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李白鲁郡送别杜甫的诗中有句,“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在兖州两人一同泗水泛舟,一同步石门、登尧祠、访范十、游甑山……携手同行,踏遍鲁城大地,当也曾同上兖州城楼。杜甫《登兖州城楼》诗中,“浮去连海岱,平野入青徐”句颇近李白,与李白诗句“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与“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句式像似,视野更开阔。不由因此猜想,太白帮少陵改诗或起自此时欤!
天宝四载秋,两人相聚,对坐已久,茫然兴起,策马登程,同到鲁城北访范十。此行,李白作《寻鲁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见范置酒摘苍耳作》,杜甫作《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陷居》。李杜访范,遂成千古佳话。参阅二诗,白诗有“雁度秋色远”,杜诗有“落景闻寒杵”,同在秋天,于访范,白诗有“忽忆范野人,闲园养幽姿。满族然起逸兴,但恐行来迟”。杜诗有“更想幽期处,还寻北郭生”。途中,白诗写“城壕失往路”,杜诗有“屯云对古城”。白诗“入门且一笑,把臂君为谁”?杜诗“入门高兴发,侍立小童清”。对辞官。李白表明“不惜翠云裘”,杜甫以“不愿论簪笏”接应。李白乘兴“自咏《猛虎词》”,杜甫则“向来吟《桔颂》……”白诗有“风流自簸荡”,杜诗有“悠悠沧海情”。此诸多相近之处,可见是同一次郊游时的作品。似乎杜甫有意仿效李白。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中。指出“(二诗)辞意亦相仿佛,当是同时所作”。又以天宝元年,兖州改称鲁郡,诗题中有“鲁城”二字,知为天宝四载李杜同在兖州时作。
“以兹谢朝列,长啸归故园。”李白被放之后,由待诏翰林转为平民。脱掉翠云锦裘,换作“角巾微服”;由当初满腔热情入京,到失意伤心而归。壮志难酬,怀才不遇,“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心灵痛遭创伤,李白视为“失道”,以“马首迷茺陂”喻之。以“遂为苍耳欺”,喻朝中小人如张土自 之流,如苍耳而已,当年初居兖州“行歌泗水春”,对前途怀美好憧憬。辞别儿童,奉诏入京,“仰天大笑出门去”,意欲去“游说万乘”,孰知事与愿违。“君王虽爱峨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经历由受宠到遭谗被疏的历程,当时过境迁,今昔殊异,积愤填膺,心神难宁之时,唯此清幽的田园,得“近作十日欢。”农家小院中的温馨,抚违法伟大心魂。这段时间,两人相处日久,情谊益深,话题放纵,以致兼带戏谑,即所谓“谑浪偏相宜”(李白访范诗句)。这是一段“脱身事幽讨”(杜甫句)之后任情恣性的闲适生活。
访范之时,还另有唱和诗,即李白《戏赠杜甫》;杜诗《赠李白》(秋来相顾),两首真情毕现的诗,却长久不被研究家们理解。
《戏赠杜甫》一诗,因未编入唐人选本曾遭到洪迈、陈仅等人的误解,以为是“好事者所撰”,“定是伪作”。郭沫若、安旗、郁贤皓等先生力作辨误。细审此诗,绝非伪作,且是唱和之作,作于访范之后走出范十的村庄行经甑山(饭颗山)时。两首七绝正引伸出一段李杜交谊的掌故。兖州的甑山,即李杜相逢作诗的饭颗山。对此,樊英民先生与余都曾据《滋阳县乡土志》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多方考证,撰述为文。
弄清作诗的时间,便不难解读这首诗。两人从范氏庄返归鲁城,谈话仍兼戏谑,李白口占一诗:
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
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有感于此诗,杜甫以《赠李白》作答:
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杜甫访范诗以“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开头。将南朝诗人阴铿比拟李白。李白便讥杜甫以“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因此,杜甫放言谓李白飘泊无定、愧对葛洪、空度时光、“飞扬跋扈”,似嫌过分之语,也正是两人交情笃厚的见证。其间夜同眠,日同行,长时相聚,亲如兄弟,这两首兼带戏谑的诗的产生,有着深厚的感情基础。
以“痛饮狂歌”“飞扬跋扈”写李白,以“作诗苦”写杜甫,道出各自的特征,皆极真切。此二绝,真情毕现之外,可窥得人物个性、形象、语言。确是重要的作品。唐人未选入集,大概因诗句率意之故。
李白杜甫在“日静无云”的秋天郊游,是“酸枣垂北郭,寒瓜蔓东篱”的收获季节。“秋来相顾”,人世浮沉。四十多岁的李白,渐入人生之秋。“我觉秋兴逸,谁云秋兴悲”?诗人心上的秋是璀灿的。从入京到还山是他生活和创作道路上前后期的分野,历经波折,作用于他的精神和作品。在《李白集》中,五分之四以上且多重大题材之作完成于后期。
杜甫从青年时代初游齐鲁,到天宝初年最后离鲁西行,他的《壮游》诗中有“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一语,“快意”者,因慢游、因省亲,尤在于与李白相聚。
在王瑶著《李白》和安旗著《李白传》两部书中,皆指出杜甫诗《赠李白》写在访范之时,那末,李白的唱和之作《戏赠杜甫》的写作时地便无疑议。
安旗《李白传》中写道:
临别时,范十请他们赋诗留念,李白写了一首《寻鲁城北范居士》,杜甫写了一首《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
杜甫和李白也要分手了,李白在尧祠石门给杜甫钱行。
他们共同感到都像飘风中的飞蓬……功业不成,丹砂未就,痛饮狂歌,视富贵如浮云把王候当粪土,只图快意一时而己。于是杜甫口占《赠李白》(秋来相顾)一诗。
两人此别,不知何日再能相聚?且对着这石门秋光,再饮几杯鲁酒。李白信口吟成《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一诗。
鲁城北访范十与石门饯别的时间相接,同在天宝四载秋天。如果说“醉别复几日”意指在范十家中畅饮。那末,“登临遍池台”句,当也含漫步饭颗山(甑山),唱和吟诗的情景。
后人注意到杜甫赠李白诗多至十五首,还有与李白有关的诗,合起来近二十首。以为李白为杜甫写的诗则甚少,(《李白大辞典》指出仅有《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沙丘城下寄杜甫》和《戏赠杜甫》三首),似乎杜甫更重情谊。这倒有些冤枉了李白,窃以为李白赠杜诗,有的未被识出,如《送友人》: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弧蓬万里征。
浮去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握别友人,诗人置身空旷的郊野。挚友乍分,依依难舍。生活动荡,前路茫茫,望长空,浮去落日也带有眷恋之情——到底与谁握别,令诗人如此惆怅!
前人论及此诗,多偏重赏读,少见有人研究考证,因为诗中仅写送客,写惜别,对于写作时间、地点,几成难解之谜。《李诗选注》谓“此诗但云送友人,不知为谁?而北郭、东城,不知为何地?”《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谓:“此诗创作时间、地址无考。”但也曾见有文章言及作诗地点,有南阳、宣城、金陵诸说,限于猜测,难得准确。近年始系此诗作于兖州,李白有家在此,方有送客活动,现存李白兖州送客诗近二十首,《送友人》是不容忽视的一首。送客地点多在城东尧祠一带,此地是水陆通衢,交通要冲,又多酒肆,便于宴饮饯别,加之景色宜人,易发诗兴。《送友人》亦写在尧祠前泗水边的石门路上。北望二十公里处九仙山嶂列,合“青山横北郭”。泗水从曲阜向西流来,入兖州境即转向南,又朝西南流,是谓“白水绕东城。”李白东鲁作品,写过这片原野上的浮云,写过这里西下的落日。鲁郡尧祠送别窦明府诗中“山光水色青于蓝,”与此诗首联意近。诗中班马,即《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诗中“送行驻金羁,歇鞍憩古木”的那匹马。送窦明府诗中“朝策犁眉(WO),举鞭力不堪”,写策马从鲁门东沙丘旁中至相距三里的尧祠,这是从李白家中到尧祠的往返之路。在相近的时间里,仍然是这匹马,送友人出走后,与孤独的诗人为伴。
李白东鲁送客诗,皆言被送行人,《送友人》别具一格。拙作《再谈李白寓家东鲁》(《中国李白研究》)95、96年集)中论及此诗作于兖州后,指出或为另一道送客诗的续作。因太白诗“十丧其九”,正篇何诗?一时不敢探究。
一旦著意于李白诗《戏赠杜甫》的写作地点,复诵此诗,诗中“孤蓬万里征”的“蓬”字,颇具冲击力,便与鲁郡东石门送杜甫诗中“飞蓬各自远 ”句,与杜甫《赠李白》首句“秋来相顾尚飘蓬”相联系,将蓬的意象,引伸思考,这首诗显然与杜甫有关。
李白由入京到还山,历经重大挫折,心情悒愤,感慨万千,上下求索,前路迷茫。故杜诗谓“秋来相顾尚飘蓬”。不久,杜甫离鲁远行,两人在鲁郡东石门分别,李白送杜诗有“飞蓬各自远”句,《送友人》中又有“弧蓬万里征”,“蓬”字的复出,可见重要。在两人频繁相处,形影相随,心事重重之时,“飘蓬”二字。极具分量。
萧涤非《杜甫诗注》注《赠李白》诗中“相顾”二字“见得彼此一样,时二人都流浪山东,故以飘蓬为比。”安旗先生深知李杜,大著《李白传》中写及石门饯别,有“他们共同感到都像飘风中的飞蓬,不知何处是安身立命之所?”陈贻欣先生注意到这个“蓬”字,所著《杜甫评传》第十四章以“转蓬”二字作题。从这“蓬”字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提供了推断《送友人》的写作时地和所送友人的依据。
这首诗,有交谊情深的背景,这“蓬”字,用于其时,意蕴深邃。细味《送友人》一诗,通篇情感,皆缘于送别杜甫。“此去尔勿言,甘心如转蓬。”(《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李白初到兖州,就曾作如此表白,为实现思想,甘心于如同飘转的蓬草,浪迹四方。
《送友人》与《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为同时作,是篇续作,正篇诗题上己有“送杜二甫”,续作便径写“送友人”三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皆以此诗似为别友人之作。前有送诗,继写别诗,二者关联,诗意延伸。
细审两人的往来诗,足见相处时久,相知良深。李杜相聚,决不限于天宝三载遇于梁宋到翌年秋在石门分别这一年多时光,更早于此时的聚会却向为研究家们忽落。
据新说,李白与杜甫初聚,最迟在开元二十四年,时李白初居兖州,杜甫省亲居住其父杜闲的官舍,两人都有同期作于兖州的作品。研究这些作品系年,因知同在东鲁。自“行歌泗水春”,相伴漫步在鲁门东泗水畔。以后,聚会渐频,友情递增。李诗《寻鲁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和《戏赠杜甫》;杜诗《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和《赠李白》是两人兖州相聚的后期作品,李白在送杜诗中与出异出其他尧祠送客诗的新切情怀。《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写举杯握别,《送友人》写杜甫刚刚离去,《沙丘城下寄杜甫》写思念。三首诗中感情脉络相合,可视为组诗。以“李白一斗诗百篇。”“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等句,可见杜甫之推崇钦敬李白。白诗“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句,可见思念杜甫之切。《送友人》诗中情愫,系因与挚友分别,从诗人遥望长空挥手惜别的神态,可以推想所送友人的形象。“落日故人情”,这“故人”是谁?是一起月下泛舟之伴,是共同狩猎孟渚之友,是同游齐州的故交,是携手同行漫步甑山的弟兄,即几天前共饮于范氏家中的杜甫。“登临遍池台”一个“遍”字,写出相聚频繁。于今落日时分,分别在石门路上,不由举手劳劳,两情依依,一再赋诗。杜甫《梦李白二首》其一有“故有入我梦”句,当是石门宴请景再现梦中。如此一再互称故人,其意颇耐寻味。
《送友人》一诗,为杜甫所重,作《梦李白二首》,其二以“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开头,显系化“浮云游子意”而成。杜甫思念李白,也怀念东鲁,怀念北郭的青山、东城的白水。
题材相近的同时之作,参照阅读,往往能得深层发现,例如将李白《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与《梦游天姥吟留别》互参,可见情绪升华和语言形象提炼。李诗《戏赠杜甫》与杜诗《赠本白》互参,可为唱和诗,可见情谊,并推知写作时地。今试将《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和《送友人》连在一起解读。
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
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
[背景]:时在天宝四载秋,杜甫将离兖州,有意与李白多番接触。两人同去鲁城北范居士家中造坊,到尘嚣之外的北方农村,呼吸清新的空气,主人热情相待,酣饮畅叙,醉眠共被,戏谑赠诗。几天以后,杜甫西行,两人在古门握别。
[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醉别方过几日,曾经一同漫步尧祠、甑山,踏遍东鲁池台。今日分手,期冀来日再会于石门路上。望泗水秋波,想起竹溪六逸共隐徂徕的日子。眼前,水上蓬草转动,人也在飘泊中。在行将踏上遥远的旅程之际,再次举杯畅饮,寄深情于酒中。
[送友人]:稍顷,杜甫已经远去,诗人静立原地。张望几天前同游的村庄,村子前是漫步、作诗的山岭。更远外,青山如障,横列在鲁城北郭。时光如流,相聚难得,只有环绕东城的泗水,漫流不息。此别,如飞蓬飘泊万里。天空中浮云、落日,也依依留连,好像理解离人的心境。再次举手相招,遥祝一路顺风。善解人意的班马,萧萧长鸣。
最为熟悉的两首李白东鲁作品,不意其意密切关联,是颇有情趣的。
姑略谈《雪谗诗赠友人》一诗。这是一首存在争议的四言诗。诗中所斥责的妇人是谁?向有二说:其一,认为斥杨妃*乱误国。洪迈《容斋随笔》、刘克庄《后村诗话》、赵翼《瓯北诗话》、詹钅英《李白诗文系年》、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等皆持此说。或认为斥夫人刘氏,郭沫若倡此说,谓“刘氏与李白离异后,曾向李白友人处播弄事非,故雪谗自辩”(《李白与杜甫》)。当以前说为是,则约作于去朝还山后的天宝四载。前人据“五十知非”句系年,恐非。“五十知非”系出自《淮南子》“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句,而非太白作诗之年。
安旗谓“(作雪谗诗)时白或遭祸,因向友人抒其觉沉忧”(《李白全集编年注释》)。
杜甫最崇敬李白,也深为了解和关心李白,对其入京、还山,知情最多,在洛阳相遇时便备述其事。杜甫谓白“脱身事幽讨”,“兼全宠辱身”。这类话题尤其在访范十时谈论最多,杜甫听腻了,便以“不愿论簪笏”作阻,或以屈原遭放逐相劝慰,有“向来吟《桔颂》”句可证。“屈原憔悴滞江潭”。此时李白的心情,确也正像流放中沉吟于泽畔的屈原。因“失往路”而“遂为苍耳欺”,于今“不惜翠云袭”,毅然辞京还家,“远为千载期”,“风流自簸荡”。放远目光,振奋精神,萌发“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之思,此与雪谗诗中之“立言补过,庶存不朽”旨意承接。此诗以“嗟余沉迷,猖狂已久”开头,与杜甫诗中“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相接。兼及“五十知非,古人常有”句,可见他乐于倾听规劝。
《雪谗诗赠友人》作为纵谈遭谗经历之时,当赠给最为关心和熟知内情的人。因此便有了这首以雪谗为内容的赠诗。
在朝遭谗被疏以致罹祸,以雪谗诗表述“心切理真”。此时,“谁察余之贞坚”?唯有“离娄自明”,“善听”(均此诗中句)以昭太白忠诚的杜甫。
《雪谗诗赠友人》可与《惧谗》一诗相参阅。谗言可畏,向谁雪谗?是向最关心他的人。诗赠予谁?显系杜甫。旨在抒愤,故诗题不著友人姓氏。初读此诗,略述浅见,聊备一说。
《秋日鲁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此诗题郭沫若释为“宴别杜甫兼示范侍御”,侍御其人,即辞京还乡隐居鲁城北的范十。并指出”兼示”二字,抄本适缺,注以“阙”字。后将“甫”作“补”,后窜入正文。范氏不是宴别对象,故曰“兼示”。最早谓此诗为送别杜甫的是唐人段成式,他见到有个本子上“杜补阙”作“杜考功”,便指出这是杜甫。据诗意,至今尚难于认定此说之准确与否?却不妨将诗中情景,视为送杜:
我觉秋兴逸,谁云秋兴悲?山将落日去,水与晴空宜。
鲁酒白玉壶,送行驻金羁。歇鞍憩古木,解带挂横枝。
歌鼓川上亭,曲度神飙吹。云归碧海夕,雁没青天时。
相失各万里,茫然空尔思。
送客地点同在尧祠、石门,时间亦是秋季,同为日落时分。“相失各万里”,行程也与杜甫西去咸阳契合。这句诗与《送友人》中“孤蓬万里征”,与《鲁郡东石门送杜甫》中“飞蓬各自远,”三者相合,足见关联。杜甫曾向范十说过出行之日,事先有约,故赶来参与宴别。此诗如确为送杜,那末,三诗作于同时。郭沫若的发现,可资深入研究。
《沙丘城下寄杜甫》,是李白怀杜诗最为著名的一首,是很重要的一首。通常系为天宝五载作于东鲁兖州:
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
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李白居东鲁沙丘家中,夕阳西下时,思念起远行之后的杜甫,心潮如汶水浩荡,便以诗寄情。据诗题中“沙丘城下”,诗中,“高卧沙丘城”,可确知李白东鲁家居之地。另外在《送萧三十一之鲁中兼问雅子伯禽》诗中中“我家寄在沙丘旁”,并参以“我家寄东鲁”(《寄东鲁二稚子》),“二子鲁门东”(《送扬燕之东鲁》)句,其居家地点,所言甚明。唯前人不知此沙丘在兖州,而迷茫千载。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书中《沙丘城下寄杜甫》题解“沙丘指兖州(鲁郡)治城瑕丘。《兖州府志》‘沙丘在东门外二里’,杜甫时在长安”。正当研究学者著意李白东鲁寓家地之时,1993年兖州出土《北齐河清三年造像》刻石,上有“岁次实沉于沙丘东城之内”句,确证兖州沙丘的存在。沙丘之谜,始得冰释。以往认为李白家在任城,实误。任城有“李白尝醉于此”沈光《李白酒楼记》的酒楼,只是他曾多次借居的贺兰氏的酒楼。以沙丘城代指兖州县城,亦见于初唐骆宾王的文章,这是唐代人所熟知的代称。
诗中以古树、秋声喻诗人孤寂,以鲁酒齐歌写思念之苦。又见石门秋波,将思念之情寄予南征的汶水,写来情深意切。
李白关于杜甫的诗有《戏赠杜甫》、《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沙丘城下寄杜甫》,加之《送友人》和另外两人同游时所作的几首,这位年长十一年的兄长,所作也甚可观。尤难得诗中寄以深情。
杜甫离鲁城到长安,“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悲辛不堪,愈加思念李白,悔于没有更多时光同在一起。严冬时,“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作《冬日有怀李白》。在《春日有怀李白》中,以“白也诗无敌”评价李白,期望再见,“重与细论文”。孔巢父谢病归江东,杜甫请他到禹穴寻李白,转致问候。因入永王李lin幕中,李白蒙冤,杜甫尤其关心,写诗深表不平。思念之切,以致“三夜频梦君”。作于李白暮年时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被视为诗体小传。
李白“济苍生,安社稷”。“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之志,与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人生愿望契合。其创作影响杜甫,其少任侠、重义气、乐于助人的高尚品格,感召杜甫。对人生、对诗歌艺术,两人的心灵上多有相通之处。诗中两曜相互尊敬,友谊诚挚,对诗的缪恋,将两颗伟大的心连在一起。
李白“一生低着谢宣城”(王士祯《论诗绝句》)锤情于谢。杜甫则尤其痴情于李白,且愈到晚岁,愈加深切。
李白杜甫聚会地点有梁宋、单父、兖州、济南等地,其初遇和最后分别却在兖州,在兖州相聚时间最久。李白赠杜诗,均作于兖州,关于李杜交谊,兖州是最为重要的地方。
杜甫青年时代游齐赵,至东鲁,写出名篇《登兖州城楼》,诗中“东郡趋庭日,南楼纵目初。”道出了此行之目的,从此开阔了视野。到最后离鲁之前,有感于“山东李白”之称,自谓“余亦东蒙客”,与李白之称东鲁兖州沙丘为“家”、为“乡”、为“故园”、“故巢”有所区别。从这些词语,可见诗仙、诗圣与这方水土的深厚情缘。
李杜交谊历来为文学史家称道。闻一多先生在《杜甫》一文中盛赞两曜相聚:
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起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我们再逼紧我们的想象,譬如说,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那么,尘世上不知要焚起多少香案,不知有多少人要望天遥拜,说是皇天的祥瑞。如今李白和杜甫一诗中的两曜,劈面走来了,我们看去,不比那天空的异端一样的神奇,一样有重大意义吗?
高适
塞下曲
结束浮云骏,翩翩出从戎。且凭天子怒,复倚将军雄。万鼓雷殷地,千旗火生风。日轮驻霜戈,月魄悬雕弓。青海阵云匝,黑山兵气冲。战酣太白高,战罢旄头空。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
高适(702~765),字达夫,渤海蓚县(今河北景县)人。晚年曾任左散骑常侍,后世因称为高常侍。二十岁左右游长安求仕不果,此后长期客居宋州宋城(今河南商丘)。开元十八年左右,北游燕赵,且于燕地从军。开元二十三年曾赴长安应试不中。天宝八载因睢阳太守张九皋荐,登有道科,授封丘尉。天宝十三载入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幕府充掌书记。安史乱起,先后任左拾遗、淮南节度使、太子少詹事、彭州刺史、蜀州刺史、剑南西川节度使等职。广德二年被召还长安,任刑部侍郎,转左散骑常侍,进封渤海县侯。次年正月卒于长安,赠礼部尚书,谥忠。
汉乐府有《出塞曲》、《入塞曲》,唐人《塞上曲》、《塞下曲》本此。高适此诗虽为乐府旧题,却通过对浴血沙场的勇士形象的塑造,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开篇四句写跨马从戎,次八句写战阵的壮阔,后八句写安边定远的壮志,人物的生动形象与精神状态跃然纸上。特别是结尾处以“古人昧此道”表现出对皓首穷一经的腐儒的嘲笑,一语道破唐代文人由边功求进取的崭新的时代风气。而这显然正是高适本人的心声,这首诗中塑造的人物形象也就可以看作高适本人人生理想的写照。
效古赠崔二
十月河洲时,一看有归思。风飙生惨烈,雨雪暗天地。我辈今胡为,浩哉迷所至。缅怀当途者,济济居声位。邈然在云霄,宁肯更沦踬。周旋多燕乐,门馆列车骑。美人芙蓉姿,狭室兰麝气。金炉陈兽炭,谈笑正得意。岂论草泽中,有此枯槁士。我惭经济策,久欲甘弃置。君负纵横才,如何尚憔悴。长歌增郁怏,对酒不能醉。穷达自有时,夫子莫下泪。
此诗作于两次求仕不成之后,故借与崔二赠答之际,深刻揭露当时统治阶级的骄奢*逸,尽情抒发沉沦不遇的满腔悲慨。开篇六句,以景托情,渲染出充塞天地的悲愁氛围。次十二句以“缅怀”引出“当途者”,详细描绘权贵们骄矜生活,并以草泽枯槁之士与之作强烈对比,促生愤慨。后八句倾诉胸中不平,并以“我”与“君”的对比扣合诗题。诗写悲愁,却毫不消沉,而是峰峦迭起、波澜层生,充满激昂顿挫之势与强烈的情感力度,构成贤人失志主题在开元盛世中的典型表现。
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
自从别京华,我心乃萧索。十年守章句,万事空寥落。北上登蓟门,茫茫见沙漠。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拂衣去燕赵,驱马怅不乐。天长沧洲路,日暮邯郸郭。酒肆或淹留,渔潭屡栖泊。独行备艰险,所见穷善恶。永愿拯刍荛,孰云干鼎镬。皇情念淳古,时俗何浮薄。理道资任贤,安人在求瘼。故交负灵奇,逸气抱謇谔。隐轸经济具,纵横建安作。才望忽先鸣,风期无宿诺。飘飖劳州县,迢递限言谑。东驰眇贝丘,西顾弥虢略。淇水徒自流,浮云不堪托。吾谋适可用,天路岂寥廓。不然买山田,一身与耕凿。且欲同鹪鹩,焉能志鸿鹄。
此诗借与薛据、郭微酬赠之机,叙述了自身的经历、情操及创作趣尚,可以视为高适前半生人生的自我总结,后半生行为的思想基础。开篇至“安人在求瘼”为第一部分,自述早年经历、思想及政治主张。卫霍,指汉代名将卫青、霍去病,用以表明自己建功立业的理想。鼎镬,是古代施行烹煮酷刑的容器,这里代指酷政。“故交负灵奇”以下为第二部分,由己及人,既扣合酬赠之题,又通过对薛、郭二人“飘飖”州县的叹惜,抒发出自身强烈的不平之鸣。贝丘、虢略,都是地名,分别在今山东博兴南、河南嵩县西北,这里代指东、西飘飖之地。全诗既有大笔勾勒,又有细致描述,语言质朴自然,却具有震撼人心的情感力度。
登百丈峰
朝登百丈峰,遥望燕支道。汉垒青冥间,胡天白如扫。忆昔霍将军,连年此征讨。匈奴终不灭,寒山徒草草。唯见鸿雁飞,令人伤怀抱。
此诗作于赴陇历哥舒翰幕府途中。在此之前,高适曾两度求仕未果,因而此诗仍带有较强的忧伤意绪。前四句写登高望远,目光直指河西边塞,并以“汉垒”置“胡天”之间,见边防之紧。燕支,即燕支山,又作焉支山,在今甘肃永昌西。中四句联想自汉代以来连年征战而匈奴不灭的绵长历史,见社稷之忧。末二句顺势而出,抒发怀抱。此诗虽写忧虑之意,但却将一己之怀抱与边塞安危联系起来,从而表现出一种忧天下之忧的阔大襟怀气度。
蓟中作
策马自沙漠,长驱登塞垣。边城何萧条,白日黄云昏。一到征战处,每愁胡虏翻。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
此诗是高适第二次出塞到蓟北时所作。由边塞的荒凉生发出对边患的忧虑,并抨击统治者用非其人,抒发自身难酬之壮志。开篇以“沙漠”、“塞垣”构定塞外特定环境,三、四句写登上塞垣所见一片萧条荒漠景象,五、六句以“征战”与“胡虏”对举,既见对胡虏反叛之忧患,更显对边将黩武邀功的批判。后四句直抒怀才不遇之愤懑。孙吴,指战国时军事家孙膑、吴起。全诗语言质朴平淡,但由于纪录了当时边塞实况,且写景壮阔,情怀激烈,仍具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其九)
朝从北岸来,泊船南河浒。试共野人言,深觉农夫苦。去秋虽薄熟,今夏犹未雨。耕耘日勤劳,租税兼舄卤。园蔬空寥落,产业不足数。尚有献芹心,无因见明主。
此题为途中纪实之作,本诗原列该组诗的第九首。前四句写行程路线及最突出感受,自北而南,满目情形大体相似,可见“农夫苦”已成普遍现象。中六句具体描述农夫之苦况,除日日劬劳之外,再加天旱、租税之双重灾难,无所收获也就是必然的了。末二句自抒怀抱,虽有良策拯民,却无由上达,于无奈中显出强烈的民胞精神与失志之愤。高适此诗作于开元年间,却能于盛世背后发现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样的题材,在盛唐诗人中大约以此篇为最早。
登陇
陇头远行客,陇上分流水。流水无尽期,行人未云已。浅才登一命,孤剑通万里。岂不思故乡,从来感知己。
此诗是高适赴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途中登陇山有感而作。前四句以陇上流水意象表达独身远行的心理感受。流水、行人,既是写实,又构成象征性的互喻关系。后四句抒发此行意欲有所作为、建立功业之壮志。“浅才一命”、“孤剑万里”,活画出慷慨任侠的形象;只身远游,固生乡思,然更感知己,足见报效国家之豪情。此诗语言简洁,但却包容着丰富内容,既思故乡,又感知遇,既叹身世飘泊,又表报国壮志,所谓“感知忘家,语简意足”(《唐诗别裁集》),写足孤身远游、求取功业之意。
古大梁行
古城莽苍饶荆榛,驱马荒城愁杀人。魏王宫观尽禾黍,信陵宾客随灰尘。忆昨雄都旧朝市,轩车照耀歌钟起。军容带甲三十万,国步连营一千里。全盛须臾哪可论,高台曲池无复存。遗墟但见狐狸迹,古地空余草木根。暮天摇落伤怀抱,抚剑悲歌对秋草。侠客犹传朱亥名,行人尚识夷门道。白璧黄金万户侯,宝刀骏马填山丘。年代凄凉不可问,往来唯有水东流。
此诗作于与李白、杜甫同游大梁之时。其时高适隐居宋中,求仕无门,即于这首咏怀古迹之作中,透露出悲凉的身世之感。全诗四句一转韵,分为五个自然段落。第一段写驱马荒城所见景象,第二段引出对往昔的遥想,第三段回到眼前,回应首段,第四段紧接,写出当年风云人物的遗迹,第五段感叹当时受赏的朱亥、侯嬴荣耀一时,终成过客,如今只有汴水东流而已,既生兴亡之慨,又将古今一脉贯穿,从而使兴亡之叹融入自己身世之感。此诗情感浓烈,思绪曲折,章法整饬,表现自然。
邯郸少年行
邯郸城南游侠子,自矜生长邯郸里。千场纵博家仍富,几度报仇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纷纷,门外车马常如云。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君不见即今交态薄,黄金用尽还疏索。以兹感叹辞旧游,更于时事无所求。且与少年饮美酒,往来射猎西山头。
此诗是高适青年时代作品,诗中描述的“邯郸少年”可以视为诗人之自况,借以表达内心的愤世之慨与任侠豪情。邯郸,是战国时赵国都城,即今河北邯郸。诗的前六句写“游侠子”生长之地与侠义轻财之举,其豪爽英姿与狂放气派跃然纸上。七、八句陡然转折,写侠肝义胆无人理解,报国宏图无从实现,只有空空怀念古代“倾以待士”的平原君。后六句即直写当今世俗人情之菲薄,表现出睥睨尘世、刚直耿介的性情节操。此诗章法齐整,意态飞动,当时即被“朝野通赏”(《河岳英灵集》),极亨盛誉。
燕歌行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据此诗前原有小序可知作于开元二十六年。高适从军燕地在开元十八年至二十一年间,此诗是离开边塞之后“感征戍之事”并回顾自身边塞经历之作。诗中充分展示了复杂的心理状态,既表达立功边塞的豪情壮志,又对边塞局势与用兵情状提出见解,因此,一方面对战士忠勇报国精神热情颂扬,另一方面又对将领奢靡生活强烈不满,并由此发出对蒙受战争痛苦的家庭的深切同情,乃至于对边将用非其人的讥讽嘲弄。全诗内容丰富,包含着对边塞情势较长时期的见闻感受,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与概括力度。此诗不仅是高适的名篇,而且堪称整个唐代边塞诗之杰作。
人日寄杜二拾遗
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身在远藩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
此诗是高适在蜀州刺史任上寄怀杜甫之作。人日,是农历正月初七日。杜二,即杜甫。杜甫居成都时,高适与之过从甚密,此诗慰故人思乡之情,发世事难料之叹,抒无所作为之憾。全诗四句一层。首四句寄慰杜甫,“思故乡”既是言杜,亦是自谓,二人故乡同为当时正在战乱的中原,这一“思”便将二人情感更加紧密地联结起来。次四句写自身,既“无所预”又“复千虑”,表白忧国情怀,“空相忆”、“知何处”,则添一层无奈与落寞之感。末四句进而将自己庸碌自适与友人飘泊四方比照,逗出“愧”意,回应篇首,写足题意。
送浑将军出塞
将军族贵兵且强,汉家已是浑邪王。子孙相继在朝野,至今部曲燕支下。控弦尽用阴山儿,登阵常骑大宛马。银鞍玉勒绣蝥弧,每逐嫖姚破骨都。李广从来先将士,卫青未肯学孙吴。传有沙场千万骑,昨日边庭羽书至。城头画角三四声,匣里宝刀昼夜鸣。意气能甘万里去,辛勤动作一年行。黄云白草无前后,朝建旌旄夕刁斗。塞上应多侠少年,关西不见春杨柳。从军借问所从谁,击剑酣歌当此时。远别无轻绕朝策,平戎早寄仲宣诗。
此诗作于已入哥舒翰幕府之时。浑将军即哥舒翰麾下之云麾将军浑惟明,其祖先乃汉代匈奴浑邪王。此诗通过送浑将军出塞,塑造出一个勇猛爱国、光彩夺目的将军形象,成为边塞诗中写人物的代表作。开篇十句写浑将军的祖先、部曲传统及其身先士卒的品质、威名赫赫的战功。蝥弧,指军旗。嫖姚,指汉代嫖姚校尉霍去病,这里喻指主将哥舒翰。骨都,指匈奴左右骨都使。次十句进而写浑将军在边境形势危急时奋不顾身、转战南北的具体行态,使其形象更加神充气足。最后四句点明“送”之题,并寄托自己的殷切期望,预祝其早奏凯歌。绕朝策,指秦大夫绕朝曾赠人马鞭,这里比喻破敌之计策谋略。仲宣诗,指王粲《从军诗》,这里比喻捷报。此诗铺绘壮美,极见盛唐气象,同时也表现出诗人自身壮伟的精神面貌与豪放的艺术风格。
封丘作
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归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笑今如此。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付与东流水。梦想旧山安在哉,为衔君命且迟回。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
高适近五十岁时才因张九皋的推荐而中有道科,然却仅得封丘尉之低职,此诗即作于封丘尉任上,抒发了失望与矛盾的心态。首四句以超脱世俗的姿态自表品格,见不堪作吏的原因。孟诸,是古泽薮名,在今河南商丘东北,这里泛指梁宋一带。次四句进而写不堪吏务的实情。复四句语意转折,由家人之不解见自身与世俗之龃龉之深。末四句明揭归隐之念,与篇首遥相照应。梅福,是汉代南昌尉,曾屡次上书,皆不被采纳。全篇四句一转韵,且皆前二句散行,后二句骈俪,经纬成文,回环往复,结构颇见匠心。而情感强烈,奔泻而出,既见跌宕之势,更显雄强伟力。
别韦参军
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国风冲融迈三五,朝廷礼乐弥寰宇。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归来洛阳无负郭,东过梁宋非吾土。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世人遇我同众人,唯君于我最相亲。且喜百年见交态,未尝一日辞家贫。弹棋击筑白日晚,纵酒高歌杨柳春。欢娱未尽分散去,使我惆怅惊心神。丈夫不作儿女别,临歧涕泪沾衣巾。
此诗作于求仕未得之时,诗借赠别之机抒失意怀抱。前十二句自叙入京求仕、落拓失意、客游梁宋的经历,先写壮伟襟抱,次讽朝政昏聩,再写客游梁宋,失意之情充溢字里行间。三五,指三皇五帝,这里喻指理想的政治。负郭,指近郊良田。后十句写与韦参军友谊及惜别之情,于众人中拈出“唯君”,见知己之感,欢娱交密,却又不得不离别,尤增惆怅,而临别之时,又以劝慰作结,足见诗人虽怨尤却不消沉,充满对前程的期待与希望。诗中暗用姜太公“垂钓”故事,可见非凡抱负。
部落曲
蕃军傍塞游,代马喷风秋。老将垂金甲,阏支着锦裘。雕戈蒙豹尾,红旆插狼头。日暮天山下,鸣笳汉使愁。
此诗作于初至哥舒翰幕府之时,表现出对边事的关切与忧虑。首联概写“蕃军”兵强马壮、意气骄横情势。颔联以“垂金甲”与“着锦裘”之具体形象写出蕃军将帅略无顾忌、首领安闲自得神情。颈联以“雕戈”、“红旆”写出蕃军兵器之锐利与军阵之齐整。尾联直点汉使之愁,并以“日暮”、“鸣笳”渲染出塞外苍凉氛围,诗之主旨至此毕现,而前六句的铺述亦至此而见其作意所在。
送李侍御赴安西
行子对飞蓬,金鞭指铁骢。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虏障燕支北,秦城太白东。离魂莫惆怅,看取宝刀雄。
此诗为送人出塞从军之作,充满亟欲立功异域的慷慨豪情,且气势纵横,音韵铿锵,曾被后人誉为“盛唐五言律第一”(许学夷《诗源辩体》)。开篇以“飞蓬”喻“行子”,虽为传统习惯,但其将之与“铁骢”、“金鞭”联结起来,即造成一种异乎寻常的力度。颔联写送别,但在“一杯”之中却涵纳“功名万里”之“心事”,这就使功业之志超越了惜别之情。颈联荡开,写出离别之地及友人将去之地,既是写实,亦是托情。尾联先以“莫惆怅”相劝慰,复以“宝刀雄”相激励,塑就一幅壮士别离的英伟形象,以人物回应篇首,以气势贯穿全篇。
使青夷军入居庸三首(其一)
匹马行将久,征途去转难。不知边地别,只讶客衣单。溪冷泉声苦,山空木叶干。莫言关塞极,云雪尚漫漫。
高适于天宝九载秋以封丘尉送兵往青夷军,此诗是返回途中入居庸关时所作。诗写行役之艰难与边地之苦寒。首联概写行役时久,去、返皆难,以下皆承“难”而出。颔联以惊讶衣单写出“边地别”的最突出感受,将“难”具体集中于此,不言寒而已觉寒气逼人。颈联写水冷、木落,从听觉、视觉两方面进而渲染寒的环境氛围,暗言其范围之广大。尾联即明言虽关塞已尽,然寒冷征途仍甚迢遥,回应开篇之征途。作为边塞之作,此诗不写战争,亦不写异域风光,而是撷取“寒”这一独特角度,透现边塞苍凉意味。
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
嗟君此别意何如,驻马衔杯问谪居。巫峡啼猿数行泪,衡阳归雁几封书。青枫江上秋天远,白帝城边古木疏。圣代即今多雨露,暂时分手莫踌躇。
此诗送李、王二少府分赴两地,皆为谪贬,且高适时任封丘尉,亦正失意,所以这首送别诗就显得内容较为丰富,情谊尤感挚厚。首联先以询问领起,牵出谪贬送别的特殊情境。中二联针对李、王二人贬谪之地,想象僻地荒寒环境,既写景,又寄情。七、八句以劝慰作结,同时揭示出积极进取的抱负与信心。此诗中连用四地名,本为律诗之忌,但由于情意真挚,气势健举,所以并不感到窒碍。
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
遥传副丞相,昨日破西蕃。作气群山动,扬军大旆翻。奇兵邀转战,连弩绝归奔。泉喷诸戎血,风驱死虏魂。头飞攒万戟,面缚聚辕门。鬼哭黄埃暮,天愁白日昏。石城与岩险,铁骑皆云屯。长策一言决,高踪百代存。威棱慑沙漠,忠义感乾坤。老将黯无色,儒生安敢论。解围凭庙算,止杀报君恩。唯有关河渺,苍茫空树墩。
高适任职哥舒翰幕府期间,随着边塞形势的转变,其对边事的忧虑情绪亦逐渐淡褪,而代之以胜利的喜悦与热烈的颂扬,此诗即作于哥舒翰大破九曲之后。此诗以排律的形式,对哥舒翰军威、破敌、谋略、忠心尽力铺排,热烈颂扬其雄武英姿与安边功业。对于破九曲之事,高适还有《九曲词三首》等作,同样展示了安边定国的光明前景与个人博取功名的饱满信心,可见这一事件对高适人生、思想实具重要影响。
送兵到蓟北
积雪与天迥,屯军连塞愁。谁知此行迈,不为觅封侯。
此诗作于送兵至青夷军之时,高适时任封丘尉之卑职,诗中发抒的是郁郁不得志之情怀。前二句写积雪铺天、军阵连云的景象,塞外特征由此得到集中概括。一个“愁”字又奠定全诗基调。后二句即写自身远行边塞军中,却并不为建功业、觅封侯,显然是以反语抒激愤之情。这首小诗虽意在抒发愁怨意绪,但却充满情感力量,表达简洁明练,读来动人心魄。
营州歌
营州少年厌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
此诗作于高适首次出塞从军燕赵期间,写边地少年生活习惯与豪爽性格。首句将营州少年与原野联系起来,点明其特定生活环境。营州,在今辽宁朝阳。厌,同餍,饱意,这里引申为饱经、习惯意。二句写其出猎情景,“狐裘蒙茸”活画出营州少年生动形象。三句“千钟不醉”,见其豪放之习,四句“十岁骑马”,见其勇悍之性。全诗充满对营州少年的赞美之情。作此诗时,高适首次出塞,所以一见粗犷豪迈的边地少年,即引起本身就“不拘小节”、“隐迹博徒”的诗人的强烈钦羡。全诗笔墨粗放,充溢着浓郁的边塞情调。
塞上听吹笛
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
此诗写塞上闻笛而生乡关之思,但首先却展现出冰雪铺凝的广袤胡天,然后再在明月与戍楼之间托出羌笛之声,而笛声乃《梅花落》之曲,这样就在荒漠塞外与故乡春色的鲜明反差之中透露出缕缕乡思。但这乡思却略无哀怨,而是随着一夜风吹渗满整个关山,以可见的壮伟景观的实态体现出巨大的内在显现力与艺术包容力。
别董大二首(其一)
千里黄云白日昏,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这是一首送别之作,但从景物描写看,却无异于一首边塞诗。诗写惜别之情,首先展现的却是一幅苍莽壮阔的塞外风光画卷。在这样的壮伟景观氛围中托出心绪,表面上是以怀才挟技无往不适相劝慰,内质中则是一种豪壮气势伟力的体现,在艺术表现上以“妙在粗豪”(徐增《而庵说唐诗》)的特点而成为千古名篇。
听张立本女吟
危冠广袖楚宫妆,独步闲庭逐夜凉。自把玉钗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
此诗通过对歌女情态的生动描绘,创造出一种清雅空灵的意境,在高适诗中别具一格。首句写妆束,显其高贵,次句写行态,见其脱俗,三句写动作,以敲竹击节逗出下文。四句“清歌一曲”点题,并以“月如霜”渲染环境氛围,既回应“逐夜凉”,更构成对清歌一曲内涵的体味,使环境、歌境、心境融通一体,在描写与感受的妙合中生成诗境整体。
除夜作
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
此诗作于除夜旅途之中,抒发思乡之情。开篇即点明身在“旅馆”,以“寒灯”与“独”构定凄冷孤寂氛围,次句转入自身,直白凄然的内心世界,同时以“何事”二字为诗意的深入提供悬念与契机。三句写乡思,却言“故乡思千里”,包含有自己思念故乡亲人,而同时遥想故乡亲人思念千里之外的自己两重意蕴,是客心凄然的第一层原因。末句“明朝又一年”点除夜之题,而自顾已是霜鬓,明朝将又添白发,乡思之中更增岁月流驶、人生苦短之叹,是为凄然的第二层原因
塞下曲
结束浮云骏,翩翩出从戎。且凭天子怒,复倚将军雄。万鼓雷殷地,千旗火生风。日轮驻霜戈,月魄悬雕弓。青海阵云匝,黑山兵气冲。战酣太白高,战罢旄头空。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
高适(702~765),字达夫,渤海蓚县(今河北景县)人。晚年曾任左散骑常侍,后世因称为高常侍。二十岁左右游长安求仕不果,此后长期客居宋州宋城(今河南商丘)。开元十八年左右,北游燕赵,且于燕地从军。开元二十三年曾赴长安应试不中。天宝八载因睢阳太守张九皋荐,登有道科,授封丘尉。天宝十三载入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幕府充掌书记。安史乱起,先后任左拾遗、淮南节度使、太子少詹事、彭州刺史、蜀州刺史、剑南西川节度使等职。广德二年被召还长安,任刑部侍郎,转左散骑常侍,进封渤海县侯。次年正月卒于长安,赠礼部尚书,谥忠。
汉乐府有《出塞曲》、《入塞曲》,唐人《塞上曲》、《塞下曲》本此。高适此诗虽为乐府旧题,却通过对浴血沙场的勇士形象的塑造,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开篇四句写跨马从戎,次八句写战阵的壮阔,后八句写安边定远的壮志,人物的生动形象与精神状态跃然纸上。特别是结尾处以“古人昧此道”表现出对皓首穷一经的腐儒的嘲笑,一语道破唐代文人由边功求进取的崭新的时代风气。而这显然正是高适本人的心声,这首诗中塑造的人物形象也就可以看作高适本人人生理想的写照。
效古赠崔二
十月河洲时,一看有归思。风飙生惨烈,雨雪暗天地。我辈今胡为,浩哉迷所至。缅怀当途者,济济居声位。邈然在云霄,宁肯更沦踬。周旋多燕乐,门馆列车骑。美人芙蓉姿,狭室兰麝气。金炉陈兽炭,谈笑正得意。岂论草泽中,有此枯槁士。我惭经济策,久欲甘弃置。君负纵横才,如何尚憔悴。长歌增郁怏,对酒不能醉。穷达自有时,夫子莫下泪。
此诗作于两次求仕不成之后,故借与崔二赠答之际,深刻揭露当时统治阶级的骄奢*逸,尽情抒发沉沦不遇的满腔悲慨。开篇六句,以景托情,渲染出充塞天地的悲愁氛围。次十二句以“缅怀”引出“当途者”,详细描绘权贵们骄矜生活,并以草泽枯槁之士与之作强烈对比,促生愤慨。后八句倾诉胸中不平,并以“我”与“君”的对比扣合诗题。诗写悲愁,却毫不消沉,而是峰峦迭起、波澜层生,充满激昂顿挫之势与强烈的情感力度,构成贤人失志主题在开元盛世中的典型表现。
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
自从别京华,我心乃萧索。十年守章句,万事空寥落。北上登蓟门,茫茫见沙漠。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拂衣去燕赵,驱马怅不乐。天长沧洲路,日暮邯郸郭。酒肆或淹留,渔潭屡栖泊。独行备艰险,所见穷善恶。永愿拯刍荛,孰云干鼎镬。皇情念淳古,时俗何浮薄。理道资任贤,安人在求瘼。故交负灵奇,逸气抱謇谔。隐轸经济具,纵横建安作。才望忽先鸣,风期无宿诺。飘飖劳州县,迢递限言谑。东驰眇贝丘,西顾弥虢略。淇水徒自流,浮云不堪托。吾谋适可用,天路岂寥廓。不然买山田,一身与耕凿。且欲同鹪鹩,焉能志鸿鹄。
此诗借与薛据、郭微酬赠之机,叙述了自身的经历、情操及创作趣尚,可以视为高适前半生人生的自我总结,后半生行为的思想基础。开篇至“安人在求瘼”为第一部分,自述早年经历、思想及政治主张。卫霍,指汉代名将卫青、霍去病,用以表明自己建功立业的理想。鼎镬,是古代施行烹煮酷刑的容器,这里代指酷政。“故交负灵奇”以下为第二部分,由己及人,既扣合酬赠之题,又通过对薛、郭二人“飘飖”州县的叹惜,抒发出自身强烈的不平之鸣。贝丘、虢略,都是地名,分别在今山东博兴南、河南嵩县西北,这里代指东、西飘飖之地。全诗既有大笔勾勒,又有细致描述,语言质朴自然,却具有震撼人心的情感力度。
登百丈峰
朝登百丈峰,遥望燕支道。汉垒青冥间,胡天白如扫。忆昔霍将军,连年此征讨。匈奴终不灭,寒山徒草草。唯见鸿雁飞,令人伤怀抱。
此诗作于赴陇历哥舒翰幕府途中。在此之前,高适曾两度求仕未果,因而此诗仍带有较强的忧伤意绪。前四句写登高望远,目光直指河西边塞,并以“汉垒”置“胡天”之间,见边防之紧。燕支,即燕支山,又作焉支山,在今甘肃永昌西。中四句联想自汉代以来连年征战而匈奴不灭的绵长历史,见社稷之忧。末二句顺势而出,抒发怀抱。此诗虽写忧虑之意,但却将一己之怀抱与边塞安危联系起来,从而表现出一种忧天下之忧的阔大襟怀气度。
蓟中作
策马自沙漠,长驱登塞垣。边城何萧条,白日黄云昏。一到征战处,每愁胡虏翻。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
此诗是高适第二次出塞到蓟北时所作。由边塞的荒凉生发出对边患的忧虑,并抨击统治者用非其人,抒发自身难酬之壮志。开篇以“沙漠”、“塞垣”构定塞外特定环境,三、四句写登上塞垣所见一片萧条荒漠景象,五、六句以“征战”与“胡虏”对举,既见对胡虏反叛之忧患,更显对边将黩武邀功的批判。后四句直抒怀才不遇之愤懑。孙吴,指战国时军事家孙膑、吴起。全诗语言质朴平淡,但由于纪录了当时边塞实况,且写景壮阔,情怀激烈,仍具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其九)
朝从北岸来,泊船南河浒。试共野人言,深觉农夫苦。去秋虽薄熟,今夏犹未雨。耕耘日勤劳,租税兼舄卤。园蔬空寥落,产业不足数。尚有献芹心,无因见明主。
此题为途中纪实之作,本诗原列该组诗的第九首。前四句写行程路线及最突出感受,自北而南,满目情形大体相似,可见“农夫苦”已成普遍现象。中六句具体描述农夫之苦况,除日日劬劳之外,再加天旱、租税之双重灾难,无所收获也就是必然的了。末二句自抒怀抱,虽有良策拯民,却无由上达,于无奈中显出强烈的民胞精神与失志之愤。高适此诗作于开元年间,却能于盛世背后发现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样的题材,在盛唐诗人中大约以此篇为最早。
登陇
陇头远行客,陇上分流水。流水无尽期,行人未云已。浅才登一命,孤剑通万里。岂不思故乡,从来感知己。
此诗是高适赴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途中登陇山有感而作。前四句以陇上流水意象表达独身远行的心理感受。流水、行人,既是写实,又构成象征性的互喻关系。后四句抒发此行意欲有所作为、建立功业之壮志。“浅才一命”、“孤剑万里”,活画出慷慨任侠的形象;只身远游,固生乡思,然更感知己,足见报效国家之豪情。此诗语言简洁,但却包容着丰富内容,既思故乡,又感知遇,既叹身世飘泊,又表报国壮志,所谓“感知忘家,语简意足”(《唐诗别裁集》),写足孤身远游、求取功业之意。
古大梁行
古城莽苍饶荆榛,驱马荒城愁杀人。魏王宫观尽禾黍,信陵宾客随灰尘。忆昨雄都旧朝市,轩车照耀歌钟起。军容带甲三十万,国步连营一千里。全盛须臾哪可论,高台曲池无复存。遗墟但见狐狸迹,古地空余草木根。暮天摇落伤怀抱,抚剑悲歌对秋草。侠客犹传朱亥名,行人尚识夷门道。白璧黄金万户侯,宝刀骏马填山丘。年代凄凉不可问,往来唯有水东流。
此诗作于与李白、杜甫同游大梁之时。其时高适隐居宋中,求仕无门,即于这首咏怀古迹之作中,透露出悲凉的身世之感。全诗四句一转韵,分为五个自然段落。第一段写驱马荒城所见景象,第二段引出对往昔的遥想,第三段回到眼前,回应首段,第四段紧接,写出当年风云人物的遗迹,第五段感叹当时受赏的朱亥、侯嬴荣耀一时,终成过客,如今只有汴水东流而已,既生兴亡之慨,又将古今一脉贯穿,从而使兴亡之叹融入自己身世之感。此诗情感浓烈,思绪曲折,章法整饬,表现自然。
邯郸少年行
邯郸城南游侠子,自矜生长邯郸里。千场纵博家仍富,几度报仇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纷纷,门外车马常如云。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君不见即今交态薄,黄金用尽还疏索。以兹感叹辞旧游,更于时事无所求。且与少年饮美酒,往来射猎西山头。
此诗是高适青年时代作品,诗中描述的“邯郸少年”可以视为诗人之自况,借以表达内心的愤世之慨与任侠豪情。邯郸,是战国时赵国都城,即今河北邯郸。诗的前六句写“游侠子”生长之地与侠义轻财之举,其豪爽英姿与狂放气派跃然纸上。七、八句陡然转折,写侠肝义胆无人理解,报国宏图无从实现,只有空空怀念古代“倾以待士”的平原君。后六句即直写当今世俗人情之菲薄,表现出睥睨尘世、刚直耿介的性情节操。此诗章法齐整,意态飞动,当时即被“朝野通赏”(《河岳英灵集》),极亨盛誉。
燕歌行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据此诗前原有小序可知作于开元二十六年。高适从军燕地在开元十八年至二十一年间,此诗是离开边塞之后“感征戍之事”并回顾自身边塞经历之作。诗中充分展示了复杂的心理状态,既表达立功边塞的豪情壮志,又对边塞局势与用兵情状提出见解,因此,一方面对战士忠勇报国精神热情颂扬,另一方面又对将领奢靡生活强烈不满,并由此发出对蒙受战争痛苦的家庭的深切同情,乃至于对边将用非其人的讥讽嘲弄。全诗内容丰富,包含着对边塞情势较长时期的见闻感受,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与概括力度。此诗不仅是高适的名篇,而且堪称整个唐代边塞诗之杰作。
人日寄杜二拾遗
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身在远藩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
此诗是高适在蜀州刺史任上寄怀杜甫之作。人日,是农历正月初七日。杜二,即杜甫。杜甫居成都时,高适与之过从甚密,此诗慰故人思乡之情,发世事难料之叹,抒无所作为之憾。全诗四句一层。首四句寄慰杜甫,“思故乡”既是言杜,亦是自谓,二人故乡同为当时正在战乱的中原,这一“思”便将二人情感更加紧密地联结起来。次四句写自身,既“无所预”又“复千虑”,表白忧国情怀,“空相忆”、“知何处”,则添一层无奈与落寞之感。末四句进而将自己庸碌自适与友人飘泊四方比照,逗出“愧”意,回应篇首,写足题意。
送浑将军出塞
将军族贵兵且强,汉家已是浑邪王。子孙相继在朝野,至今部曲燕支下。控弦尽用阴山儿,登阵常骑大宛马。银鞍玉勒绣蝥弧,每逐嫖姚破骨都。李广从来先将士,卫青未肯学孙吴。传有沙场千万骑,昨日边庭羽书至。城头画角三四声,匣里宝刀昼夜鸣。意气能甘万里去,辛勤动作一年行。黄云白草无前后,朝建旌旄夕刁斗。塞上应多侠少年,关西不见春杨柳。从军借问所从谁,击剑酣歌当此时。远别无轻绕朝策,平戎早寄仲宣诗。
此诗作于已入哥舒翰幕府之时。浑将军即哥舒翰麾下之云麾将军浑惟明,其祖先乃汉代匈奴浑邪王。此诗通过送浑将军出塞,塑造出一个勇猛爱国、光彩夺目的将军形象,成为边塞诗中写人物的代表作。开篇十句写浑将军的祖先、部曲传统及其身先士卒的品质、威名赫赫的战功。蝥弧,指军旗。嫖姚,指汉代嫖姚校尉霍去病,这里喻指主将哥舒翰。骨都,指匈奴左右骨都使。次十句进而写浑将军在边境形势危急时奋不顾身、转战南北的具体行态,使其形象更加神充气足。最后四句点明“送”之题,并寄托自己的殷切期望,预祝其早奏凯歌。绕朝策,指秦大夫绕朝曾赠人马鞭,这里比喻破敌之计策谋略。仲宣诗,指王粲《从军诗》,这里比喻捷报。此诗铺绘壮美,极见盛唐气象,同时也表现出诗人自身壮伟的精神面貌与豪放的艺术风格。
封丘作
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归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笑今如此。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付与东流水。梦想旧山安在哉,为衔君命且迟回。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
高适近五十岁时才因张九皋的推荐而中有道科,然却仅得封丘尉之低职,此诗即作于封丘尉任上,抒发了失望与矛盾的心态。首四句以超脱世俗的姿态自表品格,见不堪作吏的原因。孟诸,是古泽薮名,在今河南商丘东北,这里泛指梁宋一带。次四句进而写不堪吏务的实情。复四句语意转折,由家人之不解见自身与世俗之龃龉之深。末四句明揭归隐之念,与篇首遥相照应。梅福,是汉代南昌尉,曾屡次上书,皆不被采纳。全篇四句一转韵,且皆前二句散行,后二句骈俪,经纬成文,回环往复,结构颇见匠心。而情感强烈,奔泻而出,既见跌宕之势,更显雄强伟力。
别韦参军
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国风冲融迈三五,朝廷礼乐弥寰宇。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归来洛阳无负郭,东过梁宋非吾土。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世人遇我同众人,唯君于我最相亲。且喜百年见交态,未尝一日辞家贫。弹棋击筑白日晚,纵酒高歌杨柳春。欢娱未尽分散去,使我惆怅惊心神。丈夫不作儿女别,临歧涕泪沾衣巾。
此诗作于求仕未得之时,诗借赠别之机抒失意怀抱。前十二句自叙入京求仕、落拓失意、客游梁宋的经历,先写壮伟襟抱,次讽朝政昏聩,再写客游梁宋,失意之情充溢字里行间。三五,指三皇五帝,这里喻指理想的政治。负郭,指近郊良田。后十句写与韦参军友谊及惜别之情,于众人中拈出“唯君”,见知己之感,欢娱交密,却又不得不离别,尤增惆怅,而临别之时,又以劝慰作结,足见诗人虽怨尤却不消沉,充满对前程的期待与希望。诗中暗用姜太公“垂钓”故事,可见非凡抱负。
部落曲
蕃军傍塞游,代马喷风秋。老将垂金甲,阏支着锦裘。雕戈蒙豹尾,红旆插狼头。日暮天山下,鸣笳汉使愁。
此诗作于初至哥舒翰幕府之时,表现出对边事的关切与忧虑。首联概写“蕃军”兵强马壮、意气骄横情势。颔联以“垂金甲”与“着锦裘”之具体形象写出蕃军将帅略无顾忌、首领安闲自得神情。颈联以“雕戈”、“红旆”写出蕃军兵器之锐利与军阵之齐整。尾联直点汉使之愁,并以“日暮”、“鸣笳”渲染出塞外苍凉氛围,诗之主旨至此毕现,而前六句的铺述亦至此而见其作意所在。
送李侍御赴安西
行子对飞蓬,金鞭指铁骢。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虏障燕支北,秦城太白东。离魂莫惆怅,看取宝刀雄。
此诗为送人出塞从军之作,充满亟欲立功异域的慷慨豪情,且气势纵横,音韵铿锵,曾被后人誉为“盛唐五言律第一”(许学夷《诗源辩体》)。开篇以“飞蓬”喻“行子”,虽为传统习惯,但其将之与“铁骢”、“金鞭”联结起来,即造成一种异乎寻常的力度。颔联写送别,但在“一杯”之中却涵纳“功名万里”之“心事”,这就使功业之志超越了惜别之情。颈联荡开,写出离别之地及友人将去之地,既是写实,亦是托情。尾联先以“莫惆怅”相劝慰,复以“宝刀雄”相激励,塑就一幅壮士别离的英伟形象,以人物回应篇首,以气势贯穿全篇。
使青夷军入居庸三首(其一)
匹马行将久,征途去转难。不知边地别,只讶客衣单。溪冷泉声苦,山空木叶干。莫言关塞极,云雪尚漫漫。
高适于天宝九载秋以封丘尉送兵往青夷军,此诗是返回途中入居庸关时所作。诗写行役之艰难与边地之苦寒。首联概写行役时久,去、返皆难,以下皆承“难”而出。颔联以惊讶衣单写出“边地别”的最突出感受,将“难”具体集中于此,不言寒而已觉寒气逼人。颈联写水冷、木落,从听觉、视觉两方面进而渲染寒的环境氛围,暗言其范围之广大。尾联即明言虽关塞已尽,然寒冷征途仍甚迢遥,回应开篇之征途。作为边塞之作,此诗不写战争,亦不写异域风光,而是撷取“寒”这一独特角度,透现边塞苍凉意味。
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
嗟君此别意何如,驻马衔杯问谪居。巫峡啼猿数行泪,衡阳归雁几封书。青枫江上秋天远,白帝城边古木疏。圣代即今多雨露,暂时分手莫踌躇。
此诗送李、王二少府分赴两地,皆为谪贬,且高适时任封丘尉,亦正失意,所以这首送别诗就显得内容较为丰富,情谊尤感挚厚。首联先以询问领起,牵出谪贬送别的特殊情境。中二联针对李、王二人贬谪之地,想象僻地荒寒环境,既写景,又寄情。七、八句以劝慰作结,同时揭示出积极进取的抱负与信心。此诗中连用四地名,本为律诗之忌,但由于情意真挚,气势健举,所以并不感到窒碍。
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
遥传副丞相,昨日破西蕃。作气群山动,扬军大旆翻。奇兵邀转战,连弩绝归奔。泉喷诸戎血,风驱死虏魂。头飞攒万戟,面缚聚辕门。鬼哭黄埃暮,天愁白日昏。石城与岩险,铁骑皆云屯。长策一言决,高踪百代存。威棱慑沙漠,忠义感乾坤。老将黯无色,儒生安敢论。解围凭庙算,止杀报君恩。唯有关河渺,苍茫空树墩。
高适任职哥舒翰幕府期间,随着边塞形势的转变,其对边事的忧虑情绪亦逐渐淡褪,而代之以胜利的喜悦与热烈的颂扬,此诗即作于哥舒翰大破九曲之后。此诗以排律的形式,对哥舒翰军威、破敌、谋略、忠心尽力铺排,热烈颂扬其雄武英姿与安边功业。对于破九曲之事,高适还有《九曲词三首》等作,同样展示了安边定国的光明前景与个人博取功名的饱满信心,可见这一事件对高适人生、思想实具重要影响。
送兵到蓟北
积雪与天迥,屯军连塞愁。谁知此行迈,不为觅封侯。
此诗作于送兵至青夷军之时,高适时任封丘尉之卑职,诗中发抒的是郁郁不得志之情怀。前二句写积雪铺天、军阵连云的景象,塞外特征由此得到集中概括。一个“愁”字又奠定全诗基调。后二句即写自身远行边塞军中,却并不为建功业、觅封侯,显然是以反语抒激愤之情。这首小诗虽意在抒发愁怨意绪,但却充满情感力量,表达简洁明练,读来动人心魄。
营州歌
营州少年厌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
此诗作于高适首次出塞从军燕赵期间,写边地少年生活习惯与豪爽性格。首句将营州少年与原野联系起来,点明其特定生活环境。营州,在今辽宁朝阳。厌,同餍,饱意,这里引申为饱经、习惯意。二句写其出猎情景,“狐裘蒙茸”活画出营州少年生动形象。三句“千钟不醉”,见其豪放之习,四句“十岁骑马”,见其勇悍之性。全诗充满对营州少年的赞美之情。作此诗时,高适首次出塞,所以一见粗犷豪迈的边地少年,即引起本身就“不拘小节”、“隐迹博徒”的诗人的强烈钦羡。全诗笔墨粗放,充溢着浓郁的边塞情调。
塞上听吹笛
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
此诗写塞上闻笛而生乡关之思,但首先却展现出冰雪铺凝的广袤胡天,然后再在明月与戍楼之间托出羌笛之声,而笛声乃《梅花落》之曲,这样就在荒漠塞外与故乡春色的鲜明反差之中透露出缕缕乡思。但这乡思却略无哀怨,而是随着一夜风吹渗满整个关山,以可见的壮伟景观的实态体现出巨大的内在显现力与艺术包容力。
别董大二首(其一)
千里黄云白日昏,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这是一首送别之作,但从景物描写看,却无异于一首边塞诗。诗写惜别之情,首先展现的却是一幅苍莽壮阔的塞外风光画卷。在这样的壮伟景观氛围中托出心绪,表面上是以怀才挟技无往不适相劝慰,内质中则是一种豪壮气势伟力的体现,在艺术表现上以“妙在粗豪”(徐增《而庵说唐诗》)的特点而成为千古名篇。
听张立本女吟
危冠广袖楚宫妆,独步闲庭逐夜凉。自把玉钗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
此诗通过对歌女情态的生动描绘,创造出一种清雅空灵的意境,在高适诗中别具一格。首句写妆束,显其高贵,次句写行态,见其脱俗,三句写动作,以敲竹击节逗出下文。四句“清歌一曲”点题,并以“月如霜”渲染环境氛围,既回应“逐夜凉”,更构成对清歌一曲内涵的体味,使环境、歌境、心境融通一体,在描写与感受的妙合中生成诗境整体。
除夜作
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
此诗作于除夜旅途之中,抒发思乡之情。开篇即点明身在“旅馆”,以“寒灯”与“独”构定凄冷孤寂氛围,次句转入自身,直白凄然的内心世界,同时以“何事”二字为诗意的深入提供悬念与契机。三句写乡思,却言“故乡思千里”,包含有自己思念故乡亲人,而同时遥想故乡亲人思念千里之外的自己两重意蕴,是客心凄然的第一层原因。末句“明朝又一年”点除夜之题,而自顾已是霜鬓,明朝将又添白发,乡思之中更增岁月流驶、人生苦短之叹,是为凄然的第二层原因
塞下曲
唐 卢纶
月黑 雁 飞 高,
单于 夜 遁 逃。
欲将 轻 骑 逐,
大雪 满 弓 刀。
[作者简介]
卢纶(748-800),字允言,河中蒲(今山西永济县)人。唐代诗人。
[注释]
1.塞下曲:古时边塞的一种军歌。
2.月黑:没有月光。
3.单于(chán yú ):匈奴的首领。这里指入侵者的最高统帅。
4.遁:逃走。
5.将:率领。
6.轻骑:轻装快速的骑兵。
7.逐:追赶。
[参考译文]
月亮被云遮掩,一片漆黑,宿雁惊起,飞得高高。在这月黑风高的不寻常的夜晚,敌军偷偷地逃跑了。将军发现敌军潜逃,要率领轻装骑兵去追击;正准备出发之际,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刹那间弓刀上落满了雪花。
[提示]
这是卢纶《塞下曲》组诗中的第三首。卢纶曾任幕府中的元帅判官,对行伍生活有体验,描写此类生活的诗比较充实,风格雄劲。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表白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