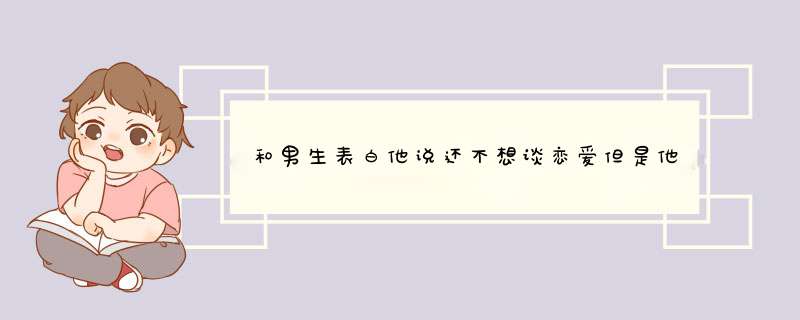
意思就是他还得再考虑考虑,希望和你拍拖,又矛盾着什么。当然也有可能是玩你呢,这种可能性很小,不过为了楼主的幸福不得不说一句。
建议楼主也送他一份小礼物表达一下心意,并且加大一下追求攻势,并且多打听一下他过去的恋爱史,一旦发现他不是什么好人就放弃吧,如果发现他挺好的,那么好好坚持,一定会对你好的。
祝楼主幸福。
所谓彩色沥青混凝土路面是指脱色沥青与各种颜色石料、色料和添加剂等材料在特定的温度下混合拌和,即可配制成各种色彩的沥青混合料,再经过摊铺、碾压而形成具有一定强度和路用性能的彩色沥青混凝土路面。也称作彩色沥青路面:
彩色沥青路面作为一种新型的铺面技术,在城市的道路施工中,具有防止交通事故/防滑、交通减速提示、吸收噪音,美化环境的功能,体现出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的特征和个性,进步全部城市的形象和功用,显示出现代化都市的气度和魅力。那么它有什么性能特点呢下面抗车辙剂生产厂家的科技人员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具有色泽鲜艳持久、不褪色,并且能耐77℃的高温和-23℃的低温。
二、具有良好弹性和柔性,“脚感”好,最适合老年人散步,且冬天还能防滑,再加上色彩主要来自石料自身颜色,所以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危害。
三、具有良好的路用性能,在不同的温度和外部环境作用下,其高温稳定性、抗水损坏性及耐久性均非常好,且不变形、不剥落,与基层粘结性良好。
四、具有较强的吸音功能,汽车轮胎在马路上高速滚动时,不会因空气压缩产生强大的噪音,同时还能吸收来自外界的其他噪音,保证了居民的生活环境
栗子
--------------------------------------------------------------------------------
作者:萧乾
黑暗与寒冷把冬夜凝成块不透明的固体。多云的天空,隐约浮荡著一道灰黄风圈,在天心摆来摆去,若在搜寻著适当的受害者。今夜,海上也许还有风骚船女弹著琵琶。乐吧,风圈冷笑著,明朝连半寸桅杆也不给留。
风似乎在试著它的锋刃,已经在树间房角穿行著了,呼著尖锐的哨子。孙家麒兀自倚坐在校园小土坡上一株蓊郁苍苍的伞形老松下,用大氅领把脖颈厚厚包起,手塞到衣袋里,摆弄著一把圆滚冰凉的栗子。他手指在那些果实中间穿来穿去。被装在黑黑角落里的小东西就任他抓得挤挤碰碰,滑溜溜地在他指缝间钻来钻去,如小狐狸精在跳花环舞。它们也许还觉得好玩呢,那只手的主人却正生著闷气。刮吧,他仰视一下那风圈。他气恨这世界的炎凉。分明适才还烫手的栗子,这时竟冰凉到这地步。可是热劲儿里去,偏偏它周身的糖质还附丽著,粘抓抓的感觉使他怔忡不安了。他重重咬了咬下唇,用力捏碎刚溜出大指缝的一颗栗子。
那暴戾的嘎吧声静止了果实的活跃。(这时它们才发现原来不是好玩的事!)那声音,那破碎,使得他畅意了。他几乎笑出声来。嘎吧,嘎吧,溜出一颗捏碎一颗。捏死你们!他自语著。捏死这些不老实的小东西,你们还闹!大指鼓著力,嘎吧,嘎吧,瞬间他几乎把袋子里的栗子全捏破了。适才供他吃,供他欢娱的小果实们,现在一个个残废地躺在黑黑衣袋里了。外皮迸裂的它们,这时不再能在手指间穿来穿去了。它们僵卧著,如垂亡的伤兵,规规矩矩。这平静显然得归功於大拇指有力的镇压。他掏出手来,指肚上有些刺痛。果实原来还有硬壳。他好像对著谁表白受了委屈,又像安慰著那指肚似地嗫嚅著:「可恶的小东西,多刁横!」
他松释地吐了一口气,扶著树杆直起身腰。一阵眩晕,他注意到课室方向的灯光了。那光焰简直像一只红手,捏住他的脖颈。他有点要——他狠狠啐了一口唾沫,对著黑空咒骂著:「狗男女,一个个,捏死你们!」
挺起腰来,展现在他眼前的是银亮亮一片平滑闪光的冰场。风吹得冰上的灯光暗淡而且摇摆,凄迷地旋转著几条修长的人影。冰刀接触冰面的哧哧声,夹杂著怒风的嚎叫,活像在他胸脯上画著横竖口子。他有些忍受不住。掉过头来,视线逢到的又恰是往常他们并肩坐过的白白石阶。在那里,他曾挺直脖颈为一个女子唱过许多首豪放凄艳的歌曲。去年这时候,还有只绵软的手把热栗子餵进他的嘴里,随著是一个温柔的微笑。他不能想了。这古怪的人生!
那时他多幸福啊。栗子瓤是金**的,他每一个日子也染上同样灿烂颜色。他是当地警察署长的三少爷,拉得一手好提琴,在冰场上是「外曲线」的高手。如今,栗子凉了,冰场除了少数来自椰林岛的华侨外,也没人照顾了。最可气的是那些小子们把宿舍用红绿纸糊满,说什麼「禁止娱乐」!
他要「自由」,偏拉那个。《小夜曲》他还拉不到一节,门砰砰响了。进来的是那个臭股长,和,唉,和他的青。想起来他简直气煞了。他等著菁保护他,甚至如往常那麼安详地倚在他左胁下,为他机警地翻乐谱。但换上了蓝布褂、戴上了「纠察员」臂章的她,却冷酷无情,已变成了另外一种人。
——家麒,你不能拉!国家到了这个地步,你还……
喝,那严峻的声调,那冰冷的面孔,快把他气炸了肺。他把提琴挟在胁下,愣著眼睛,气冲冲地走过去,一把抓著她那弱小但是倔强的胳膊。
——喂,孙同学,她是纠察员。她办的是公。请放手!
公!哦!狗男女。公!若不是心疼那值三百块的提琴,他一定挥起来打在那奥股长生满了黑髭的颊上了。他一点不知道菁是什麼时候为他勾去的。有两个来月了,她皱紧眉峰,总像是牵挂著什麼了不得的事。一见面不再那麼小鸟依人地笑了,第一句话总脱不了:「看报没有?」读书时期嘛,干麼过问政治!
如今他承认女人是不可理解的动物了。她们永不能如一个男子那麼牢牢地攫住幸福的尾巴。她们时常眼睁睁放它滑过。为了排解她的愁闷,他也算尽到一个恋人的苦心了。他唱《销魂曲》,她掉过了沮丧的头;拖她去馆子,任什麼别致的菜她也没胃口。直到她戴上「纠察员」臂章的那早晨,他才察觉糟了。瞒著他,菁已参加了一项他不以为然的工作,那直接威胁到他爹饭碗的工作。
——家麒,我得尽我作人的本分。你自己既不肯参加,暂时先别来缠我!
呵,狠心的女人。愚蠢的女人!你有什麼本分呢!能尽什麼本分呢?还不是和那奥股长厮混!他愈想愈气。在那灯光摇曳中,他彷佛看见菁和那生著黑胡髭的人在磨磨蹭蹭。对,窗户上的人影始终在不停地摇摆。他心中刺痛起来。他沉重地顿了一下脚,跄踉地踱下土坡。
冰上正滑著两三对男女。随了旋风,他们把手搭成籐萝姿势,像黄昏的蝙蝠那麼轻掠著,敏捷,和谐,杂著愉快的谈笑。这景色不能不说在故意和家麒为难。一条条幸福的背影在讥笑著、鞭打著他的心。冰上的舞姿使他厌烦。去年这时,菁不也这样把手搭在他肩上吗?那时她穿的是一件花格短袄,上面飘著雪白柔软的围巾。她几乎把半个身的重量都托给了他。(这时他还能感觉那负担的快意。)绒帽里的汗珠虽渗透,他可还不忘记为她哼华尔兹的调子。冰上掠著他们幸福的影子。兜过几个圈子后,他们携手滑到席棚下去啜热寇寇。白的蒸气暖著红润的脸蛋……
他不堪再想下去了。冒著冷风,他跨过了石桥。他笔直扑奔那人影憧憧的灯光。他握紧拳头,准备一进门,不容分说就把菁拖到怀里。抱住她,抱紧了她。如果那家伙再「喂」,就先用拳头给他妈一下。对,得给菁看看,麒不是软弱无能的。美国权威心理学家不是说过吗,古今女子皆崇拜英雄,爱野蛮。所有的西洋**都证实了这真理。夺回菁,他看不出更好的路。
楼门口这时贴出更多的标语了。红红绿绿的,什麼「准时出发」,「整队回校」,都如各色毒蛇在噬著他的心。他没心读那文字,只感到一种颜色和气势的威胁。
「喂,开门。开开门!」
「你找谁?这里正在办公。」
门开了一道缝,见并非职员,又砰地关上了。
他对那扇门发气。他明明看见一个女人的影子,彷佛伏在桌上。那一定是她。一定的。他们在里面干麼呢?鬼鬼祟祟,喝!砰砰砰,他死命地捶。
门这次豁然开了。灯光下抬起了几张脸:悲愤,紧张,兴奋,坚决是他们的神情。
家麒睁大了眼满屋里搜寻。他看到裁纸的,挥著寸毫的,研墨的。迎富有三个女生在摆弄著一架油印机。刺鼻的油墨气味使他倒退了两步。等他发见那握著油墨滚子的是谁时,他不顾一切地扑过去了。
「菁,你,你在这里!干这个……」
为他抓住胳膊的是个身材颇纤细的女生。虽然这时咬住的牙根使她的脸显得很严峻,但嘴角的笑涡愈发增添了她的温柔美丽。和房中别人一样,她穿的也是件毛蓝褂,而且工作忙得还使她的头发也有些蓬乱。她用不知所措的神情凝视自己招来的这个闯入者。像是什麼东西在她心上划了一下,她两腿有些酸软。但即刻她的眼睛与壁上的誓约相遇了。(那旁边还贴著一张涂满了鲜红血迹的地图。)她的脸绷得紧了一些,咬了咬稍见惨白的下唇,刚想开口……
「喂,这里是办公的地方。」
闯入者的眼睛瞪圆了。他看到正伏在条桌上写著标语的股长。黑胡髭彷佛又多了些,在那身棕色学生服上面是一张声色俱厉的脸,放射著两道正直森凛的目光。家麒由那上面读出鄙夷,威胁,一切难以容忍的字眼。看到菁那种近於不屑的神气,感觉了四下向他逼来的愤怒眼光,他有些窘促了。他甚而有些后悔自己的莽撞。但他抑制不住,他在桌上啪地捶了一拳,跟著冲股长说出一句不顺耳的粗话。
已经在羞惭著的女生,这时明白得自己出面来制止了。她把油墨滚子托给身旁的同伴,红著脸小声说「就来」,便低了头,默默走出门了。
登时,得意的光彩在家麒的脸上焕发了。他向著那逼视著他的股长做了一张鬼脸,才闪身跟了出来。
「菁,莫不成你变了!你别受他们笼络吧,我俩是秤杆同秤砣,分不开的。」
女生背了双手,挺直身子,眼朝著另一个方向说:「我没变,是日子变了,环境变了。家麒,我没工夫同你说傻话了。你闲著我不闲。我还有事情做。我得做。我再不做就永远做不成了。我们明天早晨要游行。我要去筹备。你走,我求你啦。」
话交代完,关心著工作,她打开门就想回屋。
「不能,菁,你不能去游行。今天爸爸来电话了,嘱咐我明天千万出不得门。他们什麼都预备好了:水龙,刺刀,哼,还有机关枪呢。你们这群一共有多少!」他由口袋里掏出手来比方,无意中带出一把破裂的栗子。「瞧,他们早晚都得像这个,给捏个粉碎。你还去混吗?来吧,爸爸有权柄不准我去,我有权柄不准你去,对吗,菁?叫那股长一个人去闯死,咱……」
他话没说完,女生气得已经有些打抖了。她猛地咬著下唇,掉过身去。她死命地挣扎,摆脱了被抓住的手臂。
「撒开我!你有什麼权柄!家麒,我有我的事。我得做。去,告诉你爸爸,把刺刀磨亮点……」
随了黎明,黑黑天心那道风圈渐渐显得朦胧了。料峭的风如一把铁铲向著大地削来,它又像一个拙笨的泥水匠东削西砍,削落了枯树枝上的残叶,削破了茅舍稀松的屋顶,也削著街头乞丐生了疮的胳膊。万物都为那残暴的风慑伏住,寒风正愁没的可削砍时,街上发见一簇整队的群众。
这是个混沌的日子。生与死的界线突然变得模糊不清了。风卷著一群不安於现状的青年在街上呐喊,北风如条狡猾的蛇,冰凉地朝那些张著的嘴里钻。填满了盛著愤怒的肺,填满了空空的肚皮。喜鹊躲在巢里,街上不见莱贩的足迹,他们还是扯了嗓子喊,小纸旗摇得哗啦啦像闹水。
迎面,旋风成为自然的烟幕,幕里隐著穿黑衣的弹压者。举著闪亮闪亮的大刀:牛皮鞘,红绸繐,天天操演著的冲锋包围阵势,到今天全用上了。寒风削砍著万物,弹压者也那麼无慈地砍削著同类。杀,杀,半条鼻梁,一泡血,想流进电车沟儿,北风不答应,即刻冻成冰块。冲,冲,养兵千日,用兵一朝。署长有命令,谁个不听命令,饭碗砸破。
衣裳扯碎。旗面刮掉,不碍事,还有旗杆。旗杆下面跳动著一颗心,气愤愤,鲜淋淋。喊,喊,嘎嘶的喉咙,冻麻了的手。不成,不成,汉奸勾当不赞成!得在自己地面上作主人,活得有味儿,奴隶不当!倒下一个,去搀,背上也挨一刀。烟火,不,空中银花,好个奇观!喊吧,水向肚里灌。脖子里也发现了什麼,冰凉,湿渌渌,眉毛上冻起冰山。高处还飞著砖头。脑袋平地突起一个包。还是冲——
北风为黄昏稍稍敛住,夜又撒下黑暗的网。「唉哟,救——」没有喊完就倒下了,在胡同拐角,黑漆漆的。嘟咭,嘟咭,揍死你这女人!还往哪儿跑,不在家里养孩子,也出来闹。闹,叫你用,啪,啪,有你的。
沥青马路,平滑,讲究,文明,在昏暗的街灯下,成了血腥的战场。一架架帆布担架,来回穿梭著。戴白帽的护士掉了颗同情的眼泪。疲倦的战士,满身血迹的战士,躺下吧。北风息了。城门关了。弹压者吹起悠长的胜利归队号奏凯回营。躺下吧,在这地窖子里。蓝眼珠的医生忙不迭地戴上金边眼镜,一个个试过脉息,迎窗看过体温计,边叹气边摇了摇头:「为什麼自己人打自己人这麼狠!怎麼回事,中国有那麼一群不可解的动物!」
医院过道里一阵骚动。一个年近五十的戎装军人,长统皮靴发出橐橐的声音,随走随向身边一个西服青年抱怨著:「真是笨蛋!你为什麼不拦住她?干麼让她参加进去!将来还不是个怕老婆的货。她要,哼,她要偷汉,你也让?等会我看,先说明白,咱们家可不要缺须短尾的。我得……」
坐在犄角一位衣帽洁白的女看护迎面拦住了他们。
「喂,先生,轻一点。这是病房,进去不得。」
西服青年刚想卖弄点洋习气,那长辈人可不耐烦了。
「怎麼,我看我儿媳妇。」(他又小声说:「没过门的。」)「我瞧瞧她到底……」
「您找谁,您说个姓名。」
这回可把老军人愣住了。他公事实在太多,今天他才知道儿子已经有了人。儿子跑来就哇呀哇呀地哭,说重伤名单上有一个是他挂念了一日夜的人。他做过许多噩梦。许多都是假的,这回可都应了。「右眼扎伤,」啊,他朝著那名单哭了好半天。那双美丽的眼睛,永远流动著柔和明朗的眼睛,温柔幸福的泉源。平素一个连「爸」全不肯叫的孩子,这时委屈地竟下了跪。呜咽得才惨呢,他哭软了一颗杀人不眨眼的心。仓促间,做爸的披上军装,就来相看这姓名不详的儿媳妇了。
「她……」
「Miss nurse,I beg your pardon,她叫於若菁。」
看护妇做了一个神秘的知会,就领头迈著轻盈碎小的步子,把他们领到一间病房前。
房门口正立著一个探病的人。身上那件棕色学生装的口袋已撕得狼狈不堪,手上的白绷带说明他也刚刚经过治疗。辨明了来人,他瞪大眼睛,用戒备的姿势厉声问:「找谁,你们?」
「找我儿媳妇!」这三个字震得墙壁起了回响。「我要瞧瞧她。我得……」
那轻伤的青年撇下嘴岔,做出极其鄙夷的样子。蓬乱的头发散在额际。他明明认出对方的身份了。受伤的那只手握起拳头:「走开吧,这儿没有儿媳妇。这儿只有为自由挨过毒打的人。你走开,你这个凶手。我伤不重。我还能拚!」
军人的指挥刀由胁下抽出来了。那不是一件生疏的朋友。哦,小伙子果然泼悍。怪不得派出弹压的人都畏畏缩缩。看那神气,想给他一刀。一种空间或时间的观念,也许是那古怪药味,按住了他的手。他昂然走进门口。他凭的是老军人的架势。但是这架势却挡不住一个愤怒的拳头。
「好呵,你,你混账!揍死你这小子。你瞧咱,咱五颗金星,你是对手?来人,来人给我带他走。」
人来了:看护妇,外科医生,助手,还有,还有一大簇各校来探病的青年。
「揍这老家伙,揍死他!」
一片嘈杂的咒骂声如潮水般哄起。那个西服青年摩拳擦掌地保护著老军人,眼看怀恨的群众拥上来了,年长的医生忙由人丛中挤出,用著急的姿势弹压了这阵骚扰。
「这里还有病人,诸位,请守秩序。老先生,你要找谁?谁是你的儿媳妇?」
病房的门开了。洁白的床单一端露出一张厚厚缠了绷带的脸,胸脯上放著一张慰问者的签名单。病者早为骚扰吵醒了。虽然露在外面的脸只剩一半,那难以容忍的不屑神情是可以辨认得出的。她索性把露在外面的一只眼睛闭上了。她太疲倦了。她有许多话要说,但现在她需要休息。
这时,西服青年多情地凑近床畔,用帽沿擦著颊上的泪。他想去摸她的手。像预感著什麼羞辱,那手缩进被里去了。青年满心不知是忏悔还是怜惜,侧过身来,似是为双方介绍,低声说:「菁,爸爸也来了。」
病人没睬他。隔一会,她的眼皮徐徐睁开了,眨了一下,又匆匆闭上了。眉间似蕴蓄著一种苦痛:厌倦?愤怒?没人知道。但是一翻身,她面向里去了。
军人和他的儿子若有所失地互相觑视著。众人也屏著声息,静看这微妙的情景。
「菁,是麒来看你了。你怎样,还痛吗?你现在明白苦处了吧!你以后可多听点话,菁……」
那柔和的声音显然一点也不中用。床上的人仍没有动静,除了床单稍稍有点起伏。她把脸深深地埋在枕侧了。
「菁,咱们还是咱们,没人能分开,对吗?」
突然,她翻过身来了。她疲惫的眼睛还放射著愤怒的火。她的嗓子劈了,嘎了,没力气了。她哑哑地但嘴部动作明明是非常坚决地说:
「走开,你捏碎了我,得叫我养息。我好了还要去干。我认不得你了。我讨厌你。你走你的路吧,不要在这里。这不是你耽的地方!」
一九三五年除夕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表白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