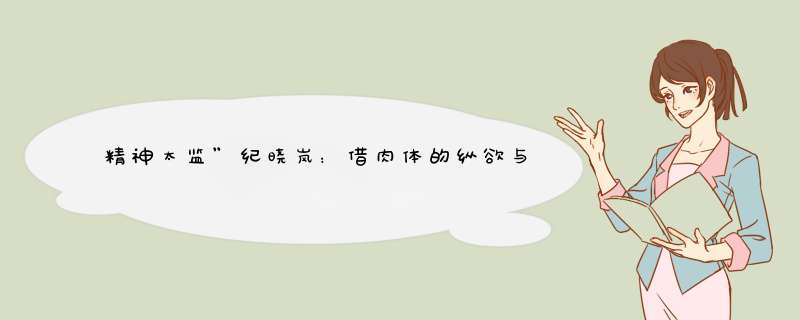
精神太监”纪晓岚:借肉体的纵欲与狂欢消磨豪情?
他在被清朝的统治者“ ”了精神和思想上的创造性,变成了一个“精神上的太监”之后,便迅速地滑向了肉体上的纵欲和狂欢,竟然“年已八十,犹好色不衰”,试图用这种肉体的狂欢,来发泄过剩的“力比多”,借以消磨豪情,转移自己内心的压抑和痛苦。
整个有清一代,纪晓岚可以算是文化方面屈指可数的几位代表性人物之一。总括他的一生,除了在仕途方面很有些得意,在满清王朝初期特别是“崇满抑汉”的大背景下,一直做到了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的高位之外,在文化方面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在干隆皇帝的直接授命下,主持编纂了清 最具有想象力的“形象工程”——《四库全书》,并著有一部以谈鬼怪故事为主的《阅微草堂笔记》。
当然,以上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家未必熟知的则是纪晓岚超乎寻常人的“纵欲”。
具体而言,纪晓岚的“纵欲”主要表现在“食”和“色”两个方面。就“食”的一面说,他的癖好是只吃猪肉,不吃米、面,而且饭量奇佳,动辄每顿吃掉十数盘猪肉。而相对于“食”的一面,纪晓岚在“色”方面的表现,则更是令人瞠目结舌,以至于不免使今人怀疑他老先生是不是染上了“ 亢进”的毛病。
关于纪晓岚在这两个方面的特异之处,清人的一些野史笔记中多有记载。这里不妨随手援引几条,以为参证。
小横香室主人在《清朝野史大观》卷三中说:“公平生不食谷面或偶尔食之,米则未曾上口也。饭时只猪肉十盘,熬茶一壶耳。”
采蘅子的《虫鸣漫录》卷二说:“纪文达公自言乃野怪转身,以肉为饭,无粒米入口,日御数女。五鼓如朝一次,归寓一次,午间一次,薄暮一次,临卧一次。为每日不可缺者。此外,乘兴而幸者,亦往往而有。”
昭枪在《啸亭杂录》卷十中也说:“(公)今年已八十,犹好色不衰,日食肉数十斤,终日不啖一谷,真奇人也。”
孙静庵《栖霞阁野乘》一书讲述了一个关于纪晓岚好色的精彩故事:“河间纪文达公,为一代巨儒。幼时能于夜中见物,盖其禀赋有独绝常人者。一日不御女,则肤欲裂,筋欲抽。尝以编辑《四库全书》,值宿内庭,数日未御女,两睛暴赤,颧红如火。纯庙偶见之,大惊,询问何疾,公以实对。上大笑,遂命宫女二名伴宿。编辑既竟,返宅休沐,上即以二宫女赐之。文达欣然,辄以此夸人,谓为‘奉旨纳妾’云。”
堂堂的一代文宗,竟然好色到了近似于“色情狂”的病态程度,甚至在堂堂的干隆皇帝面前也丝毫不加掩饰,这一现象到底是一种单纯的生理现象,还是一种复杂的精神现象?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似有进一步解析的必要。
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前人的野史笔记都将其归之于一种单纯的生理现象,说他是“奇人”,具有这个方面的特异功能,云云,都是一些被表面现象所蒙蔽了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泛泛之谈。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作为一位才情冠绝一时的大知识分子,纪晓岚的“好肉”与“好色”,不只是一种纯粹的个人生理现象,而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现象。因此,必须到纪晓岚精神世界的深处寻找原因,才能够切中肯綮,找到这种现象的最合理的解释。
首先,我以为有必要从纪晓岚在文化学术方面所取得的几项成就的“含金量”说起。
如前所述,纪晓岚为世人所瞩目的文化成就主要有两项:一是奉旨主持编纂了《四库全书》;二是在晚年写了一部“追录旧闻,姑以消遣岁月”的随笔杂记《阅微草堂笔记》。
关于《四库全书》,“五四”以后的鲁迅、唐弢等人曾将其评价为一部 中国古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实际上,在学术界尤其是国外的汉学界,持此类观点的多有人在。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其名著《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
通过这项庞大工程,清廷实际上进行了一次文字清查(文学上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是取缔一切非议外来统治者的著作。编纂人在搜求珍本和全整文本以编入这一大文库时,也就能够查出那些应予取缔或销毁的一切异端著作。他们出善价收集珍本,甚至挨家挨户搜寻。该禁的图书是研究军事或边务的著作以及有反夷狄之说的评议,还有就是那些颂扬明朝的作品。……正如L。 C。 古德里奇所论证的,这是最大规模的思想统治。
无独有偶。哈佛大学著名的中国史教授史景迁在他的《追寻现代中国》(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一书中,提及这部堪称浩瀚的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工程时,在充分肯定了它取得了“中国目录编纂的伟大成就”的同时,也鲜明地指出——
编纂《四库全书》还具有检视文献的目的,借此搜查私人藏书,并严惩那些收藏有轻视满人内容的书籍的人。这类书,以及包含有害于中国国防的地理和游记类书籍也被销毁。这些毁书行动之彻底,使得我们知道的 隆的文化顾问纳入禁毁之列的两千多种图书从此销声匿迹。
别人暂且不管,反正我个人对于上述学者的这些“诛心之论”,是心有戚戚的。故此,纪晓岚秉承皇帝的谕旨所从事的这项事业,你当然可以说它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但也完全可以说它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项“缺德工程”。
至于《阅微草堂笔记》,虽然皇皇24卷,但是仔细阅读过它的人都会发现,这部明显受了蒲松龄《聊斋志异》影响的笔记体杂记,除了语言精美典雅、行文亦庄亦谐、故事引人入胜等几个优点外,倘就其内容和思想性而言,则无非是借一些道听途说的神鬼妖狐的小故事,重弹“因果报应”的老调子,很少有震聋发聩的独到而新颖的观点和见解,因此,未免就失之于贫乏和单薄。
尤为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纪晓岚本人对这部消遣之作,也并不看重,他曾经这样评价自己的《阅微草堂笔记》:“平生心力坐消磨,纸上云烟过眼多。拟筑书仓今老矣,只应说鬼似东坡。前因后果验无差,琐记搜罗鬼一车,传语洛闽门弟子,稗官原不入儒家。”
因此,倘若从上述视角看问题,那么,总括而言,纪晓岚在文化方面的成绩其实是乏善可陈的。诚然,他拥有绝世的才情和强健的体魄,在一个正常的时代里,本应该留下能够代表自己真正水平的著述,传之后世,启发后人。但事实却是除了代满族皇帝编辑了一部 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书,写了一部没有什么思想价值的《阅微草堂笔记》之外,纪晓岚实在没有留下真正让人瞩目的有价值的伟大作品。对这样一位旷世奇才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必须强调的一点是,纪晓岚在文化方面乏有真正的大建树,并不是因为他的才学不足以达此。恰恰相反,纪晓岚是具备成为“一代宗师”的才情、阅历和精力的。而且,他本人也具有强烈的发表欲和表现欲,酷爱出风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野史上也不会留下那么多关于他妙语解颐、当众挖苦别人的段子了。
那么,才情冠绝一时的大才子纪晓岚为什么“懒于著述”呢?在这里,不妨看一下清代知识界人士对此的见解。
清人陈康祺在他所写的《郎潜纪闻二笔》卷六中,就曾经专门研究了这一问题,并引用纪晓岚自己对于这个问题做出的解释。
在“纪文达不轻著书之原因”一节中,陈康祺这样说道:“纪文达平生未尝著书,闲为人作序记碑表之属,亦随即弃掷,未尝存稿。或以为言。公曰:‘吾自校理秘书,综观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备。后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范围,其自谓过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
这段话透露出来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纪晓岚活着的时候,他的“懒于著述”的特点就已经被有心人发现了。而且,纪晓岚对时人的这种议论,似乎非常感冒,忙不迭地对此一问题专门解释一番。根据纪晓岚自己的说法,他懒得著述,是因为他看的古书实在太多,知道自己纵然写得再好,也不过是在拾人牙慧,断难超越古人已有的思想,因此才主动放弃了著述的努力。
不过,纪晓岚本人所做出的这样一种解释实在有些经不起推敲。纪晓岚的确是读书甚多,见闻颇广,但是古人读书比纪晓岚多的应当大有人在。别人先不说,单说在他之前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恐怕哪个人读的书也不能说比他老人家少吧,但为什么人家这些人就没有因此而“懒于著述”呢?
再者,如果按照纪晓岚的这个逻辑,世人今后岂不是都不要再努力著述了吗?真要如此的话,“名山事业”岂不是要寿终正寝了吗?以纪晓岚的睿智,他完全应当知道,古人并没有穷尽天下所有的真理,也不可能穷尽天下所有的真理。一个时代的人有一个时代人的独特感悟,每个人的感悟都是不可能完全重复的。
所以,纪晓岚自己所说的不愿意著述的原因完全是站不住脚的搪塞之词,他之所以没有尽心著述,写出与其才情相匹配的巨著来,明显是另有隐衷。联系到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文化界的现状,这个原因其实也很简单,这就是:高压的文化政策,频繁兴起的文字狱,已经使纪晓岚的思想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他被迫接受了精神上的“自我 ”,从此不敢写出任何有可能导致杀身之祸的文字。
众所周知,清初的文字狱是相当严酷的,而这些文字狱中相当一部分,恰恰与干隆皇帝授命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同时。根据统计,干隆一朝一共兴起文字狱100多起,而在编纂《四库全书》的期间,则发动了48起,几乎占到了总数的一半。纪晓岚帮着干隆“ ”中国的古书,最清楚满族皇帝真正的心思。一方面眼见许多著作因为政治问题而被禁毁或者篡改;另一方面,耳闻目睹当代许多文人因言惹祸,或者丢掉官职,或者全家被株连的遭遇,他不能不对文字工作的危险性产生足够的恐惧。因此,智商甚高的纪晓岚只能选择“鸵鸟政策”以自保,从此以后选择谨慎为文之一途,或者干脆就什么也不敢写了。
从另一方面分析,干隆皇帝之所以选择纪晓岚这样一个有声望的汉族大知识分子来领衔编纂《四库全书》,其中固然有满族八旗当中尽皆“绿林大学”毕业,杀人是强项,“修文”则实在拿不出手的考量,但在其内心里恐怕也不能排除通过编纂《四库全书》,让这个汉族的大知识分子接受一次具体而形象的再“教育”的“小九九”。
因此,纪晓岚看起来颇得圣宠,地位显赫,但实际上可能也只是干隆皇帝的一件小摆设而已。对此,干隆皇帝并不隐瞒。据说,有一次,纪晓岚为他的一位犯了罪的朋友尹壮图求情,干隆皇帝闻听之下立即勃然大怒:“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真是一句话惊醒懵懂人,这样的一句“夫子自道”不可能不在纪晓岚的心里留下难以挥去的阴影。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极端残酷的政治环境下,我们看到以纪晓岚为代表的汉族最优秀的脑袋,通过编纂《四库全书》这项工程,一方面秉承主子的意思,极力对古人的著作进行全面的“ ”;另一方面,在“ ”古人的过程中,自己也被有意无意地实施了“精神自宫”手术。一些汉族的知识精英从此只能够像纪晓岚一样,把超人的才情施之于说点笑话、弄个楹联和挖苦同僚的范畴,断然是不会再像其不远的前辈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一样,胸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雄心壮志,潜心于独立思考的著述事业了。
当时,由于清 大兴文字狱,大部分汉族知识分子都将精力倾注到了考证之学中,由此导致清朝的“小学”空前发达。纪晓岚既然身处其间,当然也不能例外。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五《姑妄听之》部分的序言中,他就坦承:“余性耽孤寂,而不能自闲。卷轴笔砚,自束发至今,无数十日相离也。三十以前,讲考证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三十以后,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五十年后,领修秘籍,复折而讲考证。”
这其实是一段多少有点辛酸的“自供状”,它表明了纪晓岚从事文化事业50年来的心理演变轨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纪晓岚在三十岁以后,也曾经有过“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的慷慨激昂的阶段。但自从开始受命领衔编纂《四库全书》之后,这种梦想就完全破灭了,他又重新折回到了繁琐而细致的考证之学里面,从此不再抱“名山事业”的非分之想,而是老老实实地去做他安稳的“观弈道人”的生活去了。纪晓岚的这种选择本身明确无误地传达出这样一个无情的事实:他已经 隆皇帝成功地实施了“洗脑”,由一缕桀骜不驯的“游魂”,彻底变成了一名即使是在写一部谈鬼论怪的杂记时,也念念不忘“有益于劝惩”的“卫道士”角色。
但纪晓岚毕竟不是平常的“池中之物”,他的绝世的聪明才智和旺盛的创造欲望被压抑后,必然会寻求一个新的发泄渠道,这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移情效应”。在这一点上,纪晓岚和魏晋时期司马氏强权统治下许多被压抑久了的先辈知识分子一样,于日常生活中寻觅到的一个发泄渠道就是:食和性。
而且,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征诸历史,像纪晓岚一样被实施了“精神 ”的文人,通常其肉体上的欲望往往是超乎常规的发达。而与之相反的是,那些像司马迁一样被“ 了肉体”的知识分子,则刚好在精神上呈现出旺盛的创造力量。这两者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同时印证了这样一条生物学法则:身体的某一方面被压抑,另一方面就会出奇地发达。
我们看到的纪晓岚正是这样的一个精神上极端萎缩、生理上极端膨胀的生动的典型。
他在被清朝的统治者“ ”了精神和思想上的创造性,变成了一个“精神上的太监”之后,便迅速地滑向了肉体上的纵欲和狂欢,竟然“年已八十,犹好色不衰”,试图用这种肉体的狂欢,来发泄过剩的“力比多”,借以消磨豪情,转移自己内心的压抑和痛苦。
应当说,把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改造成这样的一副德性,无疑是干隆皇帝最大的成功。因为干隆皇帝心里最清楚,纪晓岚再好色好吃,大不了也就是牺牲自己的几个宫女和国库里的一点粮食,一个沦落到整天只知道“御女”和“食肉”的人,对统治者是一点威胁也没有的。从本质上说,这样的人和那些宫中的太监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些只会跟在皇帝的 后面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的角色。因此,当纪晓岚当面说出自己喜欢女人时,干隆皇帝不但不加以责怪,反而大度地派出了自己的两名宫女去满足纪晓岚的欲望。这个干隆皇帝大约可以算得上是“爱护人才,尊重人才”的样板了。
从分析纪晓岚式的“纵欲狂”的病因,我们大约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中国自古以来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宫刑”,一种是直接割掉男人的生殖器官,使之变成生理意义上的“太监”;另一种则是剥夺知识分子独立、自由的思想能力,使之变成精神意义上的“太监”。前一种做法只能让“大丈夫”变成肉体上的中性人,却仍然阻挡不住像司马迁这样的意志强健者,因此还不算太阴毒,也并不算彻底。这后一种精神层面上的“ ”,则只会造就肢体强健的奴才和愚民,不但更具隐蔽性,而且更加彻底,更加行之有效。
本文摘自《大历史的小切面:中国近代史的另类观察》,周英杰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1
说到纪晓岚,大家的第一印象一定是那么风趣幽默。我相信这是看张国立老师演的纪晓岚得出的结论。在剧中,纪晓岚充满了知识、聪明和智慧,很受欢迎。他经常和小沈阳作对,互相挖苦,引得哄堂大笑。但要知道,影视剧大多歪曲历史,真实的纪晓岚并没有张国立老师演的那么让人大跌眼镜。
据史书记载,纪晓岚又丑又近视,但他很有才华。要知道乾隆皇帝是个很挑剔的人,那是对丑人的偏见。现在他绝对是外貌协会的主席,但他能容忍纪晓岚的丑陋,这显示了他的才华。纪晓岚因他的烟瘾而出名,而纪晓岚总是坚持抽烟。同事们偷偷叫他“吉大奉”。有一次,纪晓岚没有时间熄灭他的香烟,所以他不得不把他的烟斗和烟斗藏在他的靴子里,以便出现在神圣的家庭面前。后来,当它燃烧时,纪晓岚忍受着疼痛,直到烟从他的裤腿里冒出来。皇帝问他发生了什么事,纪晓岚回答说:“着火了!”皇帝急忙让他出去灭火,纪晓岚拄着拐杖跑了出去。虽然只是传说,但可以看出纪晓岚的烟瘾有多大!与吸烟相比,吃肉也是纪晓岚的一大爱好。据史料记载,纪晓岚几乎不吃面食,只吃猪肉。而且每顿饭吃的量也很大,有时达到10盘之多。我是多么喜欢它!
除了抽烟吃肉的怪癖,他还有一个怪癖,和电视剧里的形象完全不一样!在剧中,纪晓岚看起来很温柔,但她不是很有女人味,但历史上真实的纪晓岚是很有女人味的。虫鸣漫录记载:“纪文达公日有数妇,五鼓一次,宅一次,午一次,暮一次,卧一次,缺一不可。”例如,据记载在栖霞阁野乘年,纪晓岚有在晚上看东西的天赋,而且他非常好色。“一日不守妻,皮开肉绽。
纪晓岚的怪癖,非但没有为自己感到羞耻,反而成了炫耀的资本,但对他家的丫鬟们来说,却是苦不堪言。根据记录,在纪晓岚编辑四库全书期间,因为工作量大,我有好几天没有回家。因为连着几天没有接近女性的感觉,纪晓岚的身体居然有了反应,开始变得“红眼睛,红颧骨”。龙皇帝来视察时,被这种神情惊呆了。纪晓岚没有隐瞒,把真相告诉了龙。当甘龙知道后,他笑了,然后派了两个女仆来陪他。四库全书编好后,甘龙奖励了他两个女人。
杜小月出生于台湾省,幼年凄苦,三岁被人贩子拐到泉州学戏,从此以唱戏为生,后成名,却常遭人欺负。之后遇到其阿姐莫愁,虽然史实中刘关张诸葛都有媳妇,但是除了因剧情需要只有刘备的夫人出场,其他的几位夫人都被屏蔽了,不知道黄月英是否会哭晕在草庐。杜小月和纪晓岚是工作关系,他俩住在一起即是为了方便工作,也是为了掩盖杜小月和乾隆的情人关系。遂跟随其学武自保。
杜小月这个人其实是影视剧杜撰出来的人物,并且纪晓岚身边也缺不了杜小月的陪伴,但是两个人并没有成为夫妻,更像是一种红颜知己之间的陪伴,彼此的心意也只差一层窗户纸就可以捅破了。她的原型很可能是一位叫沈明轩的江南女子。至于沈明轩是谁不要着急,咱们从纪晓岚的原配马氏说起。
而纪晓岚 和宝宝。只有暧昧关心这一面,但是实际上那个时候哪有男人这么执着的。剧情需要而已,不娶也算是噱头,看点,伏笔。 俩位当朝一品 其一修四库全书 其二军事 财务 深得皇帝欢心。都是文臣 尤其纪晓岚 对古琴书画是痴迷 对书香是敬畏 是喜爱 。
纪晓岚也是正常男人,要说对杜小月没有那么一点动心那肯定是谁都不信。可是纪晓岚为什么放着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大美女不娶,只是命运不公,纪晓岚并不是电视里演的清贫如洗,反而大鱼大肉,妻妾成群,正史书写,其在编纂四库全书时,最后小月留在草堂已经结局了。纪晓岚还要拍第五部,但是袁丽拒绝出演,后来也就无疾而终。彻夜不归,找两侍女侍寝,乾隆为了讨好新来的干部又把小月许配给了新科状元,奈何佳人不幸,小月成了寡妇。
昨天偶然在CCTV-10《百家讲坛》中听了纪连海说的《正说清朝二十四臣之纪晓岚辅助嘉庆登极之谜》,中间提到纪晓岚贺乾隆八十大寿联,现拿来与大家分享一下。
八千为春,八千为秋,八方向化八风和,庆圣寿,八旬逢八月
五数合天,五数合地,五世同堂五福备,至昌期,五十有五年
简单分析一下这个联的含义。
1、“八千为春 八千为秋”出自《庄子·逍遥游》:“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远古时有一种大椿树,以八千年当作春,以八千年当作秋,说明这种树的长寿。
2、八风,八方所吹的风,《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始》:何谓八风?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滔风,东南曰∶熏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凄风,西方曰∶飂风,西北曰厉风,北风曰∶寒风。八方、八风都比喻天下民心,《文心雕龙·乐府》中有“敷训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动八风”的说法。
3、“八旬逢八月”自然是说乾隆的生日是在八月了。
4、五数:《易经》将1至10的十个数字区分成二组,奇数为天数,偶数为地数,天数、地数相加得数字五十五,即“天地之数”。后来战国时期阴阳五行说大行其道,甚至影响易学的诠释,天数为阳,地数为阴,并产生了生数、成数的概念,将一至十之数,以一、二、三、四、五为生数,而生数分别加上数字五,即为成数,这样五就成了生数之祖。五数契合天地,所以五数层出不穷:什么五行、五藏、五色、五音、五志、五味等等。
5、“五福”大家都很熟悉,但要说是哪五福恐怕不见得知道。“五福”说法出自《尚书·洪范》,是指寿、富、康宁、攸好德(注重以德服人)、考终命(不横不夭,能得善终)。 现在据说有一个小学叫“五福小学”,其中的五福是指德、智、体、美、劳,这才叫与时俱进哪。
6、“五十有五年”想来是说乾隆八十大寿那年是乾隆五十五年,也就说乾隆执政的第五十五个年头了。
7、按照传统,五十岁以前的诞生日一般称为“过生日”,五十岁以后才是名正言顺的“做寿”。传统的寿文化源远流长,与民族、宗教、礼仪等有密切关系,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至今仍对人的生活具有较大影响。
8、这是一个联中联,每部分末尾的字也能组成一个联:
春秋和寿月 天地备期年
看看,这个联里面包含了好多学问吧?古代文人的博学由此可见一斑哪。
乾隆二十七年十月,39岁的纪晓岚奉旨出都,任福建学政。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于翰林来说,外放学差无疑是仕途上的一个转折点。纪晓岚对此喜不自胜。登车启程,至济南改乘舟船,沿运河南下,一路行来,山川秀丽,他也不停写诗作赋,后来还结集出版,名为《南行杂咏》。传说在行舟途中,纪晓岚遇到一位老者,亦乘大船南下,还给他送来一张纸条:“我看阁下必是一位文士,现有一联,如阁下能对出,敝船必当退避三舍,如对不出,则只好委屈阁下殿后。”老者的上联是:
两舟并行,橹速不如帆快。
这是一副语意双关联。“橹速”谐指三国著名文臣鲁肃,“帆快”暗指西汉著名勇士樊哙,一文一武,正巧构成双重含义,表面上是说橹不如帆,暗含的意思是说文不如武。纪晓岚深知此联难对,不禁冥思苦想,结果让老者扬帆远去。他到福州后,主持院试,乐声轰鸣。纪晓岚触景生情,想出下联:
八音齐奏,笛清怎比箫和。
“笛清”暗指北宋名将狄青,“萧和”暗指西汉宰相萧何,也是一语双关,一文一武,文胜于武,对得天衣无缝。
一年元宵节,宫廷照例猜灯谜。纪晓岚在文华殿大宫灯上,书一谜语对联请乾隆猜,要求上下联各打一字。这对联谜面是:
黑不是,白不是,红黄更不是,和狐狼猫狗仿佛,既非家畜,又非野兽;
诗也有,词也有,论语上也有,对东西南北模糊,虽是短品,却是妙文。
乾隆辗转寻思,底不可破,窘态难堪,不得已直问纪。纪曰:“猜谜。”乾隆曰:“朕知是猜谜语,现问你谜底。”纪又曰:“猜谜。”乾隆怒形于色,正待发作。纪一见不妙,知不能再卖关子,于是笑道:“黑白红黄都不是,便是青;和狐狼猫狗仿佛而非畜兽,则是‘犭’,‘犭’、‘青’结合便是“猜”;诗词论语有的是“讠”,东西南北模糊是“迷”,‘讠’、‘迷’结合便是‘谜’。灯谜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品玩意儿,但叫人搔首拈须,急断肝肠,岂非妙文耶?万岁已知是‘猜谜’二字,硬要面试微臣,意在君臣同乐耳。”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表白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