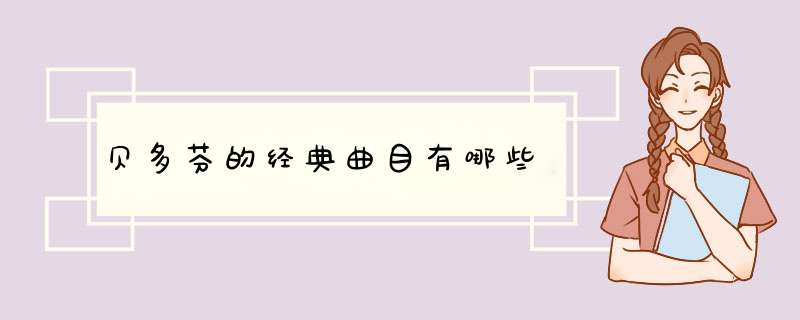
经典作品:
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
c小调第五交响曲《命运》
F大调第六交响曲《田园》
d小调第九交响曲《合唱》
C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
c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
降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
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c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悲怆》
升c小调第十四钢琴奏鸣曲《月光》
f小调第二十三钢琴奏鸣曲《热情》
降E大调第二十六钢琴奏鸣曲《告别》
E大调第二小提琴浪漫曲
《哀格蒙特》序曲
歌剧《费德里奥》
G大调小步舞曲
献给爱丽丝
土耳其送行曲
李斯特 《爱之梦第三章》 《但丁读后感》 《叹息》
贝多芬 《月光奏鸣曲第三乐章》 《暴风雨小调》 《第二十三钢琴奏鸣曲 热情》《G大调随想回旋曲Op129 》《C大调第三钢琴奏鸣曲 Op2 No3 》《c小调第八号钢琴奏鸣曲“悲怆”》一二三乐章
肖邦 《玛祖卡》 《革命练习曲》《第一钢琴即兴曲》 《夜曲第20号》 《G小调第一叙事曲》 《升F大调即兴曲作品36号》
不知道你会不会弹,我10级弹着个不觉得难。琴谱在360里搜
对于贝多芬的艺术造诣评价不能仅用简单的流派进行区分
对于贝多芬(1770-1827),我们似乎已经非常熟悉。辞世一百八十周年以来,贝多芬早已被公认是整个(西方)音乐史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伟人巨匠。汉语世界中对贝多芬的认识,可用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详、颇富文采的话语来作概括——所谓“集古典之大成,开浪漫之先河”。另一句解释贝多芬作品内涵的口号式箴言是——“从痛苦走向欢乐”,同样极富感召力。一般而论,我们好像满足于这样的界定,不再作深究。
众所周知,贝多芬的音乐创作可被划分为早、中、晚三期。而人们最熟悉、上演频率最高的贝多芬作品是他的中期创作。音乐界已经达成共识,1802年之前可被看作是贝多芬的早期。此时的贝多芬虽已在维也纳显露才华,站稳脚跟,但创作内涵和风格尚显稚嫩。1802年至1803年间,贝多芬因患耳疾而经历了痛苦的精神危机——他几近崩溃,并写下一份《海立根施塔特遗嘱》。令后人感佩不已的是,凭借艺术力量贝多芬战胜了自我,并由此步入创作成熟期:也即贝多芬的中期。而标志这场精神胜利的一个物质性结晶,就是那部极为著名的《第三交响曲》(“英雄”)。
自此至1812年,贝多芬在近十年的时间中,创作了一大批彪炳史册的杰作。目前在音乐会中频繁亮相的贝多芬曲目,许多都出自这一时期:包括《“华尔斯坦”钢琴奏鸣曲》、《“热情”钢琴奏鸣曲》、《第五交响曲》(“命运”)、《第六交响曲》(“田园”)、《拉祖莫夫斯基四重奏三首》作品59、《小提琴协奏曲》、《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等等。这些作品不仅上演率极高,而且对后世的音乐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可以推断,鉴于贝多芬的高度艺术成就,即便他在42岁中年时辍笔,他也完全有资格成为整个音乐史中处于最高等级的大师之一。
为此就不难理解,人们往往习惯于从中期风格的角度领会和认识贝多芬。总括而论,中期的贝多芬,典型体现了“英雄”风格。在音乐技术上,贝多芬的追求集中体现为“扩展”:他全方位开掘了当时音乐语言的各种潜能,具体做法如曲体上的大规模扩张,篇幅和长度的超常规扩充,主题/动机乐思的高密度运作,和声张力的大幅度提升,以及节奏冲力的高强度处理,等等。在精神内涵上,这一时期的贝多芬创作,不妨用“人定胜天”来定位。这里的“人”,不仅指集体的人,更是特指个体的人。贝多芬的中期作品,明确体现出强烈的个人主动性和个人英雄主义,从而对人的积极力量作出了全面肯定。这种带有强烈现代感的个人意识,正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思想遗产。贝多芬经由自己独特的个人(生平和艺术)体验,通过声音的特别方式抓住了时代脉搏,发出了时代最强音。这也就是后人每每听到贝多芬的中期作品,依然会感到心潮澎湃乃至热血沸腾的原因。
1812年之后,贝多芬的创作陷入低潮。随后,其作品风格与表达内涵发生了明显转向。“贝多芬的晚期风格”从中艰难浮现,最终在1817年至1818年间成型,并保持至去世。贝多芬最后十年的创作,由此成为独立的风格单位,标志着崭新的艺术境界。
这是怎样一种境界?在贝多芬中期如此壮观的景象之后,如何还能想像更为卓绝的艺术景观?
这正是贝多芬晚期创作所要给出的回答。一个对世界、对人生、对艺术怀有坚定自信并取得全面成功的音乐家,随着暮年来临,重新开启自省之路,通过透彻的再次思索和体察,终于修炼成为洞悉世界、并达至涅盘的智慧哲人。如果说中期的贝多芬体现了“人定胜天”的宏伟气概,晚期的贝多芬就达至“天人合一”的悠远境界。在前者,“人”与“天”对峙,经过硝烟弥漫的抗争,“人”最终胜出;在后者,“人”不再看重外在的胜负得失,而是与“天”求得和解,并最终与“天”达成一致,从而获得内心宁静。20世纪以来,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贝多芬的晚年创作是该作曲家最伟大的艺术结晶,其晚期风格是他最伟大的艺术创造。
针对贝多芬晚期创作的特殊性,倒是一位深谙音乐理路的文学家道出了其中的一丝真谛。捷克作家昆德拉在《帷幕》一书中写道:“在最后十年中……他(贝多芬)已经达到他艺术的巅峰;他的奏鸣曲和四重奏与其他任何作曲家的都不同;由于它们结构上的复杂性,它们都远离古典主义,同时又不因此而接近于年轻的浪漫主义作曲家们说来就来的泉涌才思:在音乐的演变中,他走上了一条没有人追随的路;没有弟子,没有从者,他那暮年自由的作品是一个奇迹,一座孤岛。”
这段话精确规定了贝多芬晚期创作及其风格的历史地位。然而,在国内音乐界文化界,对贝多芬晚期创作的理解深度仍嫌不足。这自然造成对贝多芬整体认识的扭曲。回过头再仔细检视“通过痛苦走向欢乐”和“集古典之大成,开浪漫之先河”的表述,不免会发现其中存在问题。“通过痛苦走向欢乐”这个说法实际上无法涵盖贝多芬晚期创作的精神实质。而“集古典之大成,开浪漫之先河”的表述则基本没有考虑贝多芬晚期的艺术追求。我们将看到,针对古典主义的音乐语言和艺术理想,贝多芬的晚期创作实际上是非常个人化的创造性转型,而且没有任何后人跟进,因而决不是“集大成”。针对浪漫主义的音乐理念和手法,贝多芬的晚期风格其实是一次彻底背离,因而也决不是“开先河”。贝多芬在其晚年,似乎悄然站到了历史之外,进入了似乎难以让后人理解的“孤岛”。
这一过程是怎样发生的?为何发生?让我们将镜头切回到历史的原境中。二、外部生活:时代状况与个人境遇
1812年的贝多芬,已是“人到中年”。因为创作了众多杰作,他在当时就已被公认是最伟大的在世作曲家。他受到维也纳所有政要和贵族的尊重,事业如日中天。
正因为如此,他的下一步艺术方向反而成为问题。贝多芬不时感到困惑不安。
似乎是巧合。欧洲的政治局势与精神气候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与贝多芬的内心困惑相呼应;贝多芬的内心困惑正是欧洲精神氛围的真实写照。就在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遭遇失败,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开始走向末路。这一事件中暗含某种象征意味——法国大革命所代表的启蒙思想开始遭到怀疑乃至抵制。反启蒙的保守思潮开始萌动并逐渐弥漫。此时,理性主义的乐观信念开始动摇。对人性的根本看法与启蒙时代相比,色调开始趋于暗淡。
与此相对应,在音乐艺术中,浪漫主义的观念正在聚集力量,古典主义的理想则面临瓦解。与古典主义讲求比例、平衡的大型结构思维不同,浪漫主义的抒情旋律开始走向前台,局部的色彩成为音乐主旨。韦伯、舒伯特等浪漫主义新人崭露头角。面对这样的局面,贝多芬有些无所适从。总体上说,他不喜欢年轻一代的创作。例如,他看不起罗西尼(认为他写得太快,创作不严肃),对施波尔、韦伯等评价也不高(觉得他们过于花里胡哨,华而不实)。尽管他这时越来越出名,但在音乐趣味上他自觉越来越不为人理解。音乐的发展方向是什么?贝多芬正处在重要的风格转折十字路口。这一阶段中,他的创作数量急剧下降。某些作品中还隐约透露出了准浪漫主义的情怀。如声乐套曲《致远方的爱人》(1816年)、以及《A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101(1816年)。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甚至能够感到某种舒曼式的流动性和抒情趣味。他在投石问路,但还没有决断。
就在艺术风格转折的关口,个人生活中的三个重大事件,对以后的贝多芬具有极为深刻的心理影响,并促使他改变艺术走向乃至人生态度。
第一个事件是写给神秘的“永恒爱人”的一封著名情书。此事刚巧也发生在1812年。这一年6月,贝多芬给一位神秘的女性写了一封极为热烈真挚的情书,在信中称其为心目中的“永恒爱人”。贝多芬身后很长一段时间,关于这位女性是谁,曾有各种猜测。这也成为贝多芬传记研究的著名课题。通过严谨的科学研究,美国的贝多芬权威学者梅纳德•所罗门在1977年撰文证明,这位女性是安东尼•布伦塔诺。她比贝多芬小十岁,出身于维也纳的贵族世家,丈夫是法兰克福商人。她和贝多芬都曾认真地考虑过婚娶成家的可能。但后来的事实是,出于各种原因,贝多芬未能如愿与她终成眷属。从此,贝多芬再也没有与任何女性产生恋情。不难想像贝多芬的内心痛苦和挣扎,尽管他非常渴望人间的美好爱情,他却不得不接受一个残酷现实:他不可能得到正常的爱情生活。
第二个事件是贝多芬的耳疾越来越严重,到1818年,他终于完全听不到外界声音,所以只能启用“谈话簿”来保持与外界的交往(别人问贝多芬的问题,需要写在“谈话簿”上,贝多芬在看到文字后,再作出口头回答)。由于完全失聪,进一步加剧了他的内心孤独和与世隔绝。可以想像,这必定影响到他的艺术创作和人生态度取向。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生平事件是那场著名的官司——争夺侄子卡尔的监护权。贝多芬的一个弟弟在1815年因病去世,身后留下一个未成年的儿子卡尔。贝多芬对弟弟遗孀的品格和能力心存疑虑,非常希望亲自抚养侄子。但是,弟媳妇并不认同贝多芬的意愿。贝多芬与弟媳妇为争夺卡尔的监护权对簿公堂,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诉讼。这场官司对卷入其中的所有人都是精神折磨。贝多芬对弟媳妇无端猜疑,弟媳妇也反过来恶意诽谤。更糟的是,由于贝多芬对卡尔管教过严又拙于沟通,导致卡尔产生抵触和反感,最终卡尔在1826年夏因绝望而开枪自杀(未遂)。此事对晚年体弱多病的贝多芬不啻是极为沉重的精神打击。虽然弟媳妇和卡尔在整个过程中有诸多不是,但不可否认,贝多芬也暴露出性格缺陷,以及他与常人很难正常沟通的行为缺憾。
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状况和生活境遇中,贝多芬走向了他的“晚期”。 三、艺术发现:风格路线与精神境界
1817-1818年,贝多芬在“令人烦恼的境况中”(如他自己在给出版商的信中所说)中,艰难完成了《降B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106。这是贝多芬的晚期风格宣言——他终于作出了抉择。这首作品是贝多芬钢琴奏鸣曲(或许是所有钢琴奏鸣曲)中最困难、最艰涩、最庞大、最深奥和最险峻的巨作。在音乐风格上,它断然拒绝了浪漫主义的散乱放任,不仅坚决回复到古典主义大型曲式的刚正严谨,而且在对音响材料的深刻挖掘和抽象提炼上,甚至体现出某种义无反顾和一意孤行的极端性格。堪称“天籁之音”的慢乐章特别值得一提,在此,贝多芬平生第一次升腾到人迹罕至的璀璨星空,用纯粹音响营造出真正“天人合一”的悠远意境。或许,唯一勉强可与此曲相匹配的人类语言描述,只能是康德的那句名言——“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
通过作品106,贝多芬确定了今后的艺术方向,从而进入晚期创作高峰。至1827年去世约十年时间,他写出了最后的十多部杰作[大致按创作年代顺序,包括晚期钢琴奏鸣曲四部(作品106、109、110、111),《迪亚贝利主题变奏曲》作品120,《庄严弥撒曲》作品123,《第九交响曲》作品125,晚期弦乐四重奏五部(作品127、130、131、132、135),以及《大赋格》作品133],几乎每一部都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其艺术质量之高妙和音乐创意之独特,至今仍让人惊叹不已。
这是“已知天命”的贝多芬留给世界的声音密令和精神遗嘱。这里面说了什么?又是如何诉说的?
从技术风格看,贝多芬的晚期作品之所以不同凡响,那是因为贝多芬对音乐语言的根本性质和运作方式进行了带有强烈“德国式”的透彻反思性处理,并以此在很多方面干脆越过19世纪,直接预示了20世纪现代音乐的理念和精神。例如,针对音乐的主题-动机发展手法,贝多芬一改传统的完整旋律性思维模式,往往将中心的动机构思为一种“细胞式”的、乃至是“基因式”的抽象结构,从而使音乐的运行高度集中,并使音乐的结构极端严密。像《降B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106的第一乐章和末乐章,或者《大赋格》作品133这样的音乐,由于结构的高密度压缩,以至于会让人觉得,这种音乐如果事先没有仔细阅读乐谱并作精致分析,就不可能仅凭听觉真正完全理解其中的艺术匠心。又如,聆听贝多芬的晚期作品,很快就会察觉作曲家对复调手法的大面积运用。如果说在他的中期作品中,复调手法仅仅是一种特别手法,用于特殊效果,那么在晚期创作中,复调就成为全方位渗透的常态。尤其是,赋格——这个复调音乐的代表性象征,这个从巴赫那里传承下来的前辈衣钵,在贝多芬手中一变为既有巴洛克遗风、又有古典式创意的音响建筑。几乎每一部贝多芬的晚期作品都有作为结构重心的赋格曲,它们的功能和意义各不相同,但在属性和写法上又彼此呼应。站在当下立场,对前人的艺术遗产进行创造性转化,并使之融入当下语境,贝多芬在此所呈现的理念和做法,几乎是文化创造的一种典型的(但又是不可模仿的)示范。再如,在《升C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31中,我们看到了对奏鸣曲式最为大胆但又最为老成的运用:外在的架构似乎被抛弃,但内在的精髓却全部保留;而在《迪亚贝利主题变奏曲》作品120中,当那首俗不可耐的圆舞曲主题响起时,听者可能难以想像,贝多芬会针对这个主题将进行怎样不可思议的戏剧性加工和讽刺性嘲弄:这首全部音乐史中性格变奏曲的皇冠明珠,称得上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最佳范例。
虽然应该对音乐进行上述技术和风格层面的解释,但我以为,对于任何音乐,这都是不够的,而对于贝多芬晚期,尤其不够。贝多芬晚期之所以伟大,不仅是因为他在音乐风格上的探索和成就,更为重要的是,他在音乐性格上的开拓和音乐意境上的创造。
在此,需要引入一些有关音乐的根本性美学和哲学思考。贝多芬自己曾有一句名言:“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难道音乐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音乐如何能够像哲学和智慧一样给接受者以人生启示和指引?贝多芬的这句话究竟是随意的戏言,还是认真的思考?笔者以为,贝多芬的晚期创作是一份最高质量的例证说明——音乐确乎可以独特的音响方式,显现世界的本质和人生的真谛。贝多芬的晚期音乐,在绝对的意义上,直接就“是”人生至高境界的音响肉身——也就是说,世界某种最深刻的本源和人生某种最深邃的境界,只有通过贝多芬的声音构造,才第一次而且永恒地显现出来并达到存在,我们由此才能够看(听)到并领悟如此这般的世界本质和人生况味。贝多芬的晚期创作证明,音乐和艺术不仅仅是生活的消遣和装饰,而且在最严肃的意义上,是一种回答人生命题和探索世界本源的途径和方式。
贝多芬的晚期创作究竟给出了怎样一种人生态度乃至世界哲学?我在前面已经谈到,与贝多芬中期相比,贝多芬晚期是从“人定胜天”转变为“天人合一”。在这里,“小我”让位于“大我”。或者说,从“有我之境”转变为“无我之境”。中期的“从痛苦走向欢乐”深化为晚期的“通过磨砺抵达星辰”。怒不可遏的成分明显减少,超然达观的态度占据上风。内省式的深思和超越性的宁静成为基调。勇往直前、势不可挡的冲力依然存在(如《第九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谐谑曲),但在很多时候却平添了几分犹豫和退让(如《升C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31和《A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32的末乐章)。有意思的是,与莫扎特(晚期)境界的宽容、明净、祥和与甘美不太相同,贝多芬晚期的意境更多是深沉、苍劲、敬畏、升腾、欣喜、幽默与和解。考虑到贝多芬当时与侄子和弟媳妇的困难关系,以及耳聋失聪、体弱多病、年老孤独等外在不利因素,他必定对常态的凡俗生活感到深深的无助乃至失望。但同时,他又竭力挣脱尘世俗务的干扰,沉浸在一个理想的或者说升华的世界中,通过音乐写作来为自己也为他人寻找和确定世界意义和人生价值。
他仍然有力量发出最宏大的升腾性号角和民众性颂歌(《庄严弥撒曲》和《第九交响曲》),但他此时最深切的感受来自真正个人化的内心,这特别令人感动并且因此具备了特别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因为,人性在最深刻的底部实际上是超越一切藩篱而息息相通的。通过私密性的宗教情怀(《A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32的第三乐章,“大病初愈者献给上帝的感恩之歌”),通过对人声“抽泣”的原真性展示(《降B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30中的“Cavatina”咏唱曲乐章),贝多芬将自己的日常生活感受提升到了人类生存体验的高度。对民间生活(作品130中的德国舞曲乐章)的乡土性回忆和对18世纪贵族世界的温馨怀旧(《迪亚贝利变奏曲》最后一个变奏),为音乐平添了多维的历史文化向度,使贝多芬晚期的音乐具有更为宽厚的人性温暖。在诸如作品106末乐章引子这样的奇妙音乐中,贝多芬将人的思索状态和过程直接写入音乐之中,从而突破了音乐的常规范畴。虽然很多晚期作品因为乐思的奇特而造成表演上的特殊困难,但贝多芬在最后一首四重奏(F大调,作品135)中,却以举重若轻的幽默方式来处理看似沉重的命题……
这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精神宇宙。贝多芬的晚期创作不仅达到了个人的艺术顶峰,而且也标志着整个音乐发展史的一个制高点。贝多芬一生的创作,通过早中期三个时期的发展,显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精神进步过程,其中不仅揭示出人是什么,而且展示出人应该是什么——尽管贝多芬作为普通人,身上不免带有这样那样的性格弱点和心理缺点,但贝多芬通过自己的音乐创作,用无可替代的音响呈现的方式,让我们听到并认识到,人性所具有的丰富可能性,以及人在理想中能够达到的精神高度。
月光奏鸣曲
献给爱丽丝
c小调小步舞曲
命运交响曲
春之奏鸣曲
田园交响曲
第二号钢琴协奏曲
罗曼史
悲怆奏鸣曲
欢乐颂
随想曲
贝多芬
C大调第一交响曲
贝多芬
D大调第二交响曲
贝多芬
bE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
贝多芬
bB
大调第四交响曲
贝多芬
c小调第五交响曲(命运)
贝多芬
F大调第六交响曲(田园)
贝多芬
A大调第七交响曲
贝多芬
F大调第八交响曲
贝多芬
d小调第九交响曲(合唱)
协奏曲
贝多芬
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贝多芬
C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
贝多芬
c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
贝多芬
b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
序
曲
贝多芬
《科里奥兰》序曲
贝多芬
《莱奥诺拉》序曲
贝多芬
《菲岱里奥》序曲
贝多芬
《爱格蒙特》序曲
其
他
贝多芬
G大调小提琴浪漫曲
贝多芬
F大调小提琴浪漫曲
贝多芬
钢琴奏鸣曲《悲怆》
贝多芬
钢琴奏鸣曲《月光》
贝多芬
钢琴奏鸣曲《热情》
贝多芬
钢琴奏鸣曲《黎明》
贝多芬
钢琴奏鸣曲《田园》
贝多芬
钢琴奏鸣曲《暴风雨》
贝多芬
钢琴曲《致爱丽斯》
贝多芬
土耳其进行曲
贝多芬:《月光曲》《第一交响曲》《命运交响曲》《第一交响曲》《第九交响曲》《庄严弥撒曲》
交响曲:
贝多芬 C大调第一交响曲
贝多芬 D大调第二交响曲
贝多芬 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
贝多芬 降B 大调第四交响曲
贝多芬 c小调第五交响曲(命运)
贝多芬 F大调第六交响曲(田园)
贝多芬 A大调第七交响曲
贝多芬 F大调第八交响曲
贝多芬 d小调第九交响曲[合唱(欢乐颂)
协奏曲:
贝多芬 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贝多芬 C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
贝多芬 c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
贝多芬 降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
序 曲:
贝多芬命运序曲
贝多芬 《科里奥兰》序曲
贝多芬 《莱奥诺拉》序曲
贝多芬 《菲岱里奥》序曲
贝多芬 《爱格蒙特》序曲
其 他:
贝多芬 G大调小提琴浪漫曲
贝多芬 F大调小提琴浪漫曲
贝多芬 钢琴奏鸣曲《悲怆》
贝多芬 钢琴奏鸣曲《月光奏鸣曲》
贝多芬 钢琴奏鸣曲《热情》
贝多芬 钢琴奏鸣曲《黎明》
贝多芬 钢琴奏鸣曲《田园》
贝多芬 钢琴奏鸣曲《暴风雨》
贝多芬 钢琴曲《致爱丽丝》
贝多芬 钢琴曲《月光曲》
贝多芬 管弦乐曲 《土耳其进行曲》
奏鸣及练习曲:
作品49之2(G大调)
之1(g小调)
作品79(G大调)
作品14号之1(E大调)
作品2之1(F小调)
作品14之2(G大调)
作品10之2(F大调)
作品10之1(C小调)
作品10之3(D大调)
作品13号(C小调也叫悲怆)
作品26号(降A大调)
作品27之1(降E大调)
作品28(D大调)
作品22(降B大调)
作品2之2(A大调)
作品2之3(C大调)
作品78(升F大调)
作品90(E小调)
作品7(降E大调)
作品31之3(降E大调)
作品54(F大调)
作品31之2(D小调)
作品27之2(升C小调月光)
作品31之1(G大调)
作品109(E大调)
作品110(降A大调)
作品81a(降E大调告别)
作品53号(C大调,华尔斯坦)
作品57号(F小调热情)
作品101(A大调)
作品111(C小调)
作品106降B大调(锤子钢琴)
1、维也纳初期是1794—1802年。这一时期他写了13首钢琴奏鸣曲。贝多芬音乐风格中最有代表意义的“英雄性”在这些作品中有了初步的体现。诞生于该时期的《悲怆》则是他受到耳聋威胁时的痛苦内心的表白。
2、成熟时期是1803—1814年。这一时期他又有14首奏鸣曲问世。这些作品是贝多芬脱离18世纪传统的重要标志之一,而成为进入他创新阶段的钢琴作品。从《暴风雨》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贝多芬用最平凡的素材和最朴素的音乐语言表达了他那最丰富的情感和最深刻的思想。
3、创作晚期是1814—1827年。这个时期,贝多芬创作了最后5首钢琴奏鸣曲,是贝多芬晚期风格的体现。这一时期的钢琴奏鸣曲不再像早期和中期的作品那样感情激烈、充满矛盾,而给人超凡的宁静与精神的升华。1824至1825年,首次公演《第九交响曲》及其合唱;1825年3月,创作完成《庄严弥撒曲》 。
扩展资料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 (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年12月16日—1827年3月26日),出生于德国波恩,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之一,欧洲古典主义时期作曲家。
22岁开始终生定居于维也纳,创作于1803年至1804年间的《第三交响曲》标志着其创作进入成熟阶段。此后20余年间,他数量众多的音乐作品通过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宏伟气魄,将古典主义音乐推向高峰,并预示了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的到来。1827年3月26日,贝多芬于维也纳去世,享年57岁。
贝多芬一生创作题材广泛,重要作品包括9部交响曲、1部歌剧、32首钢琴奏鸣曲、5首钢琴协奏曲、多首管弦乐序曲及小提琴、大提琴奏鸣曲等。因其对古典音乐的重大贡献,对奏鸣曲式和交响曲套曲结构的发展和创新,而被后世尊称为“乐圣”、“交响乐之王” 。
—贝多芬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表白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