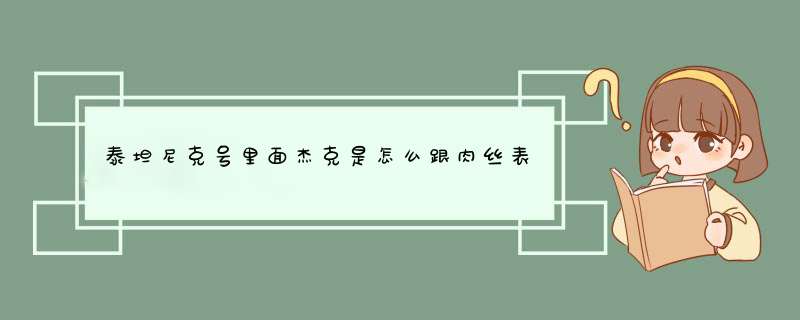
杰克是第一次。表示杰克的羞涩。
两人开车的时候,本来杰克坐在前座,是假装开车逗她开心的,没想做别的。可是他被肉斯拽到后座,杰克一开始也只是搂着,没敢有任何举动,后来肉斯说让他把手放她身上,他还是犹犹豫豫的不敢,肉斯直接拿着他的手按在自己胸部,然后就在一起了。
讲述了富家少女罗丝厌倦了上流社会虚伪的生活,不愿嫁给卡尔,打算投海自尽,被杰克救起。很快,美丽活泼的罗丝与英俊开朗的杰克相爱,杰克带罗丝参加下等舱的舞会、为她画像,二人的感情逐渐升温。
扩展资料:
剧情简介:
1912年4月10日,号称 “世界工业史上的奇迹”的豪华客轮泰坦尼克号开始了自己的处女航,从英国的南安普顿出发驶往美国纽约。富家少女罗丝(凯特·温丝莱特饰)与母亲及未婚夫卡尔坐上了头等舱;另一边,放荡不羁的少年画家杰克(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饰)也在码头的一场赌博中赢得了下等舱的船票。
罗丝厌倦了上流社会虚伪的生活,不愿嫁给卡尔,打算投海自尽,被杰克救起。很快,美丽活泼的罗丝与英俊开朗的杰克相爱,杰克带罗丝参加下等舱的舞会、为她画像,二人的感情逐渐升温。
1912年4月14日,星期天晚上,一个风平浪静的夜晚。泰坦尼克号撞上了冰山,“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面临沉船的命运,罗丝和杰克刚萌芽的爱情也将经历生死的考验。
—泰坦尼克号
从侧面的镜子里往外看
——李浩访谈
张鸿:人们喜欢给新出现的事物和现象冠名,文学评论界也一样,就如“七十年代生作家”。当然,这个命名标志的是作家在年龄上的相对一致,而我感觉这 一代的写作呈现一种文学的多元倾向,这体现在题材和个性化的写作方式上。李浩,你也是这一批作家里的一员,能说说这一代作家的成长及将会抵达一个什么样的 境界吗?
李浩:在我看来,以代际来冠名有它的道理,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那个时代所共通的某种共性,特别是在接受上。但,我觉得,这样的冠名多少也意味了一种无 能,因为它只抓住了特别浅表的一个所谓“共性”而没有把握住特征,而命名的有效,应当是在对“特征”的把握上。你觉得呢?我不反对如此冠名,但我习惯上并 不用它。我愿意看到更多的“个人”,无论他是哪一个时代的,哪一个国度的,我愿意,把莎士比亚和君特•格拉斯,把布鲁诺•舒尔茨、莱辛和鲁迅、王小波一起 放置。它们在我的书架上可能是同一排。
至于这一代人在写作上的多元倾向,我觉得是好的,写作从来不应过于一致,写作更应当是用自己的方式让“自己”呈现,在这点上,我恰觉得,其实我们这一代人 做得还不够,很不够。如果非要按代际来分,说我们的问题的话,我觉得,我们(这里包括我,我的话都属于部分对自己的自省)这些人,和现实、现世贴得太近, 文学理想的普遍缺失,思考深度不够,和生活过于和解,冒险意识普遍较弱……它的确是存在的。而我们的媚俗心,和“八零后”比较未必会弱。我很希望这一代 人,包括还在写着的“五零后”“六零后”,还有“八零后”,能写出让我惊异的、对我的审美构成溢出的作品,能写出丰富复杂、让人沉思、值得反复阅读的书, 它有,但是太少了,太少了。我想以后在一个所谓的市场条件下,这种文本可能更为稀缺。
我很难说一代人会如何,能够如何,我大约只能看到大家已经做到了如何,从这个“如何”中展开我的个人预期。我觉得,这一代人之中肯定会出非常不错的大作家 的,如果机缘合适,而自己又有足够的清醒,能出影响世界文学的作家也不一定。对于展望,说实话我并不乐观,我对整个世界的文学也不够乐观。人类在浅薄化、 物欲化,娱乐致死,这大约并不是一件好事,起码对文学如此。我只期待于个人,期待有新质的东西在我面前呈现。
张鸿:你作品中的人物都没有具体细节的描写,比如外貌、性格,这使得他们有一种典型性的同时有着更广泛的普遍性,《失败之书》的哥哥,《乡村诗人札记》中的父亲,《如归旅店》的父亲、母亲及哥哥。我读后反倒感觉这种写法成为了你的作品的一大特色,你是有意而为之?
李浩:你真是明眼人啊,是的,我是有意为之的,如果可以,我甚至想抹去它所存在的“民族特征”(现在,我多少倾向于对民族特征的 强化了,当然,前提是,我要表达的依然是普遍的,人性中的共有,所谓民族特征是着附在这个普遍性的身体上的)。为什么如此?这是缘于我对文学的理解,或者 说,是一种个人强调。对我来说,一个完全个体的差异,他有无六指,长不长黑痣都不值得我对重视,对那种“特征突出的个体”(也即所谓的典型性)的发现和展 示可以由其他作家来做,他们可以以此发展他们的故事,但,那不是我所要的,我要做的。我要写下的,我所醉心的,是人类的共性,被掩藏在我们日常和隐秘中的 人性(你看鲁迅的“阿Q”,他如果写下的只是一个个体,而没有对中国人的集体指涉,当然依然是好小说,但可能不会让我那么醉心。我喜欢在人物背后的丰富寓 意,这种喜欢甚至达到了小小的偏执)。所以,我希望,我所写下的,既是这一个,又不是独独的“这一个”,或者说,我尽可能地弱化“这一个”的色彩而强化那 种共性成分,它造成的后果就是,我的小说没有一般小说的波澜曲折,一般小说的故事丰溢,这自然会阻挡一部分的读者在外面。我清楚我所要的,我也必须承担我 的想要所带来的全部后果。
在最初写作的时候,我忘了是看谁的一本书了,他谈到一种“未完成美学”,这对我的启发很大,我觉得,好的小说,应当最大可能地调动阅读者的智力参与,你得 给他留下空间,你要做的,只是标出路标,指向可能的路径(当然,这个可能也许是作家的欺骗)。则臣反复谈过好像是汪曾祺先生的一句话吧,“有话则短,无话 则长”——我个人的理解是,别人能做到的,你在别的小说中能读出的,你可用你的经验对它进行补充的,我尽可能略。而别人做不到的,别的小说中大概还没有的 或者还稀薄的,我则要多说几句。我希望能在故事行进的过程中做到“间离”,不希望我的读者被故事的奇异、新颖或古怪所吸引,我希望在我小说里吸引他的是另 外的那些。相对而言,我更愿意安排一种惯常的、常态化的故事,先减少阅读者对故事起伏和如何结局的期待,然后用思和文字的力量将他在阅读中抓住。所以你 看,我的小说,除了缺少外貌描写,个人典型性的“表征”,还缺少景色描写——哈,它也是我有意的忽略,我虽然知道它能给小说带来什么,但,我觉得我们时代 的其他作家,或者在我之前的前辈们都做得够好了,够多了,我还是把心思往别处用一下吧。
张鸿:上次你来广东,我们谈到了“常识”。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常识湮没的年代,人人都知道常识,人人却又忘记常识,或者将常识人为地虚幻化。但常 常正常的事情需要以一种非正常的方式来做,表达常识需要勇气和智慧,而接受常识更需要一种集体的胸襟和宽容。当时你说,你想要的,是通过我们的对话,给文 学以某种的正名,恢复文学应有的常识性?那我们该怎么做才能达到我们理想中的状态?被抛弃的文学常识有哪些?
李浩:记得李敬泽在一个讲座中谈到,他说,我们现在,不得不在常识上反复纠缠,其实我们应当做些更有益的、更靠前沿的事。当时对我的触动真的很大。仔细想 一想,还真是。我们,至于是我,觉得自己很多的时候只是将常识重新审明。我的所有言谈,其实都在文学的常识之内,真的,在这点上,我觉得自己毫无创见。前 段日子和朋友交谈,她提到,米兰•昆德拉在她看来是小说的立法者,我也有大致相同的看法。我在他那本《小说的智慧》的书中很受益,哈,也显得很受害啊。
常识未明,一个原因是有意遮蔽,另一原因则是出于惰性,第三点,是媚俗,所谓的市场考虑;第四,则是一种无知的傲慢。我见过不少所谓的学者,大学生,编 辑,或者小有名气的作家,他们太多人喜欢在“理解之前做出判断”,不肯俯身学习,却以为自己掌握着人类的至少是文学的全部真理。还有一点儿,有些人(这样 的人不是少数),他们向文学要的仅是成功,是世俗的、眼下的影响,要的是红裙和红包,这里面有部分人是懂些文学的,但,他们只有将水弄混才可能在这潭水中 得鱼。于是……
所谓未明的常识,在我看来很多,譬如我们习惯上对“现实”,“现实主义”,“经验”和“时代性”的强调与窄化。在这些词上,我们容易画地为牢,把外边广阔 的空间自我舍弃,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学卖国主义”。现实,并非仅是当下生活的镜像,它还包括内心的现实,天马行空的思绪和幻想,从这点上,现实主义真的 是“无边”的,甚至,内心真实较之外在真实更逼近于我理解的“真实”;谈及“经验”我们似乎只关注于日常生活中那些,经历中得到的那些,而阅读和思考中得 来的那些受到了可怕的漠视;所谓“时代性”,在我看来是一个写作者身上不可避免的胎记,而文学是需要部分摆脱时代性困囿的,优秀的作品在哪个时代都显得“ 异质”……文学是一门艺术,它是常识。可我们是将文学作品当作一件艺术品来要求打量的么?我们是否是更应强调它的艺术质地?
“从怎么写到写什么”,它的本意大约是强调应加强对问题的思考而不仅是迷恋技术……说实话,我不认为谁能掌握严格剖开技术与内容的解剖学。在我看来,技术 与内容之间是互为表里的,密不可分的,你试着抽掉卡尔维诺的叙事技巧,试着抽掉君特•格拉斯的叙事技巧,看他们还剩下什么。至少,文学的魅力会全然丧失。 纳博科夫用一种带偏见的方式说出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空洞的思想是一腔废话,而风格和结构才是一篇作品的精华”。中国画强调“随类赋形”,也就是说, 思想或问题的表达必然会影响到技术的运用——从这点上讲,艺术形式的探索应当是贯穿写作者一生的,言说方式一直是他要面对的问题。作家的立场。
我不止一次听过这样的要求,其实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是不强调立场的,“政治正确”无法保证文学的有效,如果非要作家有一个立场的话,他也应当站在人类一边 ——和黑人白人,欧洲人拉美人亚洲人站在一起。在经典的文学那里,它们提出的问题是整个人类所面对的问题,“活着还是死去”是针对全人类说的,“我从哪里 来,我是谁?我到哪里去?”这样的提问也是普世性的。好的小说,它需要悲悯的不只针对穷人也针对富人,不只针对卖炭翁也针对外表强大的帝王。
“要写中国化的小说”——当年博尔赫斯也曾受到这类的非议。他还专门写了篇《阿根廷作家和传统》的文字为自己辩解。他说,许多被称为阿根廷传统经典的文学 并不是最具备阿根廷本土地域特点的,正是这些有着“溢出”的作品反而丰富了阿根廷的,高乔的传统。是的,按照这种自我窄化的逻辑,莎士比亚是不应写爱尔兰 故事的,因为他是英格兰人;意大利的卡尔维诺也不应写《看不见的城市》,因为那里出现了中国皇帝;卡夫卡不能写《美国》,也不能写《中国长城建造 时》,……《红楼梦》并不像当时的传统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也和中国传统小说有巨大差异,强调所谓“中国小说”“本土经验”的时候是否 应当将这些已成经典的作品也一并删除?
实际上,一个作家写什么对什么感兴趣是由他个人心性所约定的,而不应当是人为规范的结果,要求写作的方式和所谓题材实际是对艺术的践踏和漠视。无论他用哪 一种方式写下,无论他写下的是哪一个地域的故事,优秀的作品都会汇入到本民族的经典之中,成为传统的部分。“我被这部分作品深深打动了流下了泪水”——简 单的情感打动并不属于文学品质的固有指标,它不标明一篇作品的优秀——这应当是常识。写小说不等于写故事,是常识吧,可似乎越来越多的作家明知故犯;小说 不单纯负载道德的评判,不充当真理代言人的角色,这是常识吧,有众多的评论家却非要“将鞍子套到头上来”(王小波语),要小说家歌颂真善美,要小说家负载 非文学非艺术使命,要小说家如何“代言”……
张鸿:从一个女性文学研究者的角度来看,我欣赏的是文学作品中那种男性的视角,从容、大气、智慧、哲思,当然会有一些小小的机智巧妙,及个人的色彩 在里边。但我所了解的国内的这样的男性作家不多,有,但不多。也许我过于偏狭,但“好的作家一定是个思想家”(张炜)。你认为呢?而诗人多多也说过:“思 想,是弱的,而思想者,是那更弱的。”他们的话矛盾吗?
李浩:在我的阅读中,我可从来不分男作家、女作家,在我背后的神中,有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玛格丽特•杜拉斯、普拉斯、莱辛等人的位置,我将她们放在和那 些男作家并齐的位置上,打量她们的文学,用的也是基本同样的眼光。没有谁会因为她是女性而遭受苛责,当然也不会有谁因为她是女性而得到更多宽容。在我这 里,所谓“中国作家”和“西方作家”的区分也不太存在,我只愿意看到好的作品,我会把我的赞叹给予它,无论它是谁写下的。
“好的作家一定是个思想家”,对。这是常识。这是一个显见的常识,尽管它受到了某种忽视甚至诋毁。但常识在那儿,我们看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这个常识就明 确而坚固地在那里。至于多多说“思想,是弱的,思想者,是那更弱的”,应当说也是这样的常识,一种思想如果成为一种权力甚至具有了霸权性的话那它就值得怀 疑和警惕了。他们俩人的说法没有矛盾,在我看来甚至是一种统一。
作家对生活,对世俗,对人类的影响是弱的,一直是弱的,卡夫卡写下的人类境遇并没有因为他的写下而有大的改变,而贝克特,品钦,埃梅,布莱希特……这些名 字,只是为人类的内心,为人类的幽暗境遇加入了些许的微光而已。但,我们不能因为它的微小而对它过于忽略,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病症:我们期待它成为太阳 一样的强光,它达不到,我们就转向对它忽视甚至绝望……(我们对文学的要求是否也过于功利了些?包括,对思想的要求。我们也得明白,“小说家并不奢谈他的 思想”)这些文学的,文化的,文明的因子会慢慢渗入到人类的进程中,细胞里,虽然这一过程肉眼肯定看不见。何况,文学文化的无用之用也不应忽视,它应当得 到重审,一次一次。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艰晦的,但,对一部分期冀智力搏弈的人来说,却能体味其中蕴含的美和妙。哈,我得承认,我读不懂维特根斯坦,我 更多对他的生活和趣味感兴趣。他说,他在临终前说,我想告诉人们,告诉上帝,我从事了一项我喜欢的工作,它对我有意义。哈,文学,有时也得这样想:我写 作,它对我有意义。它是,首先是对自我的表达,是自我对世界的认知。进而,它也关于整个人类。
张鸿:在去年我与王棵的访谈中,我们谈到了“艺术野心”这个词,我就已经感觉到了他的那种“野心”的存在。你俩相比,我感觉王棵很“温柔”,因为你对我说过:“男作家,更应当有世界野心的。”你为你的野心所设定的目标是什么?
李浩:王棵比我聪明,他不会像我这样张狂。但我一向不惮袒露自己的野心,为此也遭受过不少的嘲笑。他们的嘲笑有道理,是的,我没有做到我想要的,我还有很 大的距离,但,我一直是在向这个目标努力的,有时,觉得自己都有点儿“岳不群”。我的野心,还是用原来的回答继续这个回答吧:在一个群贤毕至、牛人云集的 会上,我谈到我的野心,我说,现在大家谈到卡尔维诺,博尔赫斯,米兰•昆德拉,我很想兴奋地告诉你,他们是我的老师。我希望有一天,大家再谈起他们,我有 些平静,那是我的哥们儿。哈,我想做,影响作家写作的作家。这个影响,我也不希望我仅限于中国,虽然我对外文一无所知。米兰•昆德拉说,一个作家,如果他 的写作只能被本民族所理解,那他是有罪的:因为他造成了这个民族的短视。我觉得他有道理。
我说他们是我老师,大家可以理解;我说他们是我哥们儿,大家觉得我过于狂妄。哈。我承认。但,我说是我哥们儿的时候,不只是希望我的名气如何,我希望能获 得那样的名声,但,它对文学来说,不重要。我希望的是,我有能力和勇气和他们进行平等的、隐秘的、坦诚的交流,我希望我有能力和他们在文学、思想上进行对 话,交锋,对抗和相互理解,我希望,如果跻身在他们之间,我的说出让他们也不能漠视,而不仅仅是出于礼貌。博尔赫斯在一首诗和一则访谈中都这样提到,“天 堂,应当是一座图书馆的模样”。哈,这也是我的天堂。在这座图书馆里,我愿意用我的心,用我的力,用我的全部智慧和才情,和那些我敬仰的文字进行平等交 流,可能,也会有小小的争论,面红耳赤一下。
这个野心,其实比获得什么什么奖,比有怎么样的名声的野心更大,我承认。
张鸿:鲁迅文学奖、庄重文学奖,无数的写作人对此寄予无限的热望,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作品之外的因素存在。但你得到了?为什么是你?又改变了你的什么?文学给了你什么?
李浩:我的得奖是个意外,对我来说,我很感谢那些给予我鼓励和帮助的老师、评委和朋友,真的很感谢。对于文学,我一直有种感恩,我觉得,我给予文学的很 少,而文学却给予我很多了。至于作品之外的因素,哈,我不知道是什么,你的所指,但就我而言,我没有在作品之外加入任何其它因素。我可以非常坦荡并负责任 地声明,鲁迅文学奖我得的是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组的十一个评委,我一个都不认识。要说“不认识”也显得假,我认识李存葆,汪守德,但这个认识是,我参加 过某个一百多人的会议,他们在台上讲完就走了,我记住了他们的名字和样子,他们却没看我一眼。
陈建功、何建明是在领取鲁奖和召开青创会的时候认识的,后来再去北京参加个会议,我和陈建功老师打招呼,他又不认识我了。哈哈。我也挺满意这种状态,我也愿意在我心里不露声色地对帮助我的人表达感激。
为什么是我?我还真不知道。我说过,我得奖,大约证明,天上不光能掉馅饼,还有可能掉下林妹妹。那么,我似乎也可以身说法,标明它的某种公正……
得奖,改变了我生活中的一些,譬如,我得到一些刊物的重视了,我的稿子大家也看一两眼了,我的文学观点也有了更多的表达机会……哈,不过,文学和得奖之 间,不应当存在什么改变的关系,我不会为得奖而改变我的写作方向,那更不会因为得奖而改变了,你说是吧?文学,是文学,而不是文学场,更不是成功学。文 学,有一个恒定的目标和高度在那里,它值得一生去追寻,我只要奔向它就是了。不过,得奖,多少可能会免除一些吃不上饭的忧虑,让我更安心地想文学内部的事 儿。我想,在如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我的写作可能会重新遭到漠视,可能有些作品依然发不出来,对此我有心理上的准备,虽然小有不甘。
张鸿:你曾告诉过我,卡夫卡、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对你的影响极大,你用了一个词“背后的神灵”,那你详细说说,他们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二十年前,这些大师也广泛地影响当时的还很年轻的作家,如今他们已经步入中年,你觉得这些大师对你和他们的影响有何不同?
李浩:我想先说他们共同的影响,然后再分开去说。一是,他们告诉我,文学是“个人”对世界的打量,它承载着对时间,命运,哲思,生活,存在之谜的勘探,承 载着对人性细微和世界之阔的勘探;二是,他们告诉我,凡墙皆是门,文学有着一种天生的自由,好的文学,往往在惯常认定“此路不通”的地方延展出了自己的枝 繁叶茂。写作,应当探寻它无限的可能性,从而建立起只有小说能提供的,建立起属于个人的声音。三是,他们的小说,是在道德悬置的地方生出的,它们的声音都 不是强势的,也正如多多的那句诗,思想,是弱的,在他们的小说中你可以读出思想的忐忑,摇摆,无助,面对的痛苦……第四点,他们让我领略着艺术的美妙。从 形式到思想。我喜欢,美妙的“汉语”。
卡夫卡的小说给我的教益很多,我无法一一说全,如果归纳,我想一是看世界的眼光,我透过他的眼看见的是我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对我构成笼罩;二是将人 性中一直被忽略、掩藏下的点的发现,它本来很轻,本来很细,但在卡夫卡的显微术和放大术里,它长大了,样子就像一条庞大的恐龙……哈,米兰•昆德拉所提到 的“卡夫卡式”,对我影响也是很大的,后来我喜欢布鲁诺•舒尔茨大约也和卡夫卡的存在有关。同时,卡夫卡至少告诉我,梦和现实可以是一体的,粘着的,同 时,表达梦的文学未必需要幻美,文学的“彼岸性”未必需要以“牺牲”你对此世的真切认知为代价。意塔洛•卡尔维诺,他的启示是:一种在我看来滞后的旧形式 (线形的、故事套盒式的故事结构)同样可包含和容纳无尽的现代性;写下理想、梦和幻想的书可用童话的方式来完成,思考之重未必就是文字之重;再就是,后来 的卡尔维诺,所做的只是和自己的智力进行博弈,他不再对所谓的人类说话,哈,这也是我的文学理想啊。博尔赫斯所给我的,不只是形式,不只是什么叙事圈套 (这是技,不是本和源),而更是:他竟然可用小说的方式来说在日常生活逻辑之外的玄思、哲学,在他之前,这种玄思和哲学可能无法进入到文学,它是另外学科 里的东西。如果不是他的存在,这些你可能真的无法想象。在一篇小文中,我谈到,“我相信有许多人在抱着一种‘先期热情’去阅读博尔赫斯的,但他们最初会有 我一样的不适:他的小说不是我们惯常以为的样子,我们依据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经典阅读所建立的审美和认知体系(假如确有这一体系的话),在面对他的写作 的时候近乎全然失效,博尔赫斯溢出了我们旧有的审美,溢出了我们习惯认为的‘小说的样子’。他的小说带有某种的‘灾变性’——在他之前,我们很难想象玄思 会成为‘小说的’,并且是核心,持续的核心。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为我们发现并展示了这种可能。”——这是我醉心于他的原因之一。当然,我背后的神 灵还有很多,至少有三百位吧,也不只是小说家,也有哲学家、画家、社会学家……他们一起丰富了我对文学和世界的理解与想象,丰富了我的审美,丰富了我的生 命与生活。哈,现在,我致力于将他们变成“我自己”。
张鸿:评论界把你定位成了“先锋作家”,按先锋文学的那些特征来衡量,我看还是有一些相异的。你如何看你的“前辈”?中国的“先锋文学”与外国文学有没有什么渊源或传承?
李浩:我绝不反对将我看成是什么“先锋作家”,当然我也不期待从这一标识当中赚取什么好处,在鲁奖的获奖感言中我也说,这个奖,三分之一是幸运,三分之一 是奖励给日渐式微的先锋文学,最后的三分之一,才是给我那篇小说的。在我或者许多的“我”看来,文学本身就具备天然的先锋性,因为创新,因为探索,因为冒 险。你不能总写那些跟在小说之后、跟着大众的思考和理解之后的所谓小说,因为它不能给文学增添新质,而这点儿,这个“新质”,是文学存在的首要理由。你可 以选用最古老的形式、最古老的讲述方式来写小说,但,那个“新质”必须存在,成为一个硬核儿。我们把“先锋文学”只理解成是“形式探索”是非常片面的,尽 管它相当需要形式探索,并且是显著的特征。你说我与“先锋文学”的相异,我也绝对认同,前提是你把前面已有的“先锋文学”看成是一个固态的、不再延展的文 本样式。我的相异出自于一种自觉,我必须在前面已有的基础上继续冒险和前行,写作,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在我看来不应当具有“趋光性”,它要在有光的地方叉 开,向着暗处试探……我希望,我最终的写作,能摆脱所有旧有的(包括我背后神灵的)一切规约,成为“林外的树”,显现出独特来。李敬泽说我,你李浩觉得自 己是个野兽,其实你已经是家畜了——我已经在不同的场合引用他的这句话了,我觉得,这是对我的棒喝,说明我在冒险上,前行上依然不够。重提这句话,我是让 自己能够记住。
如何看待我的“前辈”?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我文学的老师和“父亲”,我承认,我在余华、杨争光、苏童、格非、孙甘露、莫言、北岛、顾城、海子、欧阳江 河、杨炼等人那里学到了很多,特别是余华,他漂亮的随笔教会我如何认识和识别小说的美,文字的美。没有他们而有我,这不可想象。我一直对他们报有敬意。这 个名单其实可以无限地列举下去。后来,我也在阿来,王小波,王小妮,路也,蒋韵,包括像则臣、吴玄、苏瓷瓷、李亚等人那里得到许多,这个名单里,有七零后 也有八零后。我觉得一个作家,应当尽可能地敞开,去学习、体味他人的好和妙,然后用自己的方式方法改造它,让它滋养你的成长。吃了羊肉未必会长成羊,那样 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可是,这一常识,在我们许多作家、批评家那里却屡遭悖反,真不知道他们脑子怎么长的。
至于先锋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关系,我觉得是一种脉承,是一种“接轨”,关于这点儿我们在八十年代已经说得很多了,已经是常识,只要回头翻翻旧书就够了。在文 学文化上,我觉得最好的处理方式应当是鲁迅的“拿来主义”,无论是谁的,无论它出自哪里,只要是好的,于我有用的,我就拿来,我就把它当成是滋养。布鲁姆 在他《影响的焦虑》中引用了歌德的一句话,难道一位诗人的所有前驱和同时代人的成就不应该属于他么?当他发现前面有花朵时为什么要畏缩不前而不去采撷呢? 只有把他人的财富拿来为我所用,我们才能创造出一点伟大的成就来。——何况,这个拿来并不造成他人财富的减少,反而可能是种增加。
我想,任何一个有理性、有审美的人也能够了解,叙事文学的主根脉在欧洲,他们发展得相当完备,真的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在这点上,我觉得我们更应向拉美的 作家学习:他们学到了欧洲现代的叙事经验,然后把这一经验加以发挥改造,来书写那一隅的独特和丰厚,这才有了拉美的“文学爆炸”,这才有了对欧洲文学的反 哺。我多希望,中国文学,或者加上日本、土耳其、韩国和泰国,我们在遵守 “世界文学公约”的前提下实现对西方文学的反哺……至少,我们应当这样致力。我还得重复米兰昆德拉的那句话,一个作家,如果只书写他本民族的人才能理解的 东西,那他是有罪的,因为他造成了这一民族的短视。这是常识。哈。如果在这一前提下打量我们的文学……
我承认我从来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他叫安德鲁·林肯(Andrew Lincoln) 英国演员。1973年9月14日生于英国伦敦。在**《真爱至上》中,他的表演让人难忘,圣诞夜的一句"enough”也成为经典台词,被影迷称为最为浪漫的暗恋与表白。近日,安德鲁·林肯确认出演《行尸走肉》主角,该剧已于6月在美国开拍。
还出演过:
《行尸走肉第二季》(2011) 《行尸走肉》(2010) 《反击》 ( 2010) 《达格南制造》(2010) 《真爱至上》 (2003) Mark
《爱无可忍》 (2004) TV Producer。 《我对你保密的事情》 (2007) DC Rae。 《呼啸山庄》 (2009) 埃德加林顿Edgar Linton。 《Moonshot》 (2009) Michael Collins。 《芳心终结者》 (2010) Jonathan。
这是孙伯伦的《一生,一程》的歌词
有人说听到了爱而不得的爱恋。歌曲哀而不伤,字里行间都是令人动容的温暖,用歌声勾勒出时间最宽的维度,在平行的时空重新审视生命中错过的一切。
一生很长,有些人只能陪你走一程,有些人一旦错过了就是一辈子。
我想很多人都会有爱而不得,断了不舍的爱恋。不敢勇敢,不敢开口,最后错过了爱的人,遗憾的过一生。
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暗恋的对像,有些人勇敢了,有些人错过了,有些人失败了。有些人留遗憾了。
前段时间的时候遇见了曾经喜欢很久却不敢表白的人,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渐渐的退出了对方的生活,重新遇见了犹如初见,多了一份冲动,为了填补确实的遗憾。
他说如果当初我勇敢一点,我再坚持一下,也许我们久走在一起了,可惜没有如果,既然遇见了那是缘分,那就弥补一下遗憾,勇敢一次。
有人说:“人生至少要有两次冲动,一场奋不顾身的爱情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好像这样的人生经历才算完整,才精彩,很多人都是以你为曾经的遗憾所以才有了后来的冲动。
有人后悔没和喜欢的人表白,有人后悔没有和喜欢的人去一趟旅行,有人后悔放弃了曾经的梦想。
但是迫于生活的压力,很多的美好都成了遗憾,留在了未来。
前段时间的时候看了一部迪士尼的一部动画片《飞屋环游记》开篇前几分钟,不少网友都在感叹,也想拥有这样的爱情,也想和喜欢的人白头到了,也有不少人悲叹,把喜欢的人弄弄丢了。人生就是这样,我们一边遇见,一边又不断的错过。看了这部**,我觉得且行且珍惜。因为遇见真的不容易,有个爱你的人更加不容易。
短短几分钟,有人说已经泪崩了,已经哭得止不住了,我想大概是有过爱而不得,得了丢失的感情才有如此的心情吧。
影片并没有煽情的情节,故事讲述的是一个从小想当探险家的卡尔·弗雷德里克森,遇到了有同样梦想的女孩艾莉。两人就因梦想命运被捆绑在一起。
艾莉告诉卡尔想去南美洲失落的“天堂瀑布”的险境的愿望,从此艾莉的愿望就成了卡尔的愿望,两人一起挣钱,希望有一天能抵达南美洲,好不容易攒够了钱,迫于现实的压力,让两人的愿望一天天推迟,直到老伴艾莉去世,都没有如愿,这让原本不善言的卡尔性格变得怪癖起来,更加的沉默寡言。原本以为卡尔去天堂瀑布的愿望会成为遗憾,谁知道,在一次误伤人,被迫传送去养老院的卡尔,舍不得自己的小窝。舍不得丢掉所有的回忆,于是萌动了一个想法,用本质的物品变成让房子飞起来的翅膀。成千上万个五颜六色的氢气球带着房子飞向憧憬的地方。这应该也算叫梦想的启航。有些事情就是需要一些冲动,才会实现久久都实现不了的愿望。
当遮掩气球的帐篷掀开时,色彩斑斓的气球全部腾飞起来,将卡尔的屋子平地拨起并共同飞向空中。正当他独自享受这伟大之旅时,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结果他发现他最大的“恶梦”就在屋外一个过分乐观,自称为“荒野探险家”的8岁小男孩罗素。但一切已为时已晚,卡尔不得不带上小男孩一起踏上这惊险刺激的探险之旅。罗素也真正的踏上探险之旅。
历尽千辛万苦,最后终于和他的七彩飞屋降落到一直梦寐以求的地方。逗逗和凯文的加入让整部影片都活跃起来。有会说话的狗,和爱吃巧克力的稀有鸟,科幻又梦幻的存在。它们的出现,所经历的事,让卡尔的性格也有所改变。
卡尔来到飞天瀑布之后遇见了曾经年少时喜欢的偶像,可是相处过之后才知道,偶像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差一点就断送了自己的命,还好有逗逗相助,凯文的救助,这才脱离险境,因此卡尔也对凯文和逗逗的态度有所改变,变得友善了。
小男孩罗素对卡尔说:探险和自己想像中的不一样。
很多事都事需要我们亲身经历过一次才能领悟真谛。有些美有些人事需要你去感受一次,相处一下,才有所了解。相处过之后才会知道这个人的品性。有些地方去过才会带给你不一样的心情。
旅行不过事想要找一条通往内心的路,领略不一样的风景,拥有不一样的心情。
看过很多类似画面唯美的动漫**,我觉得都能带给我轻松愉悦的心情。如果你也想放松一下,可以看看这种画面唯美的**,丰富一下视觉也好,我们一边遇见一边再见,如若遇到喜欢的就牢牢抓住,别让你的青春留遗憾,如果有想去的地方,就腾个时间,存好钱,好好去放松一下,努力一下去完成还没完成的梦想,哪怕失败了也没关系,起码你有努力过,争取过,青春不留遗憾。
如果觉得生活苦的话,就多看看外面的世界领路一下。
摇滚乐的概念
一直以来的悬念
究竟什么是摇滚乐呢?
长头发、皮夹克、破了洞的牛仔裤……也是,也不是;
吉他、贝司、鼓……也是,也不是;
Elvis Presley、The Beatles、Bob Dylan、Nirvana……也是,也不是;
年轻的自由、荷尔蒙的冲动、离经叛道……也是,也不是;
节奏、歌词、旋律、梦想、真实、感觉、狂野、信仰、力量、愤怒……也是,也不是;
……
这些都不是摇滚乐,也可以说都是,那么究竟形而上的具体的摇滚乐定义是什么呢?在我现在看来,提出这个问题就好像是给自己下了个套,就像有人傻到一定要问什么是真正的爱情,这世上有没有真正的爱情一样。因为永远不可能有标准答案。一直以来都没有!每当你发现好像只差一步之遥就要接触到真理的边缘了,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又冒出来了一个岔路,你只要往前在迈一步,就是真理,可这岔路却把你引回到了最初的起点,于是你的思考又要从头开始了。
历史如是说
历史上第一首被打上摇滚烙印的作品是美国的白人音乐家Bill Haley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录制的《整日摇滚》(Rock Around the Clock)。那个时候的Bill Haley穿着笔挺的西装,而且还打着领带,头发梳得油光发亮,如果这样的一个人走在大街上,或者站在现在的舞台上演唱这首歌,一定没有人会认为他是在唱摇滚,可偏偏历史把它定义成第一首摇滚作品。这也没什么奇怪,原来人们还觉得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原来人们还觉得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呢!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时代和我们开的一个玩笑。这样说来,其实任何具体的定义似乎也都是相对的,因为时代在变,人们的认识领域也在不断地随之拓展、改变。
世界上最难的就是为某种事物下一个定义,因为这需要描述的准确、精练。而世界上最容易的也可以说是为某种事物下一个定义,因为你完全可以以自己的理解方式和认识程度给出一个概念。所以很早以前,在国人的传统意识中,一头长发加上皮夹克就是摇滚。然后有人认为,摇滚就是吉他上的SOLO,贝司上的低音,架子鼓上的节奏。现在有人说摇滚是一种精神,可是,也有人说这些都不对。于是带着越来越多的疑惑,我开始翻看有关著作和资料,找到了下面一些所谓的摇滚专家们所给出的定义:
格雷尔·马库斯是闻名遐迩的摇滚名著《神秘列车》的作者,他认为摇滚无非是“一种美国文化”,比如埃尔维斯·普莱斯利无非是“把作为美国人的感受戏剧化,把这种感受的含义、价值和美国生活的利弊作形象的表达”。
卡尔·贝尔兹则在他那本《摇滚故事》中视摇滚为“民间艺术”,一种下意识的俚语表达方式。
查理·勒特称摇滚为“城市之声”,认为它是都市少年们创造的新音乐呐喊。
乔纳森·艾森则在《摇滚时代》中称摇滚为“对西方文化之伪善的反叛……是一种深刻的颠覆形式”。
戴夫·哈克《物有所值》中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分析摇滚,认为它是“工人阶级文化”;而保尔·约翰逊则在《新政治家》重视摇滚为资产阶级的阴谋,其目的是招安潜在的革命者,使他们“沉溺于其中而麻木不仁,懒散不堪并脱离实际”。
理查德·戈尔德斯坦在《摇滚之诗》中则认为,摇滚最重要的特点仍是对青春活力的肆无忌惮的挥霍……
说到这儿,我想起了美国黑人音乐家Chuck Berry用他的作品给摇滚乐下的定义,这同样是一首50年代摇滚乐诞生初期的作品Johnny B,Good。它讲述了一个弹吉他的年轻人走向成功的故事,它以叙事的手法给摇滚乐加上了一个十分诱人的光环,摇滚乐可以让一个普通人走向成功与辉煌。这个普通人可以没有任何的乐理知识,不懂音乐,只要他有理想,只要他勇敢地把自己心里想的唱出来,只要他愿意。另外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发射给外星生物的一艘飞船上,这首歌还作为人类文明的精华被刻录在一张光盘上,用以表达地球人的文明成果。
============================
摇滚的起源
什么是摇滚乐 记得曾经在广播节目上有人问伍佰为什么台湾的摇滚乐不流行,他回答说 : 因为台湾的马路不够大。真是妙答啊!!摇滚乐的解释有很多种,其一就是:一种可以摇的音乐,我是蛮喜欢这个解释,与伍佰的妙答可谓不谋而合。
其实早在30年代初期美国就有首歌叫做Rock&Roll,但当时并没有这种音乐名称。此一名词出现最被大家认识是DJ- Alan Freed于1951年在他的广播节目中首先使用了『摇滚音乐会』这个名称,据说纽约现今仍尊称他为摇滚乐之王。 而又在比尔亨利-Bill Haley和他组的慧星乐团-His Comets以一曲Rock Around The Rock于55年在排行榜呆了8周之久,在此曲大放异彩的推波助澜下,Rock便为世人所熟知,是故有人称1955年为Rock Era,而比尔亨利也得摇滚之父的雅号。
摇滚乐可说是由爵士、蓝调、乡村及西部歌曲等多种歌曲所交织而成的新音乐,但最多的元素仍取自于蓝调,甚至有人说摇滚乐就是把蓝调加重罢了,但我并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比如唱摇滚乐并不须要一定得表现出太多的歌唱技巧,接近撕吼的歌唱方式使得情绪可以全然的喧泄,不若蓝调却是勾起伤心的情绪,就因摇滚乐有此特色,无怪呼在生活普遍不安的当时能将此热潮迅速的漫沿开来,再加上Jerry Lee Lewis等先锋部队的带领下继以猫王的承先、披头的启后得使摇滚热潮漫延了数十年~
起缘于美国的摇滚乐在60年初终于发生了巨变,那就是由The Beatles开始一群英国乐团在一瞬间打进了美国市场,就有人将这件事称为第一次英伦入侵,不过还好当时在美国仍有一些团和他们分庭抗礼,如组合相似披头而曲风充满沙滩、阳光、美女、浪板等加州美景的Beach boys 。此外充满民族曲风的名谣摇滚亦紧接而生,但除了Bob Dylan外,以居尔特或爱尔兰等曲风鲜明的英国歌手亦不乏其中,但在60年代末美国乐团又再次主领大局,那就是以3J(Jim morrison、Jimi Hendrix及Janis Joplin)引领而起的迷幻摇滚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摇滚乐,不过除了Grateful Dead外大部分的迷幻团都相当早夭,在迷幻摇滚势微后,随即迈入风光的摇滚年代。
经由60年代的铺陈,遂使70年代的摇滚曲风丰富至极,由David Bowie引领而起的华丽摇滚就是在70初蹶起的,此外为了不栯于既有的摇滚类型,前卫摇滚、古典摇滚和艺术摇滚也随即而起并成为当时乐界的新像,既而爵士摇滚亦逐渐扬名,此外横跨整个70~80年代最受欢迎且最长寿的重摇滚(重金属)产生了,或许在现在而言Led Zeppelin、Deep Purple、Black Sabbath的分贝soso,然而在当时可说是震耳欲聋的摇滚类型了,此后经由不断的演进heavy metal一直受摇滚迷的青睐,此外在70年代还有跟HM曲风迥异的乡村摇滚、加州摇滚和南方摇滚亦深受欢迎。假若我们说60年代的盛事是英伦入侵,那70年代的盛事非瞬间窜起于70年代末的庞克摇滚莫属,但就如60年代末的迷幻摇滚般,庞克亦不长命。
进入80年代除了初期仍还有庞克风外,夹着70年代余威的重金属便成为领导地位,且几乎风光的80年代都是由重摇滚(重金属)拢断,但他们仍是求新求变的,风格决不同以往,故又有新浪重金属的称号,在重摇滚的强势下,除了蓝领摇滚、流行摇滚和融合雷鬼曲风的摇滚外,要能闯出一片天就得以技巧取胜,所以一些强调速弹和速度的摇滚遂应运而生,而他们引起的风潮亦不容小觑,至今速金仍然有广大的听众。
接着90年代初期引领摇滚潮流的即是西雅图之声油渍摇滚,但随即被充满电子音乐的英伦摇滚所淹没,而因这些来自英国各地的乐团很快的征服新一代的摇滚迷,故将之称为第二次英伦入侵。此外90年代末期带有庞克风或充满电音的的一些另类摇滚也虏获相当多的歌迷。或许摇滚风潮不在,承如麦克阿瑟所言老兵不死只是凋零,但摇滚新血不断产生,电音、工业、嘻哈,或许摇滚曲风已不若以往,但至少是另一种摇滚型态的延续。
给博大精深的摇滚乐分类其实是很愚蠢的,也是片面的、主观的。不过这里分类整理的目的是方便大家对摇滚乐有一个大体上的了解。
硬摇滚(Hard Rock)
60年代初由布鲁斯发展起来的一种摇滚乐风格,具有比较强烈的吉他失真,吉他比较复杂,主音吉他成分较多,布鲁斯味比较浓。最早的摇滚乐队如ROLLING STONES,The WHO,BLOOD SWEAT & TEAR等,以及后来的LED ZEPPELIN,AC/DC,CHEAP TRICK等可以说是硬摇滚乐队。硬摇滚与重金属通常不太容易区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区分方法。有人认为70年代以前的叫硬摇滚,70年代以后的叫重金属;有人认为吉他失真小一点的是硬摇滚,吉他失真强一点的是重金属;有人认为头发半长不短的是硬摇滚,长头发的是重金属;还有人认为美国乐队是硬摇滚(美国人把METALLICA叫做硬摇滚乐队),其他国家的就是重金属;我的看法是节奏吉他表现力比较弱的是硬摇滚,节奏吉他的riff表现力强且成为歌曲主导力量的是重金属。不过也没有必要区分的这么清楚,硬和重,都是我们喜欢的音乐气质啊。
重金属(Heavy Metal)
60年代末由布鲁斯和硬摇滚发展起来的一种摇滚乐风格,具有金属质感的吉他失真和反复的吉他riff是重金属最主要的特征,重金属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而且类别繁多,是70年代以来摇滚乐最大的一个分支,也可以说是最正统的摇滚乐。典型乐队包括BLACK SABBATH(第一支重金属乐队),MOTORHEAD,IRON MAIDEN,SLAYER,BATHORY,DEATH,DARKTHRONE等等。重金属与硬摇滚通常混为一谈,参见硬摇滚。重金属这个词曾经被滥用过一时,80年代不少流行金属甚至流行摇滚都被冠以“重金属”一称,不少人就此被误导。在我们这里,重金属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但有时“重金属”这三个字也专指那些最典型的重金属乐队如OZZY OSBOURNE,ACCEPT,JUDAS PRIEST等,他们通常很难划分到任何一个派别中去,只好干脆就称之为重金属。
金属(Metal)
由于80年代流行金属甚至流行摇滚的泛滥,“重金属”这个词被用得过滥,一提到重金属,人们首先反应到的是BON JOVI,GUNS 'N ROSES这样的乐队,仿佛他们就代表了重金属音乐。于是有不少乐队和乐迷开始反感“重金属”,他们开始将那些更为核心和更为硬朗的重金属音乐称为“金属”乐,也就是说,“金属”比“重金属”更重和更硬朗。不过后来这个词渐渐成为一种气质的象征,从而变得更为抽象而不容易解释,这是一种思想、形象、音色、编曲上的综合特征。譬如我们可以说早期的METALLICA金属味就比较浓,而后来就几乎没有了;我们也可以说在80年代流行金属中,WASP是比较金属的;还可以把BLACK SABBATH称为金属乐队,而LED ZEPPELIN我们顶多能说是一支重金属乐队;JUDAS PRIEST,IRON MAIDEN,OVERKILL等都是具有强烈金属气质的,而AC/DC,DEF LEPPARD,SLAYER的金属气质就弱一些(因为他们分别带有较强的布鲁斯、流行和朋克意味);死亡金属是极端金属中最metal的,因为Grindcore朋克味浓,黑金属的音色太脏——总之,这确是一个难以言传的词。
酸性摇滚(Acid Rock)
即迷幻摇滚,盛行于60年代中、后期,是嬉皮士运动的产物之一。其音乐特色是震耳欲聋的强烈节奏、尖厉响亮的电吉它单人或双人演奏。不同于重金属摇滚,迷幻摇滚没有一定的曲式,即兴演奏的成分较多,其无旋律的音调变化多端,常常富有精彩华妙的表现。"酸性"(acid)一词是迷幻剂LSD的俚语代名词,酸性摇滚因为具有狂热的迷幻音乐特点,故有其名。
艺术摇滚(Art Rock)
一种试图将古典音乐融入其中的摇滚乐。其特征为:结构较为庞大,和声语言较为复杂,并常借用古典音乐中的主题作为素材。 "艺术摇滚"于60年代兴起于英国的一些受过古典音乐熏陶的摇滚音乐家中间。"披头士"乐队的《佩普军士孤心俱乐部乐队》概念专集唱片被认为是"艺术摇滚"的先驱。 70年代中,美国也出现了类似的倾向。"艾莫森、雷克与帕尔莫"(Emerson, Lakeand Palmer)乐队将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改编为摇滚乐;Yes乐队在《接近边缘》中运用了古典奏鸣曲式。著名的美国乐队还有"纽约玩偶"(new York dolls),"路·里德"(Lou Reed)和"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他们不强调摇滚乐与古典音乐的表面联系,而注重音乐逻辑的严密与音乐素材的简练、统一,并由此启迪了朋克音乐与新浪潮音乐的产生。
朋克摇滚(Punk Rock)
70年代中后期盛行的一种流行音乐流派也是著名的音乐运动。其主旨有二:反对富足的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及反对当时的主流摇滚形式和商业的作法。朋克乐的著名乐队是英国的Sex Pistols。它以攻击性的演出、令人讨厌的舞台行为、钉型的发型、撕破的衣服、满口的脏话和政治上不稳定的歌曲为最明显的特征。对朋克乐队而言,精神和坚信常常比音乐技能来得更为重要。在当时,乐坛自鸣得意的倾向威胁到音乐素质的下降,朋克运动的兴起一定程度地振兴了摇滚乐。实质上朋克乐也并非象一贯评论所述的那样无旋律可言,很多精彩的作品对后来者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轻柔摇滚(Soft Rock)
轻柔摇滚产生于70年代初的一种摇滚乐,最初是指那些不用电声乐器,以民谣为基础的摇滚乐。后来,那些虽然使用电声乐器,但旋律优美平滑的摇滚乐也称为轻柔摇滚。这种音乐在美国唱片工业界被称为“中间路线” 广义上的轻柔摇滚泛指一切带有柔和的摇滚节奏并使用电声乐器的抒情歌曲,与Pop(流行曲)相似,港台大部分流行歌曲都可归入轻柔摇滚的范畴。
流民谣摇滚(Folk Rock)
基于民歌的结构和主题,适于民谣乐器和技术演奏改编的摇滚音乐。这种音乐集中体现于Bob Dylan的作品,Bob在民谣音乐中采用了电吉它、鼓、键盘等乐器,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他的音乐在60年代初期受到民谣纯化论者的强烈抨击。另一著名民谣摇滚团体是The Byrds。它受Beatles活泼的流行作品影响,对早期民谣和蓝草音乐进行了改造而独树一帜。 行音乐的一种流派。主要指那些60年后期、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为大家所熟悉的,主流摇滚明星的音乐。
非主流摇滚(Alternative Rock)
一种摇滚音乐形式。是80年代前期和中期,"摇滚团体"与"重金属"停滞不前后发展而成。具有更充满能量且独有特色的声音,不强调音乐的外在表现而强调离奇的音乐独创性。
山地摇滚(Rockabilly)
一种将乡村音乐中的弦乐音响与“节奏与布鲁斯”音乐的曲式结构和歌词风格揉为一体的白人摇滚乐形式。流行于50年代中后期。其特征为:主奏电吉他音响丰满而略带鼻音,低音提琴以手掌击弦,奏出活跃的低音线条,节奏吉他刮奏出清晰的节奏型,不时加入一些简单的打击乐节奏。演唱中常出现灵巧的尖声喊叫、时断时续的阻嗝声,并夹杂着椰榆、嘲讽的语气。 普莱斯利50年代中期在孟菲斯为“太阳唱片公司”灌录的一些歌曲确立了山地摇滚的风格。
雷鬼(Reggae)
一种由斯卡(Ska)和洛克斯代迪(Rock Steady)音乐演变而来的牙买加流行音乐。事实上,很难在洛克斯代迪和雷鬼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
只是后者较前者更为细腻,更多地使用电声乐器和更加国际化。如果说斯卡音乐还只是在美国流行音乐的影响下产生的一种拉美流行音乐的话,那么雷鬼则已发展成为欧美摇滚乐主流中的一种重要体裁了。
重 金 属 分 类
Black Metal 黑色金属
以邪恶、异教崇拜以及撒旦思想为其主要诉求,通常在歌词含有反基督、反宗教的倾向即被归为黑金属,除了传统重金属固定乐器之外,经常会使用其他乐器如钢琴、小提琴,或歌剧的女高音,在歌曲中营造出一股诡异又吓人的恐怖气氛。“黑金属”以来自北欧的重金属团体最具代表性。
代表性乐队:Emperor, Mayhem, Enslaved, Dark Funeral
--------------------------------------------------------------------------------
Death 死亡金属
乐风以“鞭击金属”或“碾核”为其背景演化而成。电吉他快速的反复,几无旋律的和弦,速击狂踩的双大鼓,主唱咬牙不清的低吟狂吼,歌词以死亡仇恨为主题,充满了尸体、内脏、肢解、分尸、奸尸、恋尸癖、食尸、虐待等变态字眼。“死亡金属”以来自佛罗里达州的重金属乐队最具代表性。
代表性乐队:Death, Carcass, Cannibal Corpse, Suffocation
Doom 毁灭金属
节奏和速度都很慢,非常得慢。较不激烈也不大具有攻击性,但仍是相当拥有重量感的音乐。通常具有非常干净的音乐和歌声,但有时也有粗暴野蛮的声音出现。
代表性乐队:Solitude Aeturnus, Cathedral, Candlemass
Glam Metal 华丽金属
通常指一个重金属乐队的舞台表演方式或外在形象以夸张的浓妆艳抹或俊俏的外型来吸引乐迷,这类的乐队大多是偶像团体。“华丽金属”的乐风不会太重,歌词也无太深入之含义,属于较流行的重金属音乐,是主流金属的分支。
代表性乐团:Kiss, Poison, Warrant, Twisted Sister, Motley Crue
--------------------------------------------------------------------------------
Grindcore 碾核
类似“朋克”但极具重量的音乐,主唱低鸣深沉的狂吼咆哮、电吉他超麻辣的音色再加上极快速的反复节拍及密集鼓点,构成一种几无旋律的重金属乐风,乐曲的长度都很短,从两秒钟到三分钟不等。“碾核”为一种极为冷僻的重金属乐风,大多数“死亡金属”乐队都采用此一乐风。
代表性乐队:Napalm Death
--------------------------------------------------------------------------------
Grunge 垃圾(颓废?)
另类摇滚的同义词。起源于西雅图的类金属(metal-like)另类摇滚,基本上Grunge属于另类摇滚而不应归类到重金属之下。
代表性乐队:Nirvana, Pearl Jam, Mudhoney, Alice In Chains
--------------------------------------------------------------------------------
Hardcore 硬核
源自于“朋克”,歌词直言不讳粗鄙不堪,音乐如同噪音一般。
--------------------------------------------------------------------------------
Hard Rock 重摇滚
比重金属乐“轻”一点的音乐。
代表性乐队:Foreigner, Blue Oyster Cult, Heart, Cinderella
--------------------------------------------------------------------------------
Heavy Metal 重金属
“重金属”必须具备狂吼咆哮或高亢激昂的嗓音、电吉他大量失真的音色、再以密集快速的鼓点和低沉有力的贝司填满整个听觉的背景空间,而构成一种含有高爆发力,快速度,重量感及破坏性等元素的改良式摇滚乐。通常泛指传统的主流派重金属或无法分类到其他重金属流派里的重金属乐。
代表性乐队:AC/DC, Accept, Judas Priest, Iron Maiden, WASP
--------------------------------------------------------------------------------
Industrial Metal 工业金属
采用大量冰冷的电脑采样音效,穿插以机械或金属器具的撞击声代替传统打击乐器,加上电子式的节拍,是很象科技舞曲的重金属乐,但仍保留重金属的大量失真效果。
代表性乐队:Fear Factory, Ministry, Nine Inch Nails
--------------------------------------------------------------------------------
Neo-Classical 新古典金属
受古典音乐极深,在重金属乐中加入大量古典音乐元素。
代表性乐队: Angra
--------------------------------------------------------------------------------
Pop Metal 流行金属
在重金属摇滚中加入流行音乐之元素,可说是重金属摇滚和流行音乐妥协结合的折中产品,是极易为主流市场之音乐消费者所接受的重金属摇滚乐。
代表性乐队:Def Leppard, Mr Big, White Lion
--------------------------------------------------------------------------------
Power Metal 强力金属
拥有类似“速度金属”的速度和“鞭击金属”的重量压迫感,但旋律性不及“速度金属”,爆发力也不及“鞭击金属”。
代表性乐队:Pantera, Armored Saint, Wild Dogs
--------------------------------------------------------------------------------
Progressive Metal 前卫金属
风格有别于传统重金属,在歌曲中采用大量复杂华丽的编曲,或在歌词中传达出某些前进思想供听者一个想象思考的空间。
代表性乐队:Queensryche, Fate Warning, Dream Theater
--------------------------------------------------------------------------------
Punk 朋克
歌词中传达某些叛逆思想及对生活环境、文化、社会、政治等的不满情绪,而音乐缺乏协调性无特定风格,是一种相当嘈杂的音乐,通常一群能将乐器弄出声音来的人就可以组一个朋克乐队。
代表性乐队:Clash, Sex Pistols
--------------------------------------------------------------------------------
Speed Metal 速度金属
速度为其标榜的主要特色。经常会和“鞭击金属”产生混淆,通常“速度金属”的音乐较具旋律性,主唱歌词咬字较清楚,吉他间奏富旋律性且快速而流畅;而“鞭击金属”则较缺乏旋律性,完全一速度、重量、压迫感和破坏力并重。通常“鞭击金属”乐队和“速度金属”乐队的乐手们都拥有纯熟高超的乐器演奏技巧。
代表性乐队:Helloween, Gamma Ray, Riot, Rage
--------------------------------------------------------------------------------
Thrash Metal 鞭击金属
速度也极快,具有相当快速的反复节拍(riff),电吉他粗麻的音色刷出剽悍的和弦,极具破坏力及压迫感的速踩双大鼓,主唱粗暴狂吼式的唱腔配合电吉他快速的节奏急速地唱出几无旋律的曲调。“鞭击金属”以来自旧金山湾区的重金属乐队最具代表性。
代表性乐队:Metallica, Megadeth, Slayer, Anthrax, Death Angel, Testament, Exodus, Destruction, Kreator, Coroner, Overkill
欧 洲 金 属 分 类
※黑金属※(Black Metal):
1、启蒙黑金属:在八十年代初,英国的地下重金属乐队Venom(毒汁),在音乐中明确宣扬了对撒旦的崇拜、对战争的渴望,并且是由他们第一次将“Black Metal”这个名词带到金属圈内,为日后的黑金属乐队指明了音乐方向;瑞典同样出现了两支启蒙型的黑金属乐队,Bathory(以吸血女伯爵之名命名)和Celtic Frost(凯尔特人的霜冻),他们的音乐已经基本上具备了原始黑金属的特点:粗糙、暴虐、邪恶!而Bathory的第一张专辑也被誉为是第一张黑金属唱片。不能不提的是丹麦的Mercyful Fate(仁慈的命运),他们虽然对日后的原始黑金属没有什么过多的影响,但是却对歌特黑金属、交响黑金属、歌特金属有着榜样的作用。
2、原始黑金属:原始黑金属的故乡是挪威,第一批挪威的原始黑金属乐队是1983年组建的Mayhem(故意伤害)和1991年组建的Burzum。Mayhem的1993年专辑《De Mysteriis Dom Sathanas》被日后很多新的黑金属乐队视为学习的典范,《De Mysteriis Dom Sathanas》是Black Metal历史上里程碑般的专辑,是Black Metal最最伟大的专辑之一,这里面就是最纯粹的Black Metal。
在1992-1994年间,第二批原始黑金属开始崭露头角,挪威有:Darkthrone(黑暗宝座,虽然Darkthrone1996年就已经组建,但他们正真意义上的原始黑金属作品是1992年才发表的)、Satryicon(森林之神)、Gehenna(地狱)、Immortal(不朽)等等;瑞典有:Marduk、Dark Funeral(黑暗葬礼)等等;其他欧洲国家有:波兰的Graveland(坟地)、奥地利的Abigor、芬兰的Impaled Nazarene(被刺穿的基督教徒)、马其顿的Baltak等。
3、交响黑金属:在第二批原始黑金属乐队活跃的时候,另一种新式的黑金属类型也在不断地发展起来,那就是以大量的键盘演奏来衬托黑暗的气氛,气势异常宏大的交响黑金属。代表乐队有:挪威的Emperor(皇帝)、Old Man's Child(老人的孩子)、Dimmu Borgir(雾中城堡);其他欧洲乐队有:奥地利的Summoning(召唤)、乌克兰的Nokturnal Mortum等。
4、歌特黑金属:这类黑金属主要是在原始黑金属的音乐里加入了歌特键盘、歌特女声、并且注重视觉效果,代表乐队有挪威的Dismal Euphony、意大利的Graveworm(墓穴蠕虫)、英国的Cradle Of Filth(*秽摇篮)。
5、维京金属:这是一种以北欧维京文化为基础的民谣式黑金属,代表乐队有挪威的Ulver(狼)、Enslaved、Einherjer、Borknagar等,瑞典乐队Bathory中后期的作品。
6、旋律黑金属:这是一种新兴的黑金属风格,和旋律死亡金属的意思一样,就是让极端的音乐变得旋律动听,代表乐队是瑞典的Vintersorg、Witchered Beauty等。
7、黑暗金属:这是黑金属的一个分支,运用黑金属的演奏手法及唱腔来抒发自己的感情,一般不含有恶魔崇拜,代表乐队有挪威的Aeternus(沉睡)和芬兰的Thy Serpent(巨蟒);德国的Crematory(火葬场);瑞士的Samael。
※死亡金属※(Death Metal):
1、残暴死亡金属:欧洲的死亡金属中心无疑是瑞典的Stockholm,所以无论是残暴死亡金属还是旋律死亡金属,瑞典乐队都是非常优秀的。欧洲的残暴死亡金属代表乐队有:瑞典的Dismember、Defleshed、Hypocrisy、Gardenian;德国的Krabathor;英国的Carcass。
2、旋律死亡金属:代表乐队有瑞典的In Flames、Dark Tranquillity、At The Gates、Edge of Sanity、Sacrilege以及芬兰的Amo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表白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