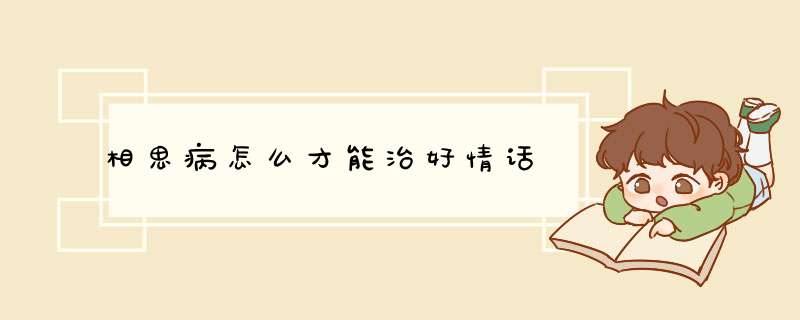
相思病怎么才能治好情话如下:
1、每想你一次,天上就多一颗星星,于是,有了银河系。
2、每一天每一个简单的问候。早安。自己。晚安。也是自己。
3、妹子,帮个忙,我爸妈想要个儿媳妇!
相思病,往往是对某一人产生爱慕之心,却无法与朝思慕想的对象相见时,产生的极度思念,严重者深陷情感之中,整日别无他想,影响到日常的工作、学习、生活,使人陷入一种类似于病态的状况。故此称为相思病。
第一种:是对方尚未知道---即求爱者羞于表达或是其它原因尚未表白时的单相思状态。
第二种:表白后尚未追求成功或者遭到拒绝后,对恋爱对象的单相思。此时往往痛苦伴随着甜蜜。
第三种:是双方相爱,却受制于父母家庭阻挠产生相思。
近年来,随着现代精神医学和心理学的发展,相思病已经引起有关专家的关注,英国的心理学家弗兰克·托里斯博士认为:相思病与精神病很接近,可以导致癫狂、抑郁、迷茫、狂躁、妄想等症状,严重者可致命。
相思病有以下几种常见的类型:第一种相思病是单向的,即单相思。例如红楼梦中的尤三姐,当贾琏逼她出嫁时,她才在无奈之下说出了她爱的人是柳湘莲,可是由于她从来没有向对方表白过,所以对方也没有机会接近她、了解她。最后,柳湘莲仅根据“贾府除了门前的两只石狮子干净罢了!”的传言毅然拒绝了她纯洁的爱情,逼得她自刎以明志,柳湘莲则因自责而出家远行。
1、方案一"如果给你个机会做我男朋友,你要不要"如果他回答要,你就说:我是认真的,你答应了就要好好做如果不要,那你就说"我开开玩笑的,哈哈"。
2、超袭方案二:"猜猜绝关于我你绝对不知道的一件事"否定他的多个答案后,回答"我喜欢你"。
3、霸道方案三:"跟姐混,有肉吃,怎样要不要做我内人啊
4、直接方案四:"你长得很像我下一任男友"。
5、委婉方案五:主动约他去情人场所,然后挽他的手。
6、深情方案六:把想说的话写成告白情书,书信或电子邮件给他,酒醉方案六:假装喝醉,趁机告白(这条比较适合男生,女生自便,亦可使用)。
7、日久见人心方案七:有事没事找他聊天,什么都说,一两个月,自然那个人会开窍(爱情白痴除外)。
8、盘敲侧击方案八:派遣心腹试探,有戏立马出手。
9、亲自出马方案九:制造身体接触,有明显反应就可以直接告白。
10、老套实用方案十:"你觉得我怎样"他回答后,"那我做你女朋友怎么样"。
母亲的牙齿
小时候我总担心母亲丢了,或者被人冒名顶替。每次母亲出门前我都盯着她牙上的一个小黑点看,看仔细了,要是母亲走丢了,或者谁来冒充她,我就找这个小黑点,找到小黑点就找到了母亲,那小黑点是两颗牙齿之间极小的洞,笑的时候会露出来。
母亲每年要去一两次外婆家。外婆家离我家也就四五十公里,但因为跨了省,让我倍觉遥远。母亲出门前我就盯着她牙上的小黑点看,努力记忆得最完整全面,如果回来的是另外一个人,就算她长得和母亲像极,我也要看她牙上的小黑点在不在。
过年前母亲也常出门,卖对联。很长时间里我家都不太宽裕,为补贴家用,爷爷每年秋后就开始写对联,积攒到春节前让母亲带到集市上去卖。十里八乡集市很多,年前的十来天里,每天母亲都得往外跑。年集总是非常拥挤,去晚了占不到好地势;天亮得又迟,早上母亲出门时天都是黑的。如果我醒了,我都要在被窝里伸出脑袋看母亲的牙和那个小黑点。到晚上,天黑得也早,暮色一上来我就开始紧张,如果比正常回来时间迟,我和姐姐就一直往村西头的大路上走,母亲都是从那条路上回来。迎到了,即使在晚上我也看得清那是母亲,不过我还是要装作不经意,用手电筒照一下她的牙,我要确保那个小黑点在。
很多年后我常想起那个小黑点,我对它的信任竟如此确凿和莫名其妙。我确信只有我一个人注意到它,它是证明一个人是母亲的最可靠、最隐秘的证据。我的确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
后来我年纪渐长,事情完全调了个个儿,总出门的是我,念书、工作、出差,我离我的村庄越来越远,进入世界越来越深;我明白一个人的消失和被篡改与替换,不会那么偶然与轻易,甚至持此念头都十分可笑;但是每次回家和出门,我依然都要盯着那个黑点看一看,然后头脑里闪过小时候的那个念头:这的确是母亲。成了习惯。
与此同时,母亲开始担心我在外面的安全和生活。我在哪里,她就开始关注哪里的天气和新闻,一有风吹草动就给我电话,我不知道她是否像我小时候那样,需要牙齿上的小黑点来确认一个人的身份,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母亲总是比儿子担心母亲更担心儿子;我同样可以肯定,在母亲的后半生里,我和姐姐将会占满她几乎全部的思维。
我长大,那个小黑点也跟着长,我念大学时黑点已经蔓延了母亲的半颗牙齿,我不再需要通过一颗牙齿来确认自己的母亲,我只是总看到它,每次回家都发现它好像长大了一点儿。我跟母亲说,要不拔掉它换一颗。母亲不换,不耽误吃不耽误喝,换它干吗?乡村世界里的一切事情似乎都可以将就,母亲秉持这个通用的生活观;我似乎也是,至少回到乡村时,我觉得一切都可以不必太较真,过得去就行。于是每年看到黑点在长大,一年一年看到也就看到了,如此而已。
前两年某一天回家,突然发现母亲变了,我在母亲脸上看来看去:黑点不在了,换成一颗完好无损的牙齿。母亲说,那颗牙从黑洞处断掉,实在没法再用,找牙医拔了后补了新的。黑点不在,隐秘的证据就不在了,不过能换颗新的究竟是好事。只是牙医技术欠佳,牙齿的大小和镶嵌的位置与其他牙齿不那么和谐,在众多牙齿里它比黑点还醒目。我说,找个好牙医换颗更好的吧;母亲还是那句话,这样挺好,不耽误吃不耽误喝,换它干吗?能将就的她依然要将就。别的可以凑合,但这颗牙齿我不打算让母亲凑合。它的确不合适。我在想,哪一天在家待的时间足够长,我要带母亲去医院;既然黑点不在了,应该由一颗和黑点一样完美的牙齿来代替它。
热爱正当年,青葱已做汤
我高二时在河南上学,成绩不好,肯定考不上好大学,想着湖北分数线低,就转了户口,去了一所省重点学校。每月只有一天假,和监狱没有区别。
整个中学时代,我就只有一张单人照,整个人看起来就是拘谨、自卑、迷茫的集合体。
而作为转校生,性格内向又不懂当地方言,自然没什么朋友。
那时我唯一的“狱友”就是阿洲。撮合我们成为好朋友的是同样稀烂的英语成绩。
我们合伙买了一套疯狂英语,每天晚自习在教室里大吼大叫,同学举报后被赶出教室,一起在操场继续大吼大叫。
高考英语我89分,他56分。
那时他帮我追过一个妞,那个妞是隔壁班的,短发很俏皮,笑容很俏皮,打扮也很俏皮。
那年的夏天我坐在靠走廊的位置,每次趴在桌子上发呆的时候,都能看见她从走廊经过。
她从没看过我一眼,但我总感觉她走路带着一阵风,有香气的、活泼的、俏皮的风。我把这个唯一的秘密告诉了阿洲,阿洲说她个小,皮肤又黑,你喜欢她什么?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我说你不懂,这是爱情。过几天阿洲打听到那个妞喜欢他们班的班长,一个高高瘦瘦爱踢足球的帅哥。然后我们组织了一场班级足球赛,我作为中卫上场,一个倒地铲把帅哥的腿弄骨折了。
我和阿洲都受到了处分。
写完检讨,我还写了一封情书。很奇怪,我那么自卑的人,居然会写情书。在这封人生中唯一的一封情书的结尾,我写道:被人喜欢总算是一件好事情,请你不要害怕。奇怪,为什么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被陌生人喜欢是一件让人害怕的事?阿洲把情书送到对方班级的时候,他们班男生纷纷站起来以为是过来打架的。
他嚣张地指着那个妞说:嗨,有人说了情话给你,都在信里!忐忑地等了一周,我收到她的回复,总共只有八个字:先抓好主要矛盾吧。开年后一些名校来校宣传,我看见那个妞站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摊位前询问了很久。
中财就成了我唯一的选择,第一志愿,不接受调剂。然后,我落榜了。我记得那天我妈跟在我身后不停地说:咱分数到了,就是没有上专业线,没事儿的,咱可以复读啊。你别不说话啊,这孩子,你说句话啊!
天下着雨,阿洲也考了所烂学校,打电话叫我去游泳,我没去。从此我们再也没见过面。
那个妞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因为性格内向,因为表白被拒,我也不敢去打听任何与她有关的信息。多年后阿洲结婚让我去喝喜酒,我说你帮我问问那个妞叫什么名字啊。阿洲说你还记得呢?我当然记得。
阿洲和那个妞,是我青春剧里的男女主角啊。而青春,就像一场暴雨后忽然从土壤里冒出来的小葱芽儿,迅速生长,然后被掐断,做成一碗热汤,最后化作一滴泪水。我也曾经无数次猜想:她在哪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还有,她叫什么名字呢?
我给她取过一个名字:林小烟,后来我写过的文字里,女主都叫林小烟。
而现在,我的桌子上放着一份简历。
刘慧娟,湖北人,2009年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毕业。
出生年月日:×年×月×日
专业:××××
工作经历……
****xxxxxxxxxx
照片里的人就是她,那个妞,长得特别像宫崎葵。
曾经对她一无所知,现在看她的简历就像在听她诉说过去这10年的点点滴滴。
生活真奇妙啊!
我爱的是林小烟,不是什么刘慧娟。
胡军,因酒生爱,喝出幸福一生
在《爸爸去哪儿》第三季里,对于节目里五个可爱的萌娃,观众喜爱有加。师弟刘烨曾形容胡军为“糙老爷们儿”。但是,在节目中胡军与儿子康康的相处过程中,观众们这才发现,这位“硬汉”不仅硬气而且细腻。而对于胡军的老婆卢芳,观众更是羡慕。
说到胡军与卢芳的认识,竟是因酒生爱。胡军从中戏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他跑了几年龙套,才获得了做男主角的机会。自己做了男主角,自然对跟自己配戏的女主角比较好奇,他私下里打听了一下,原来女主角是比他晚三届的中戏师妹,叫卢芳。
有一天排练结束后,胡军请卢芳吃饭。喜欢喝酒的胡军忍不住了:“我想喝瓶啤酒,可以吗?”卢芳大大咧咧地说:“喝吧,这有什么呀!”胡军要了一瓶冰镇啤酒,喝到一半的时候,卢芳对他说:“我陪你喝,怎么样?”胡军愣了一下,拿起杯子准备为她倒酒。卢芳说:“你喝你的,我再单独要一瓶。”
就这样,两人你一杯我一杯地喝起来。两个小时过去了,胡军去结账时,发现两人一共喝了16瓶啤酒。胡军体会到了什么叫酒逢知己千杯少。饭局结束,卢芳拦了一辆出租车回去了。
那个时候,卢芳还住在单位的宿舍里,胡军越想越担心,一个醉酒的女孩子,大晚上的,太不安全,他迅速地拦了一辆出租车赶往卢芳的宿舍,敲开门,他发现卢芳正神情自若地坐在沙发上,边织毛衣边看电视。
此番之后,胡军对卢芳真是刮目相看,淑雅又海量,真是一个“奇女子”。而卢芳对胡军的好感也多了起来,她发现,这位师哥不仅表演厉害,看着是位粗犷的汉子,却有着一颗细腻的心。
一来二去,两颗心靠得更近。胡军永远记得卢芳第一次在宿舍给他做过桥米线的情景。虽然只是一道简单的米线,准备工作却如一场晚会般隆重:用瓦罐装上鸡汤,盖上鸡油,放到酒精炉上,桌上已经摆开了8个大盘,里面分别是片得纸一般薄的猪肉、菜心、猪肝……中间的大海碗里一碗白生生的米线。
这是胡军第一次吃米线,他还没有从视觉的震惊中反应过来,鼻子就嗅到了一种亲切又陌生的酒香。卢芳竟然从床底拖出了一个硕大的玻璃酒罐子,里面泡着半罐色泽明黄的水果。卢芳说这里面是云南特产的山梨,最适合用来泡烈酒,醉了也不上头。
两人就着一罐过桥米线,每人喝下了半斤多山梨酒。1999年年初,胡军和卢芳去意大利参加**节,路过罗马广场的时候,胡军忽然跑去买了一束玫瑰,单膝跪地,像骑士一样在众目睽睽之下向卢芳求婚。广场上的老外用最热烈的掌声喝彩,而卢芳赶紧答应下来,用她的话说:“当时就觉得太丢人了,就想着赶紧答应下来,让他起来。”
结婚后,如果碰到问题,他们约定了一个最直接的解决办法:有了矛盾要吵,过错方也不必勉强地来说道歉,自己下厨房做上几个菜,摆上一瓶酒,叫对方一起吃饭,心照不宣地将那些说起来有些惭愧的道歉话用酒代替。可偏偏在这样的对酌中,道歉的话越发说得情深义重。酒杯一端,两个人的话匣子都能很快打开,聊得无边无际。到了最后,都完全偏离主题,犹如他们第一次喝酒吃饭,重新回到初恋的感觉。
疾病城市之拉穆那那城
拉穆那那城是谷木城外围的七十七层疾病圈之一,这里的人患有失忆症,他们忘记了自己是从谷木城来的,以为这是一座独立的城市,并把它命名为“环城”,但是久而久之,他们连“环城”这个名字也忘掉了。被问到这里是什么地方,他们喏喏地答不上来,于是人们根据他们咕哝的声音,管这里叫“拉穆那那”。
拉穆那那城居民的生活总是充满惊奇。从春到夏,每一天都有人“忽然”看见,燕子从南方飞回来了;从秋到冬,每一天都有人“忽然”意识到,燕子好像飞走了。一个人总是再三发现他养的黄猫右脸长着一根黑胡须,还有人总是在同一个不起眼的台阶上崴脚。父母不记得孩子的生日,孩子自己也不记得自己的年龄。不只生日,在拉穆那那城,一切纪念日和节日都不存在。每年冬天第一场雪降临的时候全城放假狂欢,第二场雪降临时又回到工作岗位。有时候两场雪之间只间隔一天,于是这一年,他们就休这一天的假。在这里,必须保证生活尽量简单、尽量有秩序,用习惯来维持城市的正常运转。一旦搞得略微复杂一点,人们的头脑就跟不上了。
拉穆那那城的政治是最混乱的,一个选民持有某种政见,被另一政党用论辩说服,等到真正选举的时刻,他又忘了自己已经被说服了,照旧按照曾经的想法投票。要真正改变一个拉穆那那人的思想非常困难,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毅力,尽管他们也有可能突然之间把自己观点的论据忘记了,但是令人惊诧的是,观点本身却不会从他们头脑中消失,而是成为一座莫名其妙地浮在空中的楼阁,且因为缺少地基,使人更加无从攻击。所以拉穆那那城史上最伟大的二十名改革家,其中有十七名不是成了虚无主义者,就是干脆自杀。——或者是十六名,或者是十八名,或者是他们全部。拉穆那那城的历史记载也是不可信的。
在另外一些层面,尤其是纯感性的群体记忆上,拉穆那那人又极易受到他人左右。据说某年春天,有个安卡基里亚人发现了商机,来这里推销柳树皮做成的口哨,鼓吹这是“童年旧物”,竟然倾销一空。要知道拉穆那那城根本没有柳树,从来也没有过,但是没人觉得这种小小的自相矛盾有什么大不了的。柳树可能枯死了,可能被砍掉了,谁在乎呢?
夏至到来之前,安卡基里亚人就离开了这里,不是因为没有树皮哨可以卖——只要愿意,他可以随便弄些小玩意儿来冒充怀旧玩具,照样赚得盆满钵满,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已经感染了拉穆那那人的失忆症,他开始算不清账,丢三落四,拿不准自己妻子的名字。趁着神智还清楚,他果断地离开了。
然而并不是每个外乡人都有安卡基里亚人的理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或早或晚,被拉穆那那人同化,忘记归乡的道路,继而忘记自己的故乡。他们还以为自己是在这座环形的城市里,吹着柳树皮口哨长大的。
拉穆那那城,一座复杂的城市,每件事都不可信,每个人都是一个谜。他们的方言里夹杂着无数种口音,他们共同信仰的神有数不清的名字。
拉穆那那城,一座简单的城市,生活既规范又平静。统一供应的工作餐永远吃不厌,循环播放的电视剧永远那么精彩。
拉穆那那城混合了真实与虚构,既顽固不化又瞬息万变。明天,它或许不再叫“拉穆那那”,或许它从来没有叫过“拉穆那那”,或许它不是环形的,或许它没有病,或许柳树曾经簇拥着这里的每处公园和街道。或许二十名改革家不是自杀,而是被处死。或许安卡基里亚商人没有离开,而是成为拉穆那那城的一员,日复一日地向旅人讲述着这个他以为是别人、其实是他自己的故事。
好人的心是一朵花
母亲是个好人,她见不得别人的痛苦与苦难。见人有难处,不管认得不认得,都要伸出援手。有好多次,母亲因帮助别人而上当受骗。我们做儿女的,经常劝导母亲,要“吃一堑,长一智”,别再在做好事这件事上“摔跟头”。而母亲呢,仍我行我素,并没有因做好事吃亏而接受“经验教训”,对人仍是一副热心肠。
“一朵花,会因别人一两次有意无意的踩踏,就不再散发出香味吗?”每当我们劝导母亲时,母亲就会对我们这些做儿女的说这样一句话。
母亲的话,也让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最终明白了,好人的心,就是一朵花,一朵芬芳的花,哪怕是受到了别人的伤害,那伤口处,溢出的,依然是那纯正的芳香。
那悲伤藏得那么好,不愿被看见
麻木先生是个严肃的人,大多数聚会的场合中,他都摆着一张冷漠僵硬的脸。
别人开玩笑时,不管在场的其他人笑得怎样花枝乱颤,他也只是轻轻地嘴角上扬,随即笑容便消失了。麻木先生偶尔也会讲个笑话,试图融入其中,但每每都以大家尴尬的呵呵声结束,还伴随着一身毛骨悚然的冷汗。
比如有一次,我们一起在一家上好的西餐厅吃饭,麻木先生一边切着三分熟还带着血丝的牛排,一边乐不可支地说:“最近看了《人体蜈蚣2》,真是太不科学了,除了第一个人能汲取营养和水分以外,后面的人都要靠吃屎活着,连尿都喝不着,哈哈哈……”
现场一阵诡异的安静,只有刀叉刮过盘子发出犀利的响声。
“最前头的人可以吃饭,最后的那个人可以排泄,中间的人最可怜。”麻木先生突然灵感一现,抬头看着大家,“哎,如果换作你们,你们是愿意吃饭还是排泄啊?”
大家沉默,操纵刀叉的手也停在半空。
许久,才有一个朋友张口解围说: “吃饭,呵呵,吃饭好,你看,咱们不是正吃着饭嘛。”
众人皆呵呵,麻木先生得到答案后,满足地低头继续吃起来,切割肉的手法娴熟。
那顿饭,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价格,换来了一晚上的肠胃不适。
哦,忘了介绍,麻木先生是我们的好朋友,是一位非常权威的脑科医生。
麻木先生有一颗胜不骄的心,纵使学术上战功赫赫,纵使我们对他万般崇拜,他对朋友们的态度一直是温和的,不露半点志得意满。
我们喜欢他,除了他人品不错以外,还因为谁都希望自己的圈子里有个挥斥方遒的医生朋友,起码看病可以走后门挂号呀。
而他也喜欢跟我们在一起插科打诨,他说他庆幸自己血淋淋的日子里还能有我们为他增添色彩,尽管他的笑话既生硬又恐怖,但大家也都不在乎。
我们总以为我们足够了解麻木先生,总以为他就是一个手起刀落、满腹医学理论的冷面笑匠,这样的想法一直持续到麻木先生的母亲生病住院的时候。
麻木先生大三那年,他的爸妈突然闪电离婚,传说是麻妈在外面有了别的男人,所以执意离开他们,但具体原因到底是什么,谁都不知道。
麻妈一走就是八年,直到前年麻木先生的父亲去世,麻妈才再次出现在麻木先生的生命里。
对于那段过去,麻木先生和麻妈都只字不提,他们的关系一直都淡淡的,很少说话交谈,麻木先生也很少在我们面前提及他的母亲。
麻妈生病的时候,正赶上麻木先生最忙碌的时候,好几天都见不着人。
我们带着麻妈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检查,很不幸的是,最后的化验结果是脑癌晚期。
朋友把这个悲恸欲绝的消息告诉了麻木先生,他的脸色平静得像一汪湖水,没有任何波澜,看过病历后,他淡淡地说:“安排病人住院吧。”
我们有些震惊于麻木先生的冷静,可又想到他在医院工作多年,见惯了生老病死,或许真的比我们更看得开些吧。
麻妈住进了麻木先生的医院,主治大夫便是麻木先生本人。
我们几个朋友排了班,轮流去医院照顾麻妈,并不是我们有多古道热肠,而是如果我们不去,麻妈通常都是一个人孤孤单单地躺在病床上的。
有一次我们去看她,才发现麻妈打着吊瓶行动不便,已经憋了一个小时的尿。
麻妈入院之后,麻木先生从未在床前照顾过她,他每天带着实习医生例行巡视、检查、提问,对待所有病人都一视同仁,没有人知道麻木先生是麻妈的儿子。
朋友们好几次想劝几句,但都被麻妈拦下了,每次她都用那双日渐混浊的眼睛盯着天花板,语气缓缓地对我们说:“算了,算了。”
麻妈的病越来越严重,她知道自己时日不多,所以每次麻木先生巡房的时候,她都紧紧握住麻木先生的手,不说话,却满眼的悲伤和哀求。
我们都不再劝说麻木先生了,只是安静地守在床边,时刻准备送麻妈最后一程。
在一个暴雨倾盆的下午,正赶上麻木先生上手术,麻妈等了他整整一天,终于还是耗尽了最后一口气,撒手人寰。
“我累了,等不了了。你们都是好孩子,所以请你们……请你们帮我转告他,对不起,请他原谅我……”
这是麻妈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看着躺在太平间、身体已经冰凉僵硬的麻妈,麻木先生在那里站了许久,最后默默地把白布盖起来,转身离开了。
在那之后,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麻木先生。
后来的一次饭局上,他再次现了身,依旧如以前一样,一张冷漠僵硬的脸,笑容轻微,转瞬即逝。
几杯黄汤下肚,麻木先生有些醉了,这是这些年来,我们头一次看见他微醺的样子,眼睛发红,眼神迷离。
他晃晃悠悠地站起来,举着酒杯走到我身边坐下,含含糊糊地对我说:“极光,我特别想对你们说声谢谢,谢谢你们在我妈弥留之际,不离不弃地守在她床前,我没能尽孝,没能送她最后一程,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表白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