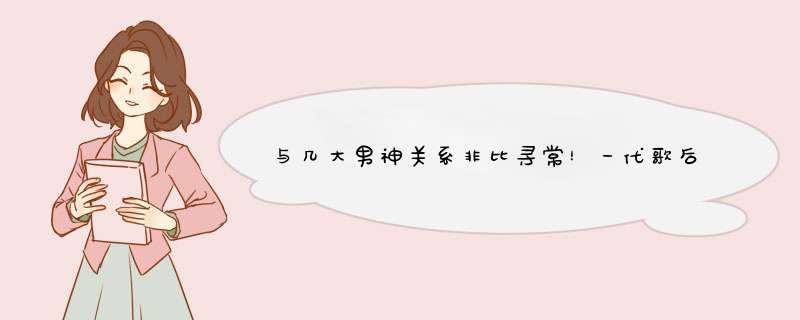
与几大男神关系非比寻常!一代歌后梅艳芳最爱的男人是谁?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自古以来有多少人为情所困,郁郁寡欢,提起当年的“香港女儿”梅艳芳,想必很多人为她感到惋惜,遗憾万分。当时的她美丽动人,事业如日中天,更重要的是歌甜,人品俱佳。正所谓“你若盛开,蝴蝶自来”,明艳动人的梅艳芳毫无疑问成为了众星捧月的女神,一时间追求者无数,可惜情人眼里出西施,梅艳芳和华仔整天出双入对,渐渐的女神暗生情愫,总觉得自己和他是佳偶天成,天作之合,郎才女貌,只可惜妾有意郎无情,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最终刘德华另娶她人,梅艳芳也孤独一个人!
为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如果当初梅艳芳和刘德华喜结连理,或许梅艳芳也不会红颜薄命,韶华易逝。自古以来爱情都是最美丽的邂逅和相守,享受,记得有一次在梅艳芳菲演唱会上,有一个粉丝向她表白,情真意切的想要和她在一起,只可惜梅艳芳说“终究你不是他,爱情也无法将就”。是啊,爱情确实无法将就,否则就是对彼此的不负责任!
虽然当时她和张国荣哥哥关系非比寻常,但是发乎情止乎礼,毫无越距之举。他们之间也只有知己之间的惺惺相惜,没有男女之爱。其实每个人来这人世间一趟不容易,谁不想过的快乐一点儿,但是天意弄人,终究是意难平!
可能是上天可怜这个穿过很多次婚纱,却没有一次属于自己的女孩,在她撒手人寰时,今生最爱的人出现在自己面前,用最温柔的公主抱,最温暖的怀抱让她香消玉殒,也算是圆满!
谈过
以梅艳芳生平故事为蓝本的电视剧《梅艳芳菲》在广东卫视播出一周,反响强烈。很多观众表示,此剧重现了梅艳芳坎坷的一生,情节感人。但是,更多的观众指出,剧中以刘德华为原型的角色“刘家华”太过大男子主义,而且做事冲动幼稚,跟现实中的刘德华形象相差太远。
“这部剧的情节有50%的真实,50%的虚构。”上周本报记者采访《梅艳芳菲》制片人时,对方曾经这么表示。她透露,剧中梅艳芳的化身“方妍梅”爱上“刘家华”的情节来源于真实的历史,但“刘家华”爱“方妍梅”却纯属虚构。不过,显然很多观众还是把这部一半虚构的传记剧给当真了,网上有不少人发问:“难道刘德华和梅艳芳真的谈过恋爱吗”
惹祸桥段
◎爱面子:华仔朝阿梅发火
剧中,刘家华开公司失败,欠了一屁股债。方妍梅帮他还债,他居然大发脾气。有观众评论:“感觉刘家华这个角色把自己的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阿梅辛辛苦苦替他还债,他居然还冲人家发火!这么大男人主义,完全破坏了刘德华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太冲动:为爱情放弃事业
剧中,阿梅突然病倒,刘家华宁可错过开工时间也要送她去医院,结果被导演一怒之下踢出了剧组。观众评论:“真正的刘德华怎么可能这么没头脑如果他连这点关系都不懂得处理,他今天能成为香港娱乐圈的天皇巨星!”
◎太弱势:怕她太强不敢娶
剧中,阿梅问刘家华:“如果我40岁还没嫁出去,你可不可以娶我”结果刘家华答:“如果你不是那么强的话,娶你是我最大的心愿。”不少观众认为,因为怕女人比自己强而不敢要,这根本就是懦夫所为:“真实的刘德华根本就不可能那么弱势,因为他自己够强大!”
观众发火
“这个角色真是太讨厌了!”不止一个观众在网上发出如此评论:“这么糟糕的男人,真不知道阿梅喜欢他哪一点!”一位观众说:“真希望那个人不是刘德华,如果他真是这样,从此我对这个人再无好感!阿梅是一个多好的女人啊,就因为他的自私小气死要面子,白白浪费了大好青春,最后抱憾而终!”甚至有观众冲动地说:“越看越想把刘家华打个鼻青脸肿,方能解我心头之恨!”
大批观众对刘家华的反感,引发了不少刘德华迷对偶像面临形象危机的焦虑。在《梅艳芳菲》的百度贴吧中,刘德华迷纷纷留言,不厌其烦地解释真实的刘德华并没有那么糟糕。还有观众提出,刘家华这个角色其实是根据赵文卓创造的,“因为只有赵文卓才受过阿梅那么多恩惠,而且阿梅一直都比他强”。但是这个观点显然站不住脚,很多观众反驳:“你没眼睛看吗那个演员的长相跟刘德华有九成相似!”
真实往事
现实中刘德华和梅艳芳的相识是在1984年第三届新秀大赛上。暗恋的说法在1990年两人主演《川岛芳子》时传出,据说当时梅艳芳一改迟到作风就是因为刘德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梅艳芳表白说她一直暗恋着一个人,媒体猜测此人就是刘德华。后来她说得更明确了:“嫁人当嫁刘德华。”
多年来,两人相继合作了《富贵兵团》、《九一神雕侠侣》、《川岛芳子》、《战神传说》、《爱君如梦》等**,但十几年的相处,梅艳芳始终与刘德华保持“朋友”的关系,如她自己所说:“爱情总是不确定,又总会受伤,倒不如友情来得有安全感,所以不敢乱想。”但梅艳芳也说,她始终难忘《九一神雕侠侣》中,华仔和她在阳台上茉莉花旁的亲吻。
坊间一直有梅艳芳暗恋刘德华的说法。1995年,梅艳芳与刘德华同台合唱《随想曲》,梅艳芳半自嘲地说:“既然这样,我们就随缘啦,这首歌很适合我们唱的……请收起彼此的爱意,留在心中像纯的酒。”或许因为早已达成共识,两人并不忌讳表达对彼此的关爱。1999年梅艳芳获金针奖,刘德华送了1000朵玫瑰花祝贺。2000年华仔首获金像奖影帝,阿梅强忍亲姐姐病逝的悲痛出席,只为说声祝贺。娱乐圈需要话题,很多活动都会安排两人一起出现。1994年“翡翠歌星贺台庆”,刘德华和梅艳芳跳贴身舞,当时现场奏是就是《婚礼进行曲》。
梅艳芳得子宫颈癌的消息,第一个告诉的人就是刘德华。当时她整天躲在家里不见人,刘德华知道后立刻赶到她家中,花了一晚上的时间说服她接受治疗。梅艳芳最后的演唱会,一连好几场,刘德华担任了其中两场的嘉宾。在第五场演唱会上,梅艳芳说:“就是这个人,自己没时间睡觉,拍戏到半夜还不忘打电话叫我吃药,我真的好感谢你,这个朋友是一生一世的。”压轴那场,两人合唱了《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成了他们的绝唱。2003年12月30日,梅艳芳逝世,开记者会的时候刘德华站在最后,戴着好大的口罩,只露出一双红红的眼睛,身上穿着没来得及换掉的拍新年短片的唐装。
链接其他争议
◎港味不足
有观众指出,《梅艳芳菲》说的是香港娱乐圈的故事,但却没有什么香港味。制片人郑凯南说:“观众说得对,场景有一部分在香港拍的,有一部分在深圳拍———比如第一集中阿梅和姐姐晚上一起去赶场的场景,其他外景地还有广州和中山影视城。因为戏太长,香港治安不允许。如果全部在香港拍,拍摄时间、地点的申请都会安排不过来。”
◎情节穿帮
有观众指出,剧中方妍梅刚出道的时候去音像店,结果店里居然挂着古天乐的专辑海报和周星驰**《功夫》的海报。郑凯南回应:“这是我们拍摄时的疏忽,观众观察得比较细致,其实我们自己直到今天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不好意思。”此外,剧中很多场开车的戏,车子都靠着路的右边,而香港的规矩应该是靠左的。郑凯南说:“这是因为广东人太熟悉香港了,提出这个问题的一定是广东观众,内地观众肯定不会发现。谢谢他们。”
◎演员不像
观众普遍认为,陈炜扮演的方妍梅很出色,但刘德华和张国荣的“替身”贺刚和黄浩则有些欠缺。郑凯南表解释:“贺刚前10集演得很好,后10集因为情节难度增大,可能他把握起来有些困难。贺刚以前完全没有演过戏,而且他比较年轻,但是他的眼神特别纯,这在娱乐圈的演员里是找不到的。至于黄浩然,他在前面几集的戏份不是很多,后面会多一些,到时候就能显出演技了,请大家耐心一点。”
梅艳芳的英雄本色3和胭脂扣是最为喜欢的作品,其中周英杰的飘逸和如花的婉转让人心动不已,可惜佳人早逝,令人唏嘘!<<女人花>>这首歌表述了作为女人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对理想对象的期许,歌声虽含有一丝抑郁,却包含着炽热的情感和感情无处诉说的寂寞,也许这就是阿梅内心世界的表白,阿梅倾注了自己的情感才让这首歌富有了生命深切缅怀梅艳芳!
刘德华只把梅艳芳当妹妹来看待,他们俩才不结婚的。在刘德华和梅艳芳的关系中,其实梅艳芳一直都是自愿主动表白刘德华的。刘德华一直含糊不清,没有承认。因此,这只是梅艳芳的单相思恋情。刘德华对梅艳芳的爱是哥哥对妹妹的爱。
梅艳芳去世前,很多人觉得刘德华对不住梅艳芳,因为她曾多次表达对刘德华的爱。然而,刘德华似乎避而不谈此事,并没有考虑娶了梅艳芳。事实上,我认为这有点像道德绑架。梅艳芳单方面欣赏刘德华只是她自己的事情。
事实上,在梅艳芳的一生中,从刘德华的种种行为来看,他似乎把梅艳芳当成了自己的妹妹。梅艳芳病重时,刘德华经常提醒她半夜按时吃药。即使梅艳芳放弃治疗,刘德华也建议她接受治疗。后来,梅艳芳举办告别演唱会时,刘德华多次与梅艳芳合唱。刘德华已经做了这么多。如果他真的爱着对方,他早就娶了梅艳芳回家过日子了。说白了,刘德华是个好人。他和梅艳芳又是多年的好朋友。只是放心不下她而已。
事实证明,刘德华的确很优秀,当时娱乐圈的很多女明星都以刘德华为择偶标准。包括关之琳、梅艳芳、王祖贤等人都开玩笑说他们喜欢刘德华,尤其是前两个人和刘德华有很多八卦,所以很多人都责怪刘德华是现在关之琳单身的原因。
我觉着是因为两人的性格不合,因为刘德华比较喜欢安静而梅艳芳比较喜欢热闹,人们对于刘德华和梅艳芳都很熟悉,据说当时的梅艳芳暗恋了刘德华很多年,甚至于很多粉丝希望二人在一起,可惜的是梅艳芳并不是刘德华的理想型,刘德华还因为这件事被人们责怪了很多年。
梅艳芳的一生也是很不容易的,可以说唯一给她温暖的就是刘德华了,而且她也说过刘德华是她的理想型,但很可惜的是由于刘德华是个比较喜欢安稳的人,而梅艳芳平时经常喜欢出入迪厅,所以二人并没有走到一起,当时的梅艳芳可是多次表示过嫁人当嫁刘德华,二人的相识也是很美好的,是在一次选秀上,刘德华是司仪梅艳芳是嘉宾,相识也是很戏剧性的。
其实当时的梅艳芳对刘德华是相当满意的,但是我觉着原因可能并不全是因为两人性格不合,可能更多的还是刘德华不喜欢梅艳芳,再就是虽然梅艳芳说过可以为刘德华改变,但是我觉着虽然可以改变,但是改了那就不是原来的她了,而且二人当时的地位是属于女强男弱的,真的在一起之后刘德华承受的压力也不会小。
刘德华对于梅艳芳的感觉更像是朋友,在梅艳芳生病时他会时刻陪伴在梅艳芳的身边并督促她吃药,并且他每年都会去怀念梅艳芳,即使做不成夫妻,有这种朋友也是很好的。
五十多年若有变,早早就变。若不变,多少年也不会变。—李碧华
@自在之思
《胭脂扣》是作家李碧华的成名之作,但从**艺术角度来说它的意义更为深刻。导演关锦鹏特殊的同性身份,使他对女性视角的拿捏细腻完美。他把中国古典文学里那种瑰丽的想象影像化成缠绵悱恻的幽怨氛围,如花浑身散发出来的“阴气”,充满了一种浪漫的凄迷,在整个华语**世界都极为特别和难能可贵。
如花原本是三十年代香港石塘咀的红牌妓女,与世家子弟十二少陈振邦相恋。因陈家的反对二人吞食鸦片殉情,相约手牵手走过黄泉、永不分别。不料死后的如花苦等十二少五十三年未能得见,于是用来生的七年阳寿换来七天的时光,到八十年代的香港寻找十二少。上来后又偶遇一对情侣—袁永定和阿楚帮助她寻找线索。
一个三十年代的女鬼跋涉于时间的长河,在五十多年的时间跨度背景下情深意笃地寻夫,东京大学的藤井教授用“香港意识”的变化来解读这部**。他说时间才是《胭脂扣》的真正线索和主题:是借一个女子穿越于两个时空两种文化的鬼魅爱情,带出香港在历史转折时期的怀旧心理,以及香港人在回归之前对自己文化和身份归属的思考。
01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性的关系只能纳入身份之中
胭脂扣,是用年华记载爱情的象征,爱是耐心,是等待意义在时间中慢慢生成的信物。一只胭脂扣,短暂地扣住了男人一时的情欲,却不能扣住男人一世的守护。
① 如花幽怨痴缠的是她求而不得的身份
中国传统差序格局的社会,每个人都活在社会赋予的身份里,女人尤其如此。没有男人依靠,女人就没有社会地位,更没有生存出路。
青楼对于男人,可以提供婚姻制度、生育功能之外的一个副产品—爱情,十二少找如花,是奔着爱情去的。一副“如梦如幻月,若即若离花”的表白,不可谓不浪漫。两百多大洋送到如花房里的原装大铜床,也是费尽了心思,不可谓不真挚。以至于老鸨不无醋意地说“我做了二十几年的老鸨子,从没见过一个孝子,像十二少这个温心官人这么会孝顺人的”。为了如花十二少和家里断了关系学唱戏,一个有钱人家的公子哥,给师傅倒痰盂、跑龙套、受人奚落,做到这份上,不可谓不情真意切。
如花正是收获了爱情,才动了“找个栖身之处,嫁个好人家”的念想。她自知身份低贱,所以拜访陈家时刻意良家妇女的装扮,并向十二少母亲表明“我和正邦是真心的,不敢计较些什么”,但即便如此卑微,她得到的也是绝望。
传统的社会结构是由不同身份架构组成的,社会身份注意亲疏、同异和是非之辩,男女性关系的最终目的指向传宗接代。十二少母亲一见如花就说“你真是个风尘奇女子……我想大概这就是人家说你们风尘女子的作风吧”,这风尘女子的身份,原本就不在正常的社会结构之中,如花想登堂入室地嫁入陈家,只能是痴人说梦的臆想。
② 十二少摆脱不掉的是他的身份束缚
女人的权力预先被设定在私人领域里,她的活动空间是封闭的,她可能拥有的权力上限非常明确—那就是依靠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女人的战场是对男人的拼杀,男人是目标,是战利品,是输赢的目的。女人的德性与智慧,首先是对男人争夺。男人说女人心海底针,不过是一种调情的戏谑之语,男人才不会真正对这个战场的输赢挂心。
哲学家周国平说:男人凭理性思考,凭感情行动;女人凭感情思考,凭理智行动。思考时,男人指导女人;行动时,女人支配男人。
作为边缘人,如花在主流社会的权力结构里本无一席之地,既然不能让权力低头,那就不如销毁权力。她给十二少酒中另下四十片安眠药,如花一杯,十二少三杯,得不到就玉石俱焚,如花的冷清映照的反倒是十二少的幽怨。
观众感动如花的深情、同情如花的苦情,一个为爱痴狂的女人为爱了却生死,是她逃不脱的宿命,这种解读是观众对这种文化传统之下女人情感走向的基本判断。因此就认定十二少的游离、躲避,是爱得不够情深意笃。
其实从身份的角度,如花既无家人也无社会地位,于是才有痴情背后的倔强与绝决。而十二少却有太多俗世的牵绊,他毕竟是为了爱情赴死了,但他社会身份背后的那些权力,不会让他那么轻易地死去。
五十多年后如花再见十二少,传统附加在男人身上的权力光鲜已然不在,倒是那份陈腐的丑陋让她落荒而逃。五十多年的痴等,原本是心存侥幸地期待权力的俯首和认同,她未曾料想的,是那份她曾经企盼的权力,已然腐朽至世人鄙弃。
③逼死如花和十二少的是封建纲常伦理
女人作为一个完整的命运共同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分少见。中国人的尊卑秩序渗透在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绝对的主权者是不存在的。女人可以享有尊严与权威,但一定是附着在传统的道德机制之上,通过馈赠和男人分享道德利益。
和如花的身份卑微相呼应的,是十二少母亲养尊处优的尊贵。在中国文化的谱系中,女人的身体、性都服从于家庭生活的恒常运转。家庭承载着女人的道德标准,持有对女人形象的发布权。家庭也是文化操作的权力场,女人身处其中,一旦处于权力的核心位置,自会与父权共谋,成为父权的代言人。
十二少母亲不无深意地提醒如花:杭州的女孩子在清明前上山采茶,摘一些最嫩的茶心,放在兜里面,用香汗体温润着带回家,这就叫做乳前龙井……你没听过吗?要用真正女儿身才算矜贵,不过要用处女的乳房湿润过才算得上是极品,我和你就不可以了……
女人是最善于在家庭领域展现自己的生存智慧和治理才华的。这种不能承担宗法道德又不易破坏的男女关系,十二少母亲可谓一出言就把如花置于道德的审判台曝晒了。
严苛的道德规范之中,道德已经内化成女人的本能,内在于女人意识之中的自动书写了。凭借男人,女人才能获得相对的权力运作空间。所以如花才说“一个女人命好就可以找个男人依靠,命不好就只有当妓女”。
十二少母亲言之凿凿地告诉如花“如果你一直缠着他不放,他早晚会回到我身边的”,这是千百年传统给予她的自信。道德编程已经植入了女人的头脑,为家庭、丈夫、儿子而活,一个社会意义的母亲,是相对于父亲的家庭权威的次级符号,她就是这样保证了权威的柔性运转,如花也是深刻认同这个权威性的。所以,逼着他们殉情的,并不是不通晓男女之情的十二少母亲,而是这邪恶的封建纲常伦理。
02身份的唤醒与爱情的迷失,两性关系的重新建构
在五十年的时间跨度背景下,这已不是一个单纯的爱情悲剧故事,而是一种包含在时代更迭下个体认知变迁的情感写照。
①女性的觉醒和男权的解构
尼采认为,男女的幸福感各不相同。他说,男人满足的是“我要”,女人满足的是“他要”。男人从满足了“我”的需要中得到幸福,女人从满足了“他”的需要中得到幸福。
从这个角度来说,如花是一个自我意识非常强大的女性,得不到就带走,而不是得不到我离开。一个名妓,男人堆里成长起来的女人,职业就是哄男人开心。她凄冷哀怨的眼神,是参透了男人薄情后的冷静,如若不然,她怎会有自杀时的杀伐决断。但是一旦看清了真相,她也绝无半点儿留恋。
如花和十二少最终相见在**片场,一个专门制造虚幻的现实地点。当过去和现在在特定的时空相遇,瞬间就让爱情的虚幻性和自我欺骗性现形了。
中国艺术重虚实,此时整个故事的所有“实”指向的其实是最终的“虚”。如花对年迈的十二少说:“十二少,谢谢你还记得我,这个胭脂盒我挂了五十三年,现在还给你,我不再等了。”于是便头也不回地离开。此刻,虚幻的情爱敌不过对俗世的贪恋,湮灭了。此时的如花,也在迷失中被自觉地唤醒,生死不渝的虚假敌不过人性的贪生的本能,爱情消失了,人性回归了。正应了如花最初给十二少说过的“真的东西最不好看”。
五十三年前,如花死去的是肉身,十二少死去的是精神。五十三年后,如花的女性意识觉醒了,十二少代表的男权也早已被时代解构。这场爱情,做了五十多年孤魂野鬼的如花虽死犹生,怅然苟活的十二少却早已死在了过去。
②现代人脱离了身份桎梏,对爱情有了新的解读
西班牙小说家乌纳穆诺曾说:世界和生命里,最富悲剧性格的是爱。爱是幻象的产物,也是醒悟的根源。
传统社会给女人铸造的藩篱,是原本就没有正当社会身份的如花无法飞越的牢笼。在一个性别角色僵化的社会里,无论她怎样粉饰与标榜自己的才情,她也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坏女人,随之而来的打压、诋毁甚至驱逐都不足为怪。
她要跨越抑或翻转传统,自己必须要有更坚强、更决断的意志。想要飞越传统和偏见的鸟儿得要有强壮的翅膀,否则伤痕累累、精疲力竭地掉回地面的景象会更为悲惨。
回到八十年代的如花即震惊又彷徨,她问袁永定和女友为什么不结婚,袁永定回答“有些事没有人逼就暂时不做”。后来阿楚询问袁永定“你会为我自杀么”,袁永定坚定地回答“不会”,阿楚也紧跟着回道“我也不会”。
旧时代的如花愿意为了一段飘渺的爱情舍弃生命,甘愿赌下一生的幸福,那是没有社会身份的女人的不得已。但古典爱情的百转千回终究是美的、是动人的,被感动的阿楚哭着告诉袁永定:做女人真难,尽了力也不知道为了什么,我嫉妒她。她敢做的事,我这辈子也不敢做,连想都没想过。
没有了社会传统的桎梏,现代人拥有了充分的选择自由,爱情倒变得寡淡无味、苍白无趣,如同日常的生活,平平淡淡的没有了色彩。
03如花的个人意识、身份认同的危机正是香港意识、香港认同危机的体现
如花代表着香港的过往,她企图从历史的尘埃中找到一种香港本土的历史认同。
① 如花的矛盾和仿徨也是香港的矛盾和彷徨,她的身份意识始终没有完成
如花追忆曾经在太平戏院和姐妹们看戏的场景,那醉生梦死般的快乐、流光溢彩的奢华,令人心醉神迷。这是借着如花这个“鬼”说出的香港历史,那海市蜃楼般的过去:有颓废艳丽的欢场,有生死不渝的爱情,相形之下,现代的香港却显得色泽苍白。
如花在爱情里的身份迷失,如同香港在文化上的身份迷失。如花初到阳间的时候去袁永定的报馆登寻人启事,袁问她要“姓名、住址、电话和身份证”,她一样都没有,袁问她“大陆人”,她说是香港人。到了她要找的老地方,如花几乎要哭出声来:“我在哪里?这真是石塘咀吗?”
过去靠传统界定身份的时候,如花是没有身份的人,现在用一堆数字界定身份,如花还是没有身份。如花没有向陈旧不堪的传统讨要到权利,她又带着声色俱美的过去向现在寻求认同,结果陷入更大的迷茫。
“我是谁”“我从哪来”“我到哪去”,是香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香港特殊的百年殖民历史,远离中原远离核心文化圈的地理位置,血缘、亲缘文化上它认同大陆,政治上它又曾经属于英国,内心身份的归属至今也没有完成。
② 如花辗转于不同的时空之中,有意追寻香港的历史地位、本土身份,试图建构香港当下的文化品格和身份
**借如花打造了一部民间的香港史,在古今对峙的时空状态下,来找寻和重构“香港本土历史意识”。历史不再是只言片语的猜测、想象和拼凑,我们跟着如花的回忆,看到了一个充满情义的“民间”香港。它虽然早已随着历史的风尘而消逝,却承载着香港人难以忘怀的家园情怀。
如花代表的香港越虚幻,逼真描摹的袁永定代表的现在香港就越贫瘠。古董店老板说那些登塘西妓女青楼艳史的“征友报“以前一分钱一份,但现在值钱了。过去的东西到了现在显出了价值,这是香港人对自己的历史期待。但这些街头小报寄托的集体记忆,塑造出的“香港形象”往往是脆弱、虚幻和自我欺骗的。
在寻找十二少的**片场,导演要求演员飞出来的时候要有女侠的威风,也要有女鬼阴森森的样子,又要像女侠又要像女鬼。这把演员搞糊涂了:怎么演啊?
**人毛尖说:香港意识也正是处于这样尴尬的境地—它悬置在历史和文化中,悬置在历史传统与当下经验中,携带着破碎的历史经验在两极或多极文化之间摇摆不定。香港在历史文化身份上的悬置以及由此而起的焦虑,正是《胭脂扣》所包含的内在阴影。
辗转于不同的时空之中,试图寻找男人依靠、试图求得权力认同的如花,却成了香港寻求自我认同的一个历史符号,成了有意追寻香港的历史地位、本土身份、建构香港文化品格和身份的情感记忆。只是这既非鬼亦非侠,永远悬置在两者之间的状态,却生生把香港推入了今日历史和文化际遇的双重危机里。
结语
梅艳芳凄丽华美地演绎了一出她和张国荣亦真亦幻关系。十二少对如花讲过一句话:“我在老地方等你,你跟在后面来。”这极似一个认真的承诺,在那一年的年尾,梅艳芳步了张国荣的后尘,去了天堂。
这部**不但有轰然崩塌的爱的传奇,轰然崩塌的两个巨星,还有轰然崩塌的一个时代。再看今天香港的困境,已经不仅仅是对痴情爱情不在的遗憾,更多的是对香港至今迷茫于自己身份的悲叹。
袁永定说:我们是普通人,在一起高兴就行了,不至于要弄到殉情吧?没那么严重。对于虚构家园梦的香港人,这何尝不是一句警醒。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表白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