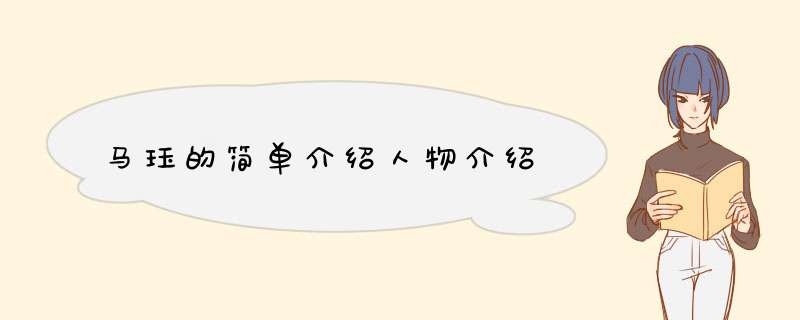
今天小编辑给各位分享马珏的知识,其中也会对分析解答,如果能解决你想了解的问题,关注本站哦。
鲁迅最爱的北大校花,美丽胜过林徽因,为何选择嫁平凡小职员呢?
民国时期的文坛,很多趣事轶闻比现在的娱乐圈还有意思。譬如“校花”,现在这时代从“校花”转为明星的不少,因为一张校园照而走红网络的大有人在,但民国时期,“校花”可不是人人能当的——
复旦校花严幼韵出身名门,浸润于富贵乡,通身优雅气质;杭州女子师范校花王映霞有“杭州第一美人”之称,迷倒无数才子;清华校花郑秀大家闺秀一枚,父亲是大法官,后来嫁给著名话剧剧作家曹禺。
而得到公认的北大校花马珏,出身名门望族书香之家,父亲马裕藻、母亲陈德馨都是著名学者,父亲任北大国文系主任长达14年,与章太炎、蔡元培、鲁迅等文坛大腕交情很深,当年北大红楼有两个“好好先生”,一个是校长蔡元培,另一个就是马裕藻了。
马家和北大百年校史联系紧密,除了马裕藻,还有“四马”马衡、马鉴、马准、马廉也跻身北大,投身教育;马家四代人都读北大,2012年马裕藻曾外孙女孔涛重回未名湖,距当初马裕藻被聘为北大教授,刚好过去一百年。
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大家也能想象马珏的校花之名不光因为外表,还因为她通身的书香气质。1910年,马珏出生于日本东京,父母当时正在留学,后来双双回国,马珏自然也回到国内,然后有了传闻中和鲁迅的一段暧昧缘分。
鲁迅先生作为正面人物,按照国人的习惯他必须是“完人”,不可能有什么暧昧情愫,但实际上,鲁迅也是男子,欣赏美丽有才的女孩实属正常,至于到底涉不涉及暧昧,只能见仁见智。当时,马裕藻任职北大,鲁迅也被聘到北大,两人是同事,又是至交。
马珏进北大之前,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走到哪都引人注目。1915年,还在孔德学校念书的马珏第一次在家里见到了鲁迅,为此她写下《初次见鲁迅先生》这篇文章,发表在《孔德学校旬刊》上。文章的内容非常有意思,可以读出马珏是个真性情的女孩:
“在所看的这些小说里,最爱看的,就是鲁迅先生所作的了。我看了他的作品里面,有许多都是跟小孩说话一样,很痛快,一点也不客气;不是像别人,说一句话,还要想半天,看说的好不好,对得起人或者对不起人,鲁迅先生就不是”
马珏说,自己之前没有见过鲁迅先生,想象中认为他是“小孩似的老头”,喜欢和孩子在一起;没想到15岁初见鲁迅,他却“穿了一件灰青长衫,一双破皮鞋”,手里总拿着烟卷,看起来“又老又呆板”,感到非常惊讶,原来,他是个“老头似的老头儿”呀!
而马珏在书房待得不耐烦要走的时候,鲁迅忽然主动开口,问她有没有看过《桃色的云》这本书。马珏摇头,鲁迅便说,这本书外面不好买,他那儿还有一本,她要是想看,自己可以拿过来。
于是马珏不好走了,因为按照马家规矩,晚辈是要送客的,结果鲁迅一坐就几小时,马珏还小,只觉得呆等着“麻烦”。好不容易鲁迅起身,马珏跟在后面送,鲁迅又回过头来说:“那本书,有空叫人给你拿来呀!”
马珏有些不好意思,送鲁迅到大门口就转身进屋了,不忘在心里暗暗想:鲁迅先生原来是这样一个人!这篇文章发表之后,鲁迅也读到了,他非常高兴,夸马珏写得好,肯说实话,还将这篇文章收入《鲁迅著作及其他》中,频繁送书给马珏。
就这样,鲁迅和马珏开始通信,一通就是六七年。《鲁迅日记》中提到马珏的次数多达53次,其中马珏给鲁迅的信有28封,鲁迅的回信有13封,每当鲁迅去马家,马珏若在,必定要和她说几句话,马珏也在父亲带领下去鲁迅家中玩。
值得一提的是,马珏当年填志愿也问了鲁迅意见。1926年,马珏写信告诉鲁迅,自己想学农。鲁迅回信很快,表示支持她自己的想法。两年后,马珏考入北大,因为马裕藻希望女儿为女权努力,她转入政治系。当时鲁迅对马珏十分关心,为她取号,注意到她生病,马家父女也常探望鲁迅,让鲁迅非常感动。
在北大期间,马珏是被竞相追捧的校花,被形容为“大理石雕出的那么美”,使燕京与清华的校花“粉黛无颜色”,据说每天都有十几封情书悄悄送到,日子一长都能装订成本了。要论容貌,马珏可能还胜过民国女神林徽因一筹,只不过,马珏的人生路线和林徽因截然不同。
可能性格偏低调,爱好偏文艺,马珏最终并没像父亲期望的那样成为大人物,1933年,她嫁给年轻英俊的天津海关职员杨观保,因为顶着校花名头,马珏在当时很受关注,《北洋画报》多次报道,刊登马珏个人照和她的结婚照,在上海的鲁迅也收到马家寄来的结婚请柬。
得知马珏结婚,鲁迅就不再送书给她了,可能因为某种防范意识。马珏杨观保夫妻俩都是知识分子,但并没有很大成就,马珏在上海儿童图书馆工作,一生籍籍无名,杨观保也平淡一生,可能马珏身为校花,最大追求并不是出名,而是有一份稳定的爱情,柴米油盐过一生。
不论怎样,马珏能得到鲁迅先生的青睐必然有过人之处。她聪颖美丽,性情真实,不高调张扬,不图富贵。平凡也是美,马珏的美没有林徽因那样让人惊艳,但细水流长,也算是一道靓丽的民国风景了。
让鲁迅先生暗恋的北大校花马珏,长得有多漂亮?
清末民初,是个盛产美女与女神的时代,美女如云来形容那个时代,是相当恰当的。诸如潘素、唐瑛、林徽因、陆小曼、夏梦、尤敏、上官云珠、严幼韵、严仁美、黄慧兰、黄柳霜、胡蝶、张爱玲、郭婉莹她们的旧影,她们的传奇,都让人心生向往。
著名作家吴组缃先生有段回忆说:“上世纪20年代,故都的两所美国气味浓厚的燕京与清华盛行选举‘校花’或‘皇后’。北大没有沾染这一风气,而北大政治系女生马珏却被公认为‘皇后’,名满北京九城,燕京、清华的校花不免‘粉黛无颜色’的愧感。”这位北大女生马珏,就是鲁迅先生曾经喜欢过的北大校花。
马珏是浙江鄞县人,父亲马裕藻,母亲陈德馨,都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两人于1903双双考取官费留学日本,马裕藻在日本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就读,陈德馨进日本目白女子大学学博物。
1910年,他们的长女马珏出生于日本东京。马珏父母经过七年苦读,一起毕业。1911年马裕藻回国后,担任浙江教育司视学。1913年至1915年任北京大学教授、研究所国学门导师,讲授文字音韵学,1921年任北大国文系主任。
马裕藻的女儿马珏长得非常漂亮,在北大被称为“校花”。当时校园中曾流行过一句话:“马裕藻对北大有啥贡献?最大的贡献就是为北大生了个漂亮的女儿。”只可惜,马珏留下的清晰照片太少,我们只能从他人的口述中去想像她的美丽与迷人。
马珏到底有多漂亮?马裕藻一位学外语的朋友曾这样赞美:“像大理石雕出的那么美。”据说马珏在北大读书时,每天收到十几封情书,甚至有装订成本的。
马钰70年前北京大学的校花谁知道她晚年的情况?谢谢
马珏晚年和三个孩子生活在一起,她一生没有离开过大陆,曾在上海儿童图书馆上班,后来跟随丈夫到山东枣庄生活,她能操持家务,自己做菜做饭。1994年,马珏病故,享年84岁。
鲁迅最喜欢的女学生就是民国时的北大校花马珏,马珏是北大教授马裕藻的长女。马珏的相貌十分漂亮,身材修长,相貌清丽。马珏到底有多漂亮,从当时的文人对她的夸奖就可以看出。
一位著名文人曾经这样称赞她:“上世纪20年代,故都的两所美国气味浓厚的燕京与清华盛行选举“校花”或“皇后”。北大没有沾染这一风气,而北大政治系女生马珏却被公认为“皇后”,名满北京九城,燕京、清华的校花不免“粉黛无颜色’的愧感。”
看来马珏是回眸一笑百媚生,众多校花无颜色。
北平曾流行过一句话:马裕藻对北大有啥贡献?最大的贡献就是为北大生了个漂亮的女儿。
北大的男学生,背地里则称马裕藻为“老丈人”。
马珏的父亲马裕藻的一位朋友曾这样赞美马珏:“她像大理石雕出的那么美。”
据说马珏在北大读书时,每天最少收到十几封情书,甚至有装订成本的。
鲁迅先生北大任教时,和马珏的父亲马裕藻是同事,他们十分谈得来。鲁迅经常来马珏家做客,与马珏的父亲一谈就是半天。
1925年,十五岁的马珏写下了《初次见鲁迅先生》一文,刊登于1926年3月的《孔德学校旬刊》上,那是马珏所就读的学校刊物。
鲁迅先生来孔德学校,读到那期《孔德旬刊》,十分欣赏。他夸马珏写得好,说马珏写的都是实话。后来鲁迅把这篇文章收进了他亲自编选的《鲁迅著作及其他》一书中,还送书给马珏。
过了几天,马珏的父亲带马珏去鲁迅在八道湾的家里玩。从此之后,鲁迅到马珏家,常问起马珏;如果马珏在,就和马珏很关切地说几句话。
马珏和鲁迅还多次通信,从1926年元月3日到1932年12月15日,他们通信持续六七年之久。
鲁迅先生对马珏的信几乎每信都回,循循教导,诲人不倦。据有关资料显示,《鲁迅日记》中记有马珏的文字,共有五十三次之多,其中马珏给鲁迅信有二十八封,而鲁迅回信有十三封,另有送书。
美貌如花的马珏没有嫁给豪门公子,而是嫁给天津海关职员杨观保,还送了鲁迅先生结婚请柬。1933年3月13日,马珏结婚,在她婚后,鲁迅先生就不再和她通信,也不再交往了。
马珏和杨观保的婚事在当时是一件盛事,《北洋画报》还刊登了他们的结婚照。但是估计鲁迅没有出席她的婚礼。杨观保追求马珏非常尽力,精诚之至,金石为开,马珏和杨观保结婚时,马珏还没有大学毕业。
看来美女都早婚。天生丽质难自弃,被人追求得紧,早早步入婚姻大门。
鲁迅喜欢送自己写的书给马珏,而马珏结婚后,鲁迅不再送书给她的事,李霁野说:“一次送书给我们时,他托我们代送一本给她,我谈到她已经结婚了,先生随即认真地说,那就不必再送了。”
马珏和丈夫有三个孩子,她一生没有离开过大陆,曾在上海儿童图书馆上班,后来跟随丈夫到山东枣庄生活,她能操持家务,自己做菜做饭。1994年,马珏病故,享年84岁。
-马珏(鲁迅先生好友之女)
这个在鲁迅日记中提及53次的北大“皇后”,究竟是不是他的暗恋?
鲁迅日记中提及53次的北大“皇后”,是鲁迅的暗恋对象,鲁迅十分的喜欢她。鲁迅提及的北大皇后的叫马钰,比鲁迅小29岁,马钰的父亲是鲁迅的朋友,是鲁迅可能就认识了马钰。
而在马钰15岁的时候,鲁迅其实就与马钰相见了,可能在那个时候,鲁迅对马钰也就有了一丝的好感,只是当时马钰太小了,还是个小孩。马钰也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和鲁迅初次见面之后,就写了一些话,对鲁迅所说的,还说中了。鲁迅为此就非常的欣赏马钰这个小姑娘,鲁迅对她产生了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对她非常的好,每次出版新书就会送她一本,可知鲁迅对马钰是喜欢的,只是不知道马钰对鲁迅是怎样的看法。
而且在鲁迅的日记中,写马钰的次数就有53次,一个男孩在日记中写一个女孩有那么多次的时候,其实是这个男孩喜欢上了这个女孩,所以说鲁迅肯定是喜欢上了马钰的,但是马钰是不知道的,而且鲁迅也没有将自己的爱意表达给马钰,知道马钰结婚之后,鲁迅才跟她不来往了,也不在日记里提起了。我觉得鲁迅也是十分的藏得住,要是他能将爱表达出来,说不定马钰对鲁迅也有好感,可能马钰和鲁迅就可以在一起。也有可能是因为鲁迅觉得和马钰的年龄相差有点大,让鲁迅对自己没有自信心,导致不敢说出来,只敢在自己的日记中表达出来。如果我是鲁迅的话,我肯定要说出来,不然放在心里会很不舒服的,有爱就要表达出来才好。
所以说鲁迅在日记中提及了53次的北大皇后马钰,其实就是他的暗恋对象,如果鲁迅当时跟马钰表白了,可能就不会是后面那样子的结果了。
怜香惜玉无关情,鲁迅张中行和马珏
张中行老先生在他那本2006年出版的《负暄三话》中,有一篇文章《马珏》。
他写道:“我1931年考入北大,选中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马幼渔先生(名裕藻)是马珏的父亲;马珏在政治系上学,有一顶了不得的帽子,'校花'。”
吴组缃教授回忆红楼往事时,说:“上世纪20年代,古都的两所美国气味浓厚的燕京与清华盛行选举校花,皇后。北大没有沾染这一风气,而北大政治系女生马珏却被公认为'皇后',名满北京四门九城,燕京,清华的校花不免'粉黛无颜色'的愧感。”话语间透出无比的自豪。
当时在大学校园有句很流行的玩笑话,说马幼渔对北大的最大贡献,是为北大生了个女儿马珏。为此把他戏称为“国民老丈人。”
曾经在北大红楼近处居住过的杨沫,说:“还记得和我一起学昆曲的有北京大学校花马珏。能和一个漂亮姑娘一起学习喜爱的昆曲,我更加高兴了。”杨沫本人很漂亮,她能称为“漂亮姑娘”的马珏,可见的确“漂亮”无疑了。
马珏这朵“花”,绝不是绣花枕头,不是摆着好看的花瓶。她的天生丽质与她的气质素养品性,是相得益彰的。她老爸老妈都是远渡重洋学有所成的海归,她自小看到的是书本,闻到的是书香,听到的是读书声,整个一个由“书”哺育滋养长成的大家闺秀。
马珏15岁那年,小荷才露尖尖角,就写了一篇散文《初见鲁迅先生》。鲁迅先生读后大加赞赏,还收录在他亲自编辑的《鲁迅著作及其他》那本书中。
这样内外兼美光艳四射的“校花”,自然成了北大校园一道靓丽的风景,吸引着无数人的眼球。
张老先生在他的书中回忆道:“诚如我所见,有些人就尽量贴近她坐,以期有机会能交谈两句,或者还想'微闻香泽'吧。以及她后来的文中所说,常常接到求爱求婚的信。我呢,可谓高明,不是见亭亭玉立而心如止水,而是有自知之明,自惭形秽,所以共同出入红楼三年(她1934年离校),我没有贴近她坐过,也就没有交谈的经历。”
张老先生这番话,是对60多年前“校花”的回忆。一江春水向东流,悠悠往事全都云朦胧月朦胧,唯独对“花”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他没有描写“校花”多么美艳,而是从“有的人”的反应那个角度,折射出她的娇媚动人,有点乐府写美女罗敷的手法。
“有些人”,竟敢“贴近她坐”,甚至“微闻香泽”,张先生好像以仰慕之情对那些人的勇气,表示佩服,其实倒泄露了有那么一股发酸的味道。他自己并不是“心如止水”,即使今天想起来,对三年“没有贴近”,“没有交谈”,仍然尚未释怀,很有点遗憾乃至后悔,只恨昨日之事不可追吧。
出乎意料的是,60年后,竟然有了与“校花”近距离接触,咫尺之间独对红颜的难得机缘,是上天给予的补偿?恩赐?虽说“校花”早已消逝了昔日的花容月貌,可毕竟曾经有过力压群芳的辉煌。张老先生有点“漫卷诗书喜欲狂”了吧。
张老先生一准是衣履规整,用剃须刀把嘴巴刮得干干净净,挺直腰板前往的。但是,他
说:“见之前,我心情有些沉重,不是因为都是红颜变成白发,是因为她变化太大,就体貌的处境说,昔年她在众人之上,现在她在众人之下。见面之后,没想到,心情变为更加沉重。”
他又说:“见面之前,我推想她必是寒暄几句,然后举茶送客。见面之后才知道,她是另一极端,她念旧,由另一室扶杖移来,一接近就'执手相看泪眼'。谈,她像是有说不尽的话,情深,发自肺腑,与今日的各种花各种星迥然不同。”
此情此景,让两个人都会不禁想起“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惆怅悲凉。
鲁迅先生似乎比晚生张中行先生的运气要好得多。他与马幼渔是相交密切的挚友,频繁的你来我往。马珏十四五岁,还是个邻家有女初长成的小丫头的时候,鲁迅先生作为马家的座上客,就已经与二千金马珏相识了。
自马珏那篇《初见鲁迅先生》发表之后,清纯率真的文字更是成为一种媒介,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年龄相差27岁的两个人,越来越在精神上贴近,靠拢,成为心心相印的忘年之交。
鲁迅先生特意为马珏起了个号:“仲服”。马珏是马家二姑娘,“仲”即二,好理解。那个“服”是什么意思,就不大好揣测了。
在鲁迅日记里,马珏的芳名曾经出现53次。_饺俗1926年到1932年,共传寄信件四十多函。而鲁迅先生在与其他人通信时,也会常常提到马珏。1927年5月17日,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今天下午我去未名社一趟。又去看幼渔,他未回,马珏因病进了医院许多日子。”十几天后,又在信中告诉许广平:“晚上是在幼渔家里吃饭,马珏还在生病,未见。病也不轻,但据说没有危险。”对这个他叫做“仲服”的女孩,关切之情,溢满字里行间。
在两个人交往期间,鲁迅先生凡有新书出版,都会寄给马珏,直到1933年马珏结婚。他在向朋友交待寄书事宜时,这样说:“今日寄上《萧伯纳在上海》六本。还有一本拟送马珏的。此刻才想到她已结婚,别人常去寄书,似乎不大好。”
鲁迅先生对小美人马珏这种怜香惜玉的情怀,后来在萧红身上又重现了一次。那是1934年年末,漂泊在上海的萧红,在大陆新村9号鲁迅先生住宅,找到了回家的感觉,成了每日必来的常客。
萧红一来,鲁迅先生惯有的横眉,立刻松了,小楼里不断响起他的笑声。不论在写什么做什么,都会放下来陪萧红聊天。常常聊到深夜,鲁迅先生上楼加件袍子,下来继续聊,直到要收末班电车了,才依依分手。鲁迅先生还要送到大铁门外。即使下雨,倚门挥手的桥段,也不能省略。
为了给萧红找发带,鲁迅先生不满意许广平配的颜色,甚至拉下脸子把夫人呵斥一通。萧红做的韭菜盒子,鲁迅先生破例吃得津津有味,不肯放下筷子。
有一本萧红传记,作者写道:“总到人家串门,确实会把人家的生活打乱,去了,女主人要陪着笑脸和时间,后来许广平也觉得有些累”。恐怕不只是“累”吧。可看见鲁迅先生开心,许广平只能强颜欢笑。
1976年,张仲行老先生去苏州闲住,常去小商店买酒。“卖酒的是个年轻女子,至多二十岁,细高个儿,也许从业不久吧,与顾客面对还脸红。她不会说普通话,我不懂苏州话,所以我们交往,只能以形代声,比如买哪一种,就指黑板哪一种,然后是伸指,一指是买一两,二指是买二两。然后付钱,她找零数,总是点头兼微笑。就这样,我们的交往,总不少于十次吧,竟没有交谈一句。过后回顾,住苏州半个月,_医煌疃嗟模故钦馕荒昵岫恢彰墓媚铩薄
苏州地杰人灵,古迹众多,可观可记者,不能细数。可这篇回忆录,虽然也出现过沈复,柳如是几个人的名字,但几乎一笔代过,偏偏用这么多笔墨写这个“年轻而不知道姓名姑娘”。有那么一点情有独钟吧。
而且,这篇文章作于二十年后,可“细高个儿”,“脸红”,“点头兼微笑”之类的细节,仍念念不忘。同时颇有几分牵念:“一晃将近二十年过去,她还在那个商店吗?如果江山不改,年近不惑,应该升为店主了吧?”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书生的怜香惜玉并不因这个独特身份,而扭扭捏捏,遮遮掩掩。而是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坦诚直率,憨态可掬。于是,书生的怜香惜玉,就变得可敬可叹了。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表白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