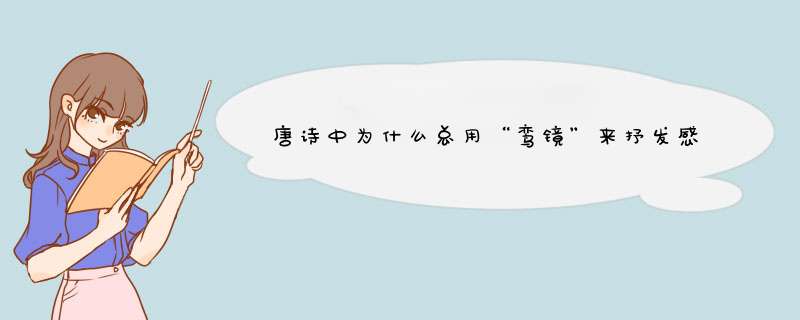
今天,校易搜带给你一篇
唐代是一个高度繁荣的封建时代,艺术氛围浓厚。不仅涌现出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等杰出代表,其他天才诗人也相继涌现,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激情浪漫的诗词歌赋。正是这些诗词,让盛行于唐代的冷鸾镜和冷鸾镜一样,成为了唐代众多女性情感生活的载体。
唐代诗人“王建”示意图
唐代诗歌中的鸾镜
正如唐代学者乔在《诗经杂歌》年所写,“妾有秦家之镜今天,作为礼物,互相认识并不反对”。起初,冷酷无情的鸾镜显然成了唐代男女表达离别之情、寄托爱情的“象征”。
再比如《感官之镜》里的“美女和我不想待在一个盒子里”。秋水里没有芙蓉花,因为花已经枯萎了。也是唐代女性在与恋人分手后,通过《鸾歌》表达的思想。
所以,就连唐代的一些女性也给鸾镜带上了一种“封建迷信”的玄学味道。他们用镜子占卜,称为“镜卜”或“镜听”。
唐代诗人王建曾根据唐代妇女“镜中听”的现象,写出《镜中听言》。“当你和一面镜子结婚时,会有很多摩擦,而丈夫则通过它旅行。”
它通过《鸾经》清晰地刻画了这些唐女的模样,通过她们洞察到了恋人的现状,表达了对恋人的思念和永远在我心中。
罗示意图
是初唐四杰之一,也不算太远。《鸾经》年,他留下一句诗,“龙标不报,明镜倒”。
然而,这些案例只是唐代“鸾镜”相关诗歌的冰山一角。但唐代诗歌中的每一面“鸾镜”,无论艳丽、婉约、浪漫还是悲凉,几乎都承载着唐代女性对恋人、爱情或离别的渴望。
相信大家不难发现,它就是唐代无处不在的“鸾镜”,没有情感特征。在这些唐女的心目中,它似乎是她们感情生活的载体,是她们与恋人之间的“信物”。用“一面镜子,一种爱”来形容这种文化特征并不为过。
那么是什么让这些普通的“鸾镜”如此“不一般”呢?
化妆镜示意图
“銮镜”的由来
说白了,“鸾镜”终究是一面普通的铜镜,还是一面以“夫妻纹”为主题的铜镜,在古代也被称为“化妆镜”。如果放在现代,只是现代女生梳妆台上必不可少的“化妆镜”。
但在古代,没有先进的玻璃精炼技术,没有先进的化学“银镜反应”理论,更没有先进的电镀技术。
所以没有办法用“汞”和“锡”做“汞玻璃镜”,也没有办法用“银”或“铝”做“电镀玻璃镜”。
在古代,人类只能以“水”为面,即以“水”为镜。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开始使用青铜器后,不方便与水相对,于是进一步按照“虑水”的思想制作“铜镜”。——庄子
盛水的“铜盆”示意图
这里的“鉴”并不是我们现代通常所说的“鉴定”、“评价”、“欣赏”。按照《女道士王赠道士李融》的解释,这里的“简”应该是指“盆”,也就是“铜盆”。
所以“镜”的起源其实是基于古代的“盛满水的铜盆”,把水去掉,只留下盆。然后在建造的时候,特意把铜盆的边缘去掉,只留下“盆底”,再用“铅锡”打磨,使其发亮。
然后随着封建制度的更新和重复,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栾镜象的质量和产量也有了质的飞跃。就像我们现在的镜子,已经成为人们家中不可或缺的东西。
铜镜文物说明
但是,无论是历史渊源,还是镜子的制造工艺,显然都和现代的镜子一样稀有和常见。基本上没有理由拿这么一面普通的镜子当信物。
就像我们是现代人,谈不到男女分家的时候,让他们每天多照照镜子。可以想象场景会是什么样子。
这就意味着,《唐女传》用“鸾镜”作为“感情生活”的载体,一定还有别的原因。准确的说,这个原因不是“鸾镜”,而是“鸾镜”镜框或者背面的“夫妻纹”。
鸾鸟画像插图
《鸾歌》体现了唐代女性情感生活的精髓。
《说文解字》,《山海经》记载:“西南三百里女儿山有鸟,如翟、鸾,天下太平。”
《西山经》年,“鸾鸟,”也被记录了下来。换句话说,同样是“鸾鸟”的凤凰的神话特征,使得它在传说之初就有了不同的含义。再加上古人普遍的封建迷信,使得“鸾鸟”逐渐从古人虚构的人物演变为“吉祥”的象征,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此外,由于凤鸟也属于凤凰,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开始对凤凰另起称呼,夫妻,用“夫妻和睦”来表达夫妻之间的和睦。
但因“凤帝,灵鸟任锐也。如果男性是“凤”,那么“鸾”自然成为隐喻“美”的最佳载体。——《诗大亚湾卷》
如唐代诗人陆褚在《广雅鸟释》中描述,“今幸为秦晋所用,教夫妻早上妆楼。”这无疑是用“鸾”比喻美的真实体现。
双鸾题葵花镜示意图
因此,由于“夫妻”独特的象征意义,成为唐代最常见的装饰图案,体现在服饰、铜镜、石雕、金银器皿、玉器等诸多物品上。就像陕西历史博物馆里的“双鸾花镜”、“双鸾飞镜”、“双鸾花镜”一样。
简而言之,《鸾镜》承载了唐代女性情感生活的精髓,但实际上它是“夫妻模式”的一种独特形式,它的神秘起源,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吉祥寓意,如长寿、吉祥、平安、爱情、幸福等。
正如唐代诗人李群玉在《补妆》中所描述的“我见过双熊舞镜,对联飞迎春”,这无疑是“夫妻模式”下唐代女性情感生活的真实写照。
古代新娘插图
比如前面提到的“结婚摩擦多”这句话,正是因为“夫妻”这种吉祥的象征意义,使得女性在封建时代结婚几乎是必须的。作者之所以要说《镜中之恋》,也是这个原因。
夫妻题材的鸾镜,在当时是很容易买到的物品。它比衣服等易损物品便宜,更适合长期保存。通过鸾镜自然成为了普通女性追求幸福爱情和婚姻的首选。
毕竟金银之类的东西太贵,一般的唐女买不起;石雕比较少见,大部分人没有雕刻技术;即使不穿衣服,时间久了也难免会有一些损伤,不是吗?
唐代人物画素描图
唐代女性较少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
此外,受唐代繁荣、开放、自由等因素的影响,唐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在封建时代是独一无二的,很少受到“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的影响。
她们可以抛头露面,走出闺房,走上街头,自由出入公共场所,像当时的男人一样参加各种娱乐和社交活动。
当然,对于男女之间的交往,自然不同于封建时代的大多数政权。甚至有很多女人直到新婚之夜,也是第一次看到自己的老公长什么样。
正如中国国家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原主编高在《伤逝》一书中所写,“未婚女子私交甚好,
唐朝的女人,从名门千金到闺中淑女,田间村妇,几乎所有女人都能大胆向自己的“白马王子”表白。她们追求爱情和婚姻的自由,表现了唐代封建时代女性特有的勇气和主动热情。
然后因为这种丰富多彩的“感情生活”,产生了爱情、思念、离别、悲伤等一系列感情。当然,他们需要找一些能让他们放下情绪,然后倾诉寻求安慰的事情。
在这种背景下,《鸾歌》走进了唐代每一位女性的视野,通过张扬、婉约、浪漫、悲凉,成为她们“感情生活”的“表征”。
古人之所以将鸾镜一分为二来象征夫妻分离,或者用二次轮回来比喻夫妻团圆的做法和观念,其实正是因为鸾镜在时代的发展中逐渐具有了这种特殊的“文化象征意义”。
国防情报局要求照片插图。
它不再是一面普通的镜子,而是一种文化符号,标志着古代女性的“爱情观”。这是一个可以将他们的“爱”流传千古的“永恒纪念品”。从这个角度来说,并不比象征永恒爱情的Dia差。当然,这里不谈价值,只谈意义。
结束语
《鸾镜》是这样的。它与“夫妻模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唐代女性情感生活的载体。它的功能不再像现在女生必备的“梳妆镜”,只是照照镜子,它还起到了“象征性”的社交功能。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无数古代诗人才能给后人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成为我们探寻古人生活轨迹和情感生活的渠道之一。
俗话说“凤凰离恨,百岁心难忍。若弘子遇隋朝,破镜无故重寻。”也许每一面流传至今的《鸾镜》背后,都有一个古代女子美丽优雅的爱情故事。——“笔红耳实”
爱人。《灵舟》是连载在在17k小说网的一篇古典仙侠类的网络小说,作者是网络写手九当家。这本书主要讲述了太古神凤转世而来的风飞云于奇异世界中大放异彩的故事。在小说中东方镜月和主角的关系在太古时与主角相爱,却因身份相对立,主角自愿被其所杀,这一世是主角末册封的女人。
苏摩为了救白樱的命死了,在临死前终于对白樱表白,并在死前驾御了7海,淹没了云荒,为鲛人复了仇 云焕和他体内的魔被慕烟永远的封印了,萧陪着他一起被埋葬在沙漠中。 白樱在哀祭塔里陪着苏摩的尸体直到老死,死了以后灵魂去接真岚进入归墟一起转世去了 (苏摩做为鲛人没有灵魂,无法转世,遗憾。。。)
二、西汉中期铜镜:光明的渲染 西汉中期的典型铜镜是日光镜,典型纹样是文字,典型铭文内容是“见日之光”。这种舍弃图形而单纯以文字装点铜镜的原因可能与丧葬观念有关,直接以文字的形式显示铜镜的作用较之象征意义的图形更加通俗易懂。这是将铜镜比拟为太阳的确定完善时期。在用途方面,铜镜由照容、佩戴而向随葬转化,设计理念也因为铜镜用途的改变而作了很大调整。
这个时期铜镜的设计理念和早期一样,也有着明显的承前启后特征。在铜镜图形和构图布局方面既有完全照搬早期图样的,也有开创晚期新风的,因此,呈现给人们的印象是丰富多彩,变化多端。如果再详细分期的话,中期前段主要是继续了西汉早期的传统,图像以植物纹为主,由花卉变为草叶,继而星云、螭龙、云雷等等;后期则由日光加草叶加连弧,最后完全舍弃动植物图像而以文字所取代,文字成了主导装饰元素。
在构图方面,除了象征太阳光芒的连弧纹被继续接受外,短斜线的光焰纹也被特别加强。中期前段典型的星云纹镜最突出的特点是把太阳和星宿合二为一,进一步强化了铜镜的照明意图。就图像而言,星云纹镜的纹样在草叶纹镜大连弧的基础上,按照四分的方式把大量乳钉装点在镜背上,使铜镜的照明能力进一步提高,既有太阳的光芒,又有星宿的闪烁,白天、黑夜都有光明,铜镜的照明成分再次被充实扩大。同时,为避免乳钉象征星宿的表现被误解,还在各个乳钉及其组合之中串联上云气,以表明星宿所在的宇宙环境,加深人们对星宿形象的认识。星宿是夜空照明的光源,这种加大星宿图像的设计,应该与黑暗或黑夜有关。仅仅一个太阳还不能满足照明的需要,还要加上众多星宿,说明人们对黑暗世界的担忧是何等的恐惧,对光明的追求又是何等的强烈!而这种程度的黑暗决不会是普通的自然现象,而应该是指暗无天日的墓葬或地下黄泉世界。至于在镜钮四周以四个较大一点的乳钉为中心划分为四区或环绕六个乳钉并保存了六边形的连弧纹,则有可能象征了普照四方的观念,正所谓“铜镜一出,天下大明”。如此强烈地追求光明,实际上也暗示了铜镜的主要用途,就是为墓室照明,让地下充满阳光,让阴曹地府像人间世界一样光明,白天黑夜没有差异,地上地下共处一个世界,让死者安心安息,去他界继续快乐生活。
在光辉普照的设计理念主导下,以文字为主体的日光镜和昭明镜逐渐主宰了西汉中期的统治地位。也许抽象的云气乳钉还不足以表明铜镜照明的意图,所以,明白如话的日光铭文就开始取代原来的图形,让人们看了铭文就明白,简单直接,一目了然。但是,对于早期创造的太阳纹样,日光镜也没有完全弃之不用,而是像星云镜那样缩小范围,减少面积,将原来延伸至镜缘的大连弧安排到铜镜中心,使之围绕镜钮放射光芒。16条连弧缩减为6条,由外向变为内缩,由大到小,最终彻底抛弃连弧。不过,除了用文字直接表现铜镜是太阳的象征外,这个时期的日光镜还将早期蟠螭纹镜中出现的光焰纹接受过来,发扬光大,一圈不够,再加一圈,以烘托和加强太阳的意味。另外,为了保持太阳的动感运转,有些铜镜还在镜钮周围添加了几条同向弧线,以象征“太阳”的旋转,保持“太阳”的运行动态。这一点在《长安汉镜》1999YCH M108:18(图13西安昭明镜拓片)、1997FXC M9:2(图14西安昭明镜拓片)和1999YCH M52:21(图15西安昭明镜拓片)等昭明镜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文字内容主要为两大类:一是怀念,二是表白。怀念的文字主要表现在日光镜上,表白的文字则集中在昭明镜上。怀念内容是“长毋相忘”、“长不相忘”和“久不可忘”;表白的则还是早期昭明镜的内容,说镜子好,人也好。但与早期相比,表白的内容有所删节,主要是“内清质而昭明,光辉象夫日月,心忽扬而愿忠,然雍塞而不泄”。早期铜镜有怀念美人或大王的表现,这个时期的怀念则更加强烈,怀念的对象也由帝王、美人扩展至寻常百姓逝去的先人和亲人,并最终由特指的铭文转化为更广泛的对亡人的怀念,长不相忘的意义终于完全融合在了丧葬活动之中。结合铜镜像太阳一样为墓室照明的用途,可以推断这些铭文反映的应该是对死者怀念的一种普遍性的情绪。
文字内容的压缩,特别是文字图形化的处理,说明这个时期固然有明白如话的简化设计,但也开始产生了将文字当作图像设计元素的理念。所以,有一些铜镜在铭文之间添加一些如“而”、“田”以及谷纹云气符号等,使其铭文有所变化,最终将铭文改造成铜镜纹样的一部分,装饰成特殊的纹样带。铭文一旦被当作图案使用,文字内容就不可避免地流向程式化,和文字设计的初衷相背离,最终使这种通俗明白的设计在规范装饰之中改变了本来面目,这也是西汉中期铜镜纹样的一个重要变化。
三、西汉晚期铜镜:辟邪和永恒
西汉晚期典型铜镜的类型是博局镜,其主导形式是外圆内方,并在布局之间添加四神、鸟兽或几何纹,将象征太阳的铜镜营成了神秘和升仙的环境,让铜镜充当起辟邪道具和升仙指南(图16日照海曲西汉墓博局纹镜)。象征太阳光芒的连弧纹被完全舍弃,代之而起的是锯齿状的三角纹或三角连弧纹,中期铜镜的典型纹样光焰纹继续存在,此外还出现了四乳、七乳禽兽镜等新的图案样式。
从西安出土的博局镜形式看,最简单的纹样是乳钉或谷纹与博局的组合,博局为主,乳钉或象征云气的谷纹穿插其间,复杂者则在博局和云气之间添加禽兽或四神,乳钉则被淡化或删除。禽兽和四神或围绕博局的“V”形或“T”形纹对称设置,禽兽的数量一般成四对八个。这种数字的对称或对偶,应该与西汉晚期阴阳思想的影响有关。
将游戏活动的棋盘装点在铜镜上,意图何在《汉书·哀帝纪》、《五行志》、《元后传》、《王嘉传》等记载过一件大事,哀帝建平四年(BC3年),发生了一次民惊,平息民惊的一个方法就是举行聚会,设置博局,歌舞祭祀西王母。结合“刻镂博局去不羊(祥)”、“左龙右虎去不羊(祥)”、“上有古守(兽)辟非羊(祥)”等铜镜铭文,可以清楚地看出,铜镜上的博局纹样和四神等形象是为了辟邪。将这样的铜镜随葬地下,可以驱除恶鬼,保证亡灵不受侵害,安息地下。但是,博局纹样也许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升仙或长生不老。《风俗通·正失》说:“武帝与仙人对博,碁没石中”。这当然是传说,但下棋入迷忘却时间,也就是让时间停止,正好可以延年益寿。枣庄小山西汉中晚期画像石椁墓葬中,其石椁底板刻画有博局画像,棺材放置在底板上,这种设计意图十分明确,那就是将死者定格在棋盘上,让其永恒不朽(图17枣庄小山石椁画像墓线图)。结合这个时期铜镜铭文中的“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敖四海”、“保长命兮寿万年”等文字内容,可以推断,铜镜上的博局、云气及禽兽和镜上的仙人形象,显示的是升仙和不老长寿的理想追求。这种辟邪和升仙,也正好是西汉中晚期画像石的主要题材。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应该与西汉中晚期谶纬迷信思想的流行有关,也与王莽时期儒家思想教条化有关。
就铭文而言,这个时期的铭文继续了日光、昭明镜的圈带设计,将主题内容布置在外圈,十二地支则安排在镜钮周边。铭文内容一是鼓吹铜镜做工好,质量上乘,如“尚方作镜真大好”“尚方御镜大毋伤,巧工刻之成文章”“新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清且明”等广告语;二是歌颂王莽的新朝,如“杜氏作镜四夷服,多贺新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唯始建国二年新家尊,诏书数下大多恩”等媚上语句;三是升仙和长生不老,如“上大山,见神人,食玉英,饮澧泉,驾文龙,乘浮云”“凤凰舞兮见神仙”等;四是辟邪,如前文所述;五是保佑家人平安幸福,如“长保二亲和孙子”“长保二亲受大福”“长保二亲及妻子”等。把众多希望甚至梦想付诸铜镜之上,表明铜镜具有重要的护佑作用,这种作用应该是辟邪作用的延伸和扩展。由此,也可以明白,至少从西汉中期以来,人们已经普遍认为铜镜具有辟邪和护卫的成效。基于这样的认识,西汉晚期铜镜为什么要选择博局及四神等纹样的意图也就一目了然。这也是解读铜镜纹样的一把钥匙,一条线索。
从西安出土的铜镜还可以看出,西汉晚期除了博局镜这样具有典型晚期风格的铜镜外,还大量流行过日光、昭明和四乳镜。其中四乳四虺镜以其蚯蚓似的虺龙形象,加剧了铜镜的恐怖成分,使其辟邪的功能更加突出。而日光、昭明镜的铭文则完全规范化、程式化、装饰化,其内容除了继续中期的基本模式外,少有变化。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表白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